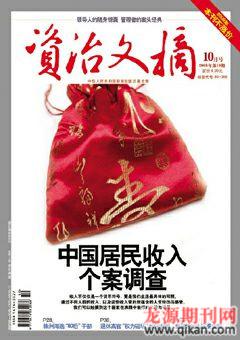醫生需要強制治療權嗎?

當一名醫生面對患者拒絕治療時,為了患者的最大利益,應該敢于拒絕患者的決定,畢竟生命只有一次。
廖新波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
我們現在的醫療改革方案離現代醫療模式的要求太遠,也與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差太遠,也與人們日益增長的需要相差太遠。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對醫生的積極能動性沒有充分發揮,也沒有充分尊重,比如醫生的專業自主權完全是跟這病人走,看病人的“臉色”行事。與我國相似,患者拒絕治療的事件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也時有發生,不同國家醫務人員以及法官對于建立在知情同意權基礎上的患者自我決定權的觀點不同。
美國:1993年判例
一名30歲認知能力正常的懷孕32周的患者,當時已經破膜,由于宗教的原因拒絕剖腹產手術,要求自然分娩。但如果不手術,胎兒可能不能成活,并對母體造成嚴重傷害。醫院最終決定進行剖腹產手術。產后該產婦起訴醫院。法官在判決書中指出,盡管剖腹產手術沒有取得患者的同意,但是為了孕婦的身體和未出生的胎兒這兩個“重大利益”所進行剖腹產手術和相關后續治療都是合法的,醫院無需承擔侵權責任。由此可見,一些美國法庭認為在保護第三方(特別是胎兒)的身體和生命時,強制治療是公平的,即使違背其宗教信仰,醫院采取的措施也是恰當的。
英國:1997年判例
一名懷孕40周的患者產前檢查胎兒臀位,若是自然分娩,50%幾率對胎兒造成嚴重損傷,對母體傷害較小。孕婦起初同意剖腹產,但當她看到手術室的醫療器械后,因恐慌而拒絕剖腹產。醫院認為剖腹產是正確的處理,并繼續治療。之后,患者以違反知情權起訴醫方。上訴法庭駁回了患者的訴訟請求,并認為孕婦看見手術器械出現恐懼,影響其正確判斷,當時拒絕治療是片面的,拒絕手術也是無效的。
加拿大:1990年判例
患者屬于基督教耶和華見證會成員,該會有規定,會員在手術時不能輸血。患者發生交通事故后昏迷,外科醫生在治療時發現患者隨身帶有一張卡片,聲明本人是耶和華見證會的成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輸血。根據當時情況,患者不輸血就會死亡。醫生最終決定給予輸血,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患者后來起訴,法院判決醫生構成侵權。法官認為,自我決定權是社會權利的基石,本案中,患者拒絕輸血的后果即使是不良的、錯誤的甚至愚蠢的,醫生需做的是勸說和解釋,去幫助患者改變決定。醫生對耶和華見證會的人員輸血治療違背了患者的自我決定權。最終判決醫生對該患者賠償精神損害費20000加元。
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公民,患者有自我決定權和知情同意權。患者的知情同意權是指在不違背法律及公序良俗的情況下,事前明確表示愿意承擔某種不利的后果。
醫療行為對人體具有侵襲特性決定了診療行為前,醫生必須履行知情同意權。該知情同意權免除的是,按照診療常規治療時對人體造成的合理、必須的損害的侵權責任。在上述英國的判例中,孕婦在神智正常狀態下,做出同意剖腹產的合理決定,但當她看到手術器械,因恐慌拒絕剖腹產時,已經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知情同意,而是建立在重大誤解基礎上的決定權,因此,拒絕治療是無效的。而在美國判例中,因為孕婦拒絕手術的自我決定權不利于保護產婦的身體健康和未出生的胎兒生命這兩個“重大利益”,違背了公序良俗,因此是無效的自我決定權。所以在這兩種情況下,醫生所履行的合理診療決定權是無須承擔侵權責任的。加拿大關于拒絕治療的這則判決發生在安大略省,其他省的法官對該判決的意見不一。基督教耶和華見證會的成員在歐美國家常見,判決也不同,尤其在涉及到第三方時。比如美國一個2歲的嬰兒需要輸血時,其母因為宗教因素而拒絕;請速栽法官決定時,法官認為必須馬上給患兒輸血,而拒絕患兒母親因為宗教因素做出的拒絕治療的決定。美國和加拿大的不同判決,可供我國醫務人員做決定時參考。總之當一名醫生面對患者拒絕治療時,為了患者的最大利益,應該敢于拒絕患者的決定,畢竟生命只有一次。
(摘自人民網強國博客2008年8月18日,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