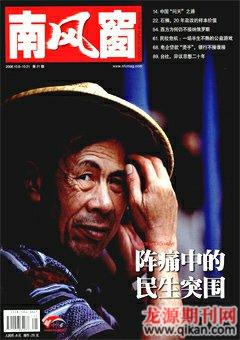轉型陣痛中的企業和勞動者命運
郭 凱
許進良模樣很黑,講話聲音也非常粗。這個1960年出生在蘇州吳縣一個農民家庭的民營紡織企業家,商海拼殺多年,本色不改。
2008年,對許多過去進行出口紡織服裝產品生產的企業而言,是個困難年。但是在許進良這里,2008卻是他的飛躍年。
政策“反復”中的艱難營生
命運的反復,要回溯到2004年。
那一年,為了控制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的通貨膨脹和投資過熱的勢頭,中央政府不得已祭出了宏觀調控的系列政策。無奈受累于2003年各大部門各自布局,中央政府2004年整體宏調政策出手太晚,對通脹和過熱的治理沒有達到理想效果,“局面失控”開始讓有關方面膽顫心驚。最后,那一輪調控以中央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直接處理江蘇鐵本公司項目達到高潮,史稱“鐵本事件”。
“鐵本事件”和鐵本事件“當事人”,是那一年的“大事件”、“大人物”。就在同一年的經濟震蕩中,還有很多“小人物”遭遇了“小事件”。許進良,就是其中之一,還有他的雅新服裝有限公司。
2004年,蘇州吳中區民營企業雅新服裝公司由于一個生產和管理意外事件,遭遇幾十萬的經營損失,現金流極度緊張,眼看資金鏈就要斷裂,已經有著幾百萬元規模的企業無法延續生產,就只能破產。許進良跑遍了各個大小金融“衙門”,就是貸不到款,但廠里幾百口工人,在等著老板出糧。在許的眼里,看得到的幾乎都是“絕路”。
“只能說我命大”,在2008年8月,許進良這樣總結。2004年,最后靠朋友們湊錢還有“民間金融”出手,許進良籌到了現金。給工人支付了拖欠的工資、償付了生產債務之后,余下的“銀兩”怎么用才能精打細算挨過來?生產怎樣布局,才能保證下一次遇到危機時不這么被動?許進良開始了一個農民企業家從前沒有做過的企業長期發展規劃。
他判斷,在蘇南地區,眼看紡織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成本一天天上升,一直在蘇州開制造廠不是長久之計。2005年到2006年,他把制造工廠搬到了生產成本更廉價的江西,他把蘇州的廠房和土地轉成倉庫、產品展銷廳和商業性的生產物業,除了自用,還租給別的企業。
因此在今年紡織業出口大環境不景氣的時候,他的成本比還留在蘇州的生產企業低,尤其是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人社保的繳納標準低,這也讓他節約了不少費用。“沒有蘇州老廠區的倉庫和物業開發經營補貼,也根本沒有足夠的盈余資金轉型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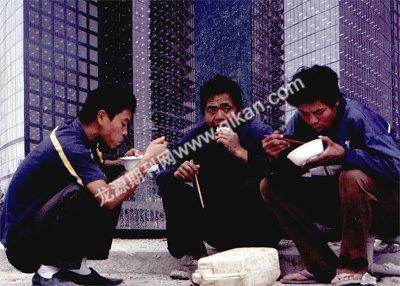
許進良說,2004年他栽了跟頭,靠民間金融活了下來,但他也因禍得福,早作打算,躲過了2008年的這一波小紡織企業倒閉潮,并且趕上了蘇州地區的物業和土地增值,獲得的收入讓他有能力早下手收購了北京的一個中小規模、有自有品牌的羊毛衫企業。作為一個過去面向出口、專事貼牌生產的民營紡織企業,“從出口向內轉,如果沒品牌、沒渠道、沒市場團隊,這個轉型要多久才能做完?”
現在看來,許進良當時的收購價格是很優惠的。許說,現在大家都來找這種有國內市場、規模不是太大的紡織企業收購的話,就會發現這樣的企業資源很有限。更多的出口企業,如果在紡織品出口競爭中被淘汰、要轉國內市場的話,大概就只能第二次創業了。
當被問及進一步擴大企業經營鏈條、擴大生產規模和市場占有率的戰略時,許進良說,他不會考慮收購現在國內的那些中小紡織企業,因為它們沒有任何(收購)價值。沒有價值的原因,在于沒有生產技術、沒有管理技術、沒有競爭技術。但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企業和資金投入這個行業?
許進良說,2004年宏觀緊縮后,不想2005年、2006年各大小金融機構又開始大舉放貸,很多企業發現終于有錢借了,“紛紛把握機會,大舉借錢,大舉擴張”。宏觀政策的反反復復,對企業投機心理的影響,是造成2004年后的幾年間紡織行業過度投資、過度競爭的主要原因。
張家港市大型民營紡織企業江蘇東渡紡織集團董事長徐衛民說,2008年倒得快的紡織企業,大都是在過去幾年平面化大舉擴張生產規模的企業。“在前兩年的成本上升期擴張得越多,在今年問題暴露的高峰期就倒得越快。”挺過這一段
然而,問題不僅僅在于整體宏調政策的反復無常。許進良說,紡織行業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人成本是重要的生產成本,在前兩年企業有利潤、都在大舉擴張的時候,辦企業的誰都不知道,2008年會有《勞動合同法》出臺執行。“如果不是我剛好把工廠搬到內地,今年所有的政策和國際形勢撞到一起,我也受不了。”
東渡紡織集團董事長徐衛民說,雖然說今年有國際大環境的客觀不利因素,但是國內宏觀政策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形勢,深度匯率改革、出口退稅改革和新《勞動合同法》都沒有在前幾年的行業擴張和經濟上升期及時推出,不僅沒有給企業自我權衡和經營調試的緩沖期,還在今年與國際經濟不景氣帶來的市場萎縮、國內通貨膨脹導致的成本上升,“集中撞在了一起”。這是對紡織行業企業生存的最大打擊。
由于通貨膨脹,農民工生活成本上升,要求提高工資水平,現在在蘇南地區招工也是一大難題。江蘇省中小企業局綜合管理處處長繆鳴說,現在招工難的情況,在江蘇不僅僅是紡織業一個行業的遭遇,很多行業的中小企業都遇到這種情況,要么招不到工,要么招不起工。繆鳴說,這在長三角、珠三角,屬于同類性質的問題。
匯改后采取的“小幅漸進升值”方式,則給出口企業帶來了一直延續至今的傷害。蘇州經貿委薛峰主任說,他們經貿委到企業調研的時候,總有出口企業問,“你們能不能和中央政府說,每次人民幣調匯率之前,先告訴我們一聲?”
薛峰說,出口企業的提問,雖然有人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恰恰反映了目前這種匯改方案下,出口企業面臨的被動局面。很多企業剛剛簽了出口合同沒有多久,匯率接著就變了,企業說是“一天一個樣”,到頭來,只落下交貨也賠錢、不交貨也賠錢(違約金)的結局。
在江蘇傳統紡織工業集中的吳江市,紡織企業就陷在了這種匯率改革制度下,營生艱難。吳江一個中型紡織出口企業吳江中春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陳芳英說,在中春紡織,對美元地區出口只是一部分公司產品還有不小的份額是面對歐元區出口,但許多歐元區的客戶就是不肯用歐元和他們簽合同,一定也要用美元。
經常是合同簽完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就變了,而最怕是產品生產完工了之后,匯率已經變了一大截。這時候,“寧愿賠違約金,也不愿意交貨后再等收美元進來。”因為不但交貨會虧錢,等對方把美元匯過來,他們緊趕慢趕去結匯,結果發現虧得更多。“賠違約金,至少損失在當時還是可以控制的。”陳說,如果在簽合同時,匯率已經變化、人民幣兌美元已經升值,至少企業可以根
據成本判斷,這樣的單子能不能接,如果出口價格不能接受、選擇不簽單,也不用賠違約金、浪費采購和生產開支了。
“有時候也會對未來感覺渺茫,不過現在就只能希望挺過這一段。只要我們挺下來、沒有垮掉,總是有很多客戶要來進口的。”陳說。
徐衛民則表示,現在這種人民幣小步漸進升值的方式,不但救不活過度競爭的紡織行業內那些沒有實力、一直靠各種出口補貼生存的若干企業,還會把本來有實力發展自有品牌、進行技術和出口產品升級的企業拖垮,讓這些企業沒辦法根據真實匯率和外國客商談判價格,面臨不停賠錢的生存危機。
至于出口退稅,徐衛民說,出口退稅的回調,絕不是對所有出口企業都有好處的,尤其是對有競爭力、原本可以與國外客戶議價的出口企業。因為出口退稅的補貼,讓一些本來按照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應該退出的企業,繼續得以以廉價競爭手段壓低中國出口紡織品的整體價格,傷害其他企業。而出口退稅,“也很可能是補貼那些貿易型的代理公司的,讓他們和生產性的自營出口企業繼續進行價格競爭。”
要為企業和勞工落“實力”
在紡織業曾經是傳統支柱產業的蘇州,經貿委主任薛峰說,紡織企業確實遇到困難,正在經歷經濟轉型過渡期,但是沒有任何必要恐慌,區域內很多新興支柱產業正在蓬勃崛起。同時,對于紡織這樣的傳統產業,需要各級政府落“實力”,從行業的真實需要出發,扶助行業實現產業升級,其中,對行業技術革新和企業生產技術改造升級的支持很重要。
薛峰舉例說,現在的印染紡織業面臨的一個很大困難是產業發展與水資源保護的關系問題。但是,發展印染紡織工業不代表就一定會帶來水污染,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在于技術創新和突破。薛說,他曾經到過一些銳意革新的印染紡織企業,那些企業進行了很大投資,試圖在“無水印染”技術上實現突破。但是各級政府對此也有責任,需要幫助企業分擔技術革新的投資風險。
而且從更廣泛的支持行業發展、實現產業升級角度出發,政府對紡織行業技術革新的支持,將惠及更多企業和工人。
吳江市經貿委主任王劍云說,希望中央的宏觀政策部門在出臺全國性的或者“一刀切”式的政策之前,能夠謹慎出手,先到可能受到影響的基層了解企業和當地實際。他舉例,新的行業政策要求要控制印染紡織行業、不許在太湖周邊多少范圍內再投資行業項目,但是要進行技術改造、產業升級就需要追加投資,而且通過技術改造,行業企業可以有機會煥發生機,但是“一個政策一刀切下來”,有競爭力、有希望的企業,也就喪失了發展機會,只能坐等死亡。

江蘇省前發改委主任、現南京大學教授錢志新說,我們講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升級,本身就包含了要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改造升級、提升產業競爭實力的含義。許多傳統行業同時也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有大量的產業工人基礎,對這些產業提供切合實際、確實能促進產業升級發展的產業政策,與我們要花力氣發展高科技產業、新知識經濟產業,是互相促進、互相關聯的。
據了解,有關方面已經開始在江蘇進行調查研究,試圖依托蘇南和蘇北之間、聯接長三角和環渤海之間的海岸線區域,布局新興產業、建成新經濟增長點。這樣的思路,與廣東的湛江區域開發、廣西北部灣開發等新經濟增長極的構建基本相似。
然而,如果中央政府不能在解決收入分配矛盾、提高國內居民消費能力的根本問題上落“實力”,各個省區的新增長極,未來都會陷入以出口為經濟導向的珠三角、長三角的窠臼。
廣東省一位政府官員說,今天珠三角或者長三角所處的經濟轉型周期,都不需要驚慌。在早先的上海,紡織業曾經是第一大支柱產業,但經過產業轉型、經濟結構升級,現在上海已經成為亞洲最繁華的經濟中心之一。
目前的廣東東莞,區域經濟同樣在轉型,而且也為地方經濟進一步提高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提供了有利條件。在珠三角先行一步的深圳,早已經度過了轉型過渡期,支持地方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龍頭企業基本都是科技、高端制造與服務業企業。
更為深遠的擔憂,在于如何提高國內勞動者的消費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終要靠內需支撐。但是,現在中國的所得稅制一直以過度對工薪階層的收入課稅為增長支撐。在價格體系上,直接影響中西部人口收入和消費能力的資源性商品價格改革推進乏力,事實上繼續惡化了東西部的收入差距,因為中西部一直在以被管制的廉價價格,向東部工業省份輸出能源資源。而作為最大消費人口群體的農民,面對過度管制的糧食價格,靠種糧致富的道路,被毫無討價還價空間的政策堵死了。
如果上述影響內需的根本問題不能夠從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逐一解決,可能要經歷經濟轉型期的陣痛的企業和勞動者,就不僅僅局限于目前已經出現在人們視野中的那幾個傳統行業。
責編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