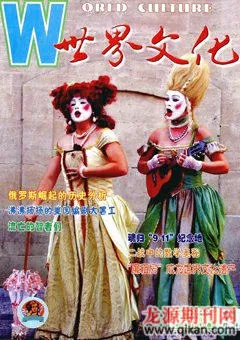卡夫卡與弗洛伊德
卡夫卡(1883~1924)與弗洛伊德(1856~1939)基本上屬于同時代的奧地利人:一個是偉大的作家,一個是杰出的心理分析學家。他們是如此相似:都出生于猶太資產階級家庭,生活在種族的仇恨和歧視之中,接受的是德語教育,都對探索人類心靈的秘密興趣濃厚;但他們又是如此的不同:弗洛伊德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他可以并且能夠克服一切障礙,他相信理性和意志的力量;卡夫卡則對什么都不抱希望,他相信“每一個障礙都摧毀了我”,他懷疑理性和意志的力量。沒有材料證明他們曾經會過面,但有材料證明卡夫卡的思想和創作曾經受到過弗洛伊德的影響。卡夫卡不經意地成為了弗洛伊德理論的論證材料;弗洛伊德卻因為不了解卡夫卡而終成遺憾。兩個同時代的偉人擦肩而過,留給我們的思考和啟示卻意味深長。
卡夫卡的朋友布羅德曾經說過,“不可否認,卡夫卡的情況可以作為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的一個案例。這種解釋太容易了。事實上,卡夫卡本人對這些理論是非常熟悉的,但并不很重視,只是把它當作事物非常粗略的和近似的圖像。他認為這些理論在細節上并不是很恰當的,特別是關于沖突的本質。”卡夫卡在日記中也的確證實了這一點,1912年9月23日,卡夫卡寫道:
在22、23日夜間,從晚上10點到清晨6點,我一氣呵成寫完了《審判》。由于一直坐著,我的腿如此發僵,以至都不能將它們從桌子底下移出來。當故事情節在我面前展開時,我處在極度的緊張和歡樂之中……夜里我多次將批評的重點落在我自己身上……寫作期間我的情緒是:高興,比如說,可以給布羅德的《阿卡狄亞》提供某些優秀的作品,當然也想到了弗洛伊德。
卡夫卡在創作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弗洛伊德,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卡夫卡對弗洛伊德及其理論是比較熟悉的。卡夫卡上大學時有一位專攻心理學的朋友奧托,他后來曾去維也納跟隨弗洛伊德繼續研究心理分析,并參加過弗洛伊德組織的“星期三晚間研討會”。卡夫卡與他的親密交往,無疑使卡夫卡增加了對弗洛伊德的了解。1899年奧地利作家卡爾·克勞斯創辦了《火炬》月刊,他在這份雜志上經常刊登攻擊弗洛伊德的文章,而這份雜志卡夫卡是非常熟悉的。卡夫卡當時還聽過克勞斯的有關弗洛伊德理論的講座。1913年,卡夫卡結識了一位朋友,名叫恩斯特·魏斯。他是一位猶太醫生,早年在維也納學醫時他便發現了弗洛伊德。他對卡夫卡的思想和創作有一定影響。
卡夫卡與弗洛伊德的個人身世和經歷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他們處在同一個時代,弗洛伊德生于1856年,比1883年出生的卡夫卡大27歲,死于1939年,比1924年去世的卡夫卡多活了42歲。弗洛伊德生于莫拉維亞一個小鎮弗萊堡,以后主要在維也納受教育和行醫;而卡夫卡除了在歐洲有過幾次短暫的旅行和逗留外,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布拉格。這些地方當時都屬于奧匈帝國,由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他們都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卡夫卡的父親經營紡織品、百貨;弗洛伊德的父親是一個羊毛商,只不過弗洛伊德很小的時候他父親的生意就敗落了。他們都是極端敏感的猶太人,接受德語教育,雖然都精通或熟悉多種語言,但他們的母語都是德語。當時歐洲的排猶主義情緒給他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但是,他們兩人卻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來對付或挑戰這種環境:卡夫卡越來越多地將自己封閉起來,越來越深地去探索自己的心靈和人類的靈魂;弗洛伊德則反而更加增強了他的反抗和叛逆情緒,并發憤圖強、有所作為。面對充滿敵意的外部世界,卡夫卡變得越來越內向;弗洛伊德則變得越來越外向。有趣的是,弗洛伊德的外在成功最終卻是通過對人的內心世界的探索而獲得的。
卡夫卡的生活和創作似乎給弗洛伊德的理論提供了一個絕好的例證,可惜弗洛伊德并不知道卡夫卡。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卡夫卡大概可以算得上最典型的“弒父娶母”病例了。卡夫卡在那封著名的致父親的信中袒露了他與父親的關系:“許多年后,我還一直保留著這種驚恐的想象:那個巨大的男人、我的父親,審判我的最后法庭,深夜里向我走來,毫無理由地把我從床上拽起來帶到陽臺上去──換句話說,這才是他所關心的,而我則是無足輕重的。”在“父子矛盾”中,母親似乎一直站在父親一邊。在這場爭奪母親的斗爭中,卡夫卡永遠是一個失敗者。在這種情況下,卡夫卡懷恨他父親,甚至想謀殺他父親,都應當是十分自然的想法。
更有甚者,年幼的卡夫卡本來就沒有獲得多少母親的關愛,而當他的兩個弟弟分別在1885年和1887年出生時,卡夫卡對這兩個闖來同他爭奪母愛的競爭者更是懷有強烈的怨恨。“卡夫卡一定希望他們遠離他的生活,并且,在最初的想象中他試圖通過魔法將他們謀殺。”事情后來果然按照他的想象發展,他的幻想變成了事實。格奧克1887年春天死于麻疹;亨利希1888年死于中耳炎。卡夫卡在無意中“謀殺”了兩個年幼的弟弟。弟弟的死給卡夫卡心靈留下了沉重的負罪感,以致于他從來都沒有覺察到,而多年后他在作品中卻泄露了他的這份壓抑情感,這也許就是他的作品中充滿了犯罪、贖罪和懲罰的原因之一。
在這種背景下,卡夫卡完全有可能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和學說,并將其灌注到他的文學創作中去。卡夫卡非常重視夢的意義和作用,他的某些有關夢的觀點與弗洛伊德頗有相同之處,盡管我們目前還沒有材料證明,卡夫卡曾經讀過弗洛伊德的《釋夢》。布羅德認為,“若沒有弗洛伊德,卡夫卡也許從來不會對自己的夢給予那么多的注意。”“卡夫卡似乎只對自己的夢感興趣。”1910年,卡夫卡第一次寫日記就記下了自己的夢。以后他在致女友菲莉斯的信中曾數十次談到夢,他說他幾乎天天夢見她。卡夫卡說過,“我們只是以自然性質的無法理解的高速度走過真正的事件之前或者之后經歷它們,它們是夢幻般的、僅僅局限于我們心中的虛構。”他說,他的小說《司爐》是“夢囈”,是“閉著眼睛的圖像”。另外,在創作中,父子矛盾一直是卡夫卡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卡夫卡曾計劃將自己的全部作品命名為“逃離父親勢力范圍的愿望”。總之,卡夫卡的所有小說幾乎都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論進行分析和闡釋。
但是,卡夫卡與弗洛伊德畢竟還有許多不同之處:弗洛伊德具有英雄氣概,卡夫卡更多的卻是弱者情懷;弗洛伊德試圖對非理性進行理性的分析和概括,卡夫卡則更愿意對理性進行非理性的描述和說明;弗洛伊德愛情幸福、婚姻美滿、家庭快樂,卡夫卡則愛情失敗、沒有婚姻、沒有家庭;弗洛伊德活著的時候就已看到他的思想和學說風靡世界,而卡夫卡活著時卻幾乎默默無聞;弗洛伊德活到83歲高齡,有6個子女,卡夫卡則只活了41歲,而且孤身一人。卡夫卡因為肺結核而早逝,弗洛伊德則因為癌癥而病逝,“結核病是源自病態的自我的病,而癌癥卻是源自他者的病”;作為結核病患者的卡夫卡在一點點回歸自我,而作為癌癥患者的弗洛伊德則在一步步走向世界。特別在信仰和宗教問題上,卡夫卡則堅決地抵制弗洛伊德的理論。卡夫卡反對弗洛伊德的“理性主義”,反對他所堅信的“知識就是力量”的信條,反對將信仰當作疾病來進行精神分析治療。凡此種種,均說明卡夫卡與弗洛伊德是有距離的,卡夫卡不可能不假思索地選擇和接受弗洛伊德,并且,卡夫卡的創作從來都不拘泥于任何理論,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弗洛伊德的理論。卡夫卡以獨特的思想和方式超越了他那個時代以及他周圍的所有作家,當然,他也超越了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