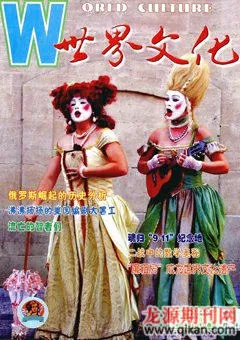吟唱羅馬帝國挽歌的愛德華·吉本
“偉大屬于羅馬”,羅馬帝國的榮耀牢牢地印在西方人的心靈深處。而記錄其興衰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以下簡稱《衰亡史》)縱橫千年、內容豐富、行文恣肆,不僅令史家為之傾倒,亦令文人騷客為之忘倦,風行世界數百年而不衰。正是由于這部歷史巨著,其作者愛德華·吉本(1737-1794)成為18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史學家,且躋身世界偉大的歷史學家之列。
吉本的家鄉在英國倫敦附近的普特奈鎮。他出身于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其母親生有7個孩子,吉本為長,他的5個弟弟、一個妹妹先后夭折。吉本雖僥幸避開死神之吻,卻難逃病魔糾纏,多次瀕臨死亡邊緣。吉本10歲時,其母過世,之后由姑媽撫養,不幸的童年和多舛的命運磨礪了吉本的意志,培養了他堅強的性格。吉本從小就酷愛讀書,求學孜孜不倦。他尤其對歷史感興趣,認為歷史是智慧之源。到吉本14歲時,他已通讀希羅多德、色諾芬、塔西佗等人的歷史名著,為日后自己的創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15歲時,吉本以優異成績進入英國著名學府——牛津大學,開啟了他人生的新紀元。起初,他因進入名校學習深造而自豪,但一年之后,卻發現自己并沒有學到什么東西。成立于中世紀的牛津大學完全被庸俗的環境所包圍,宗教氣息濃厚,旨在培養虔誠的教徒。后來,吉本在彷徨之中改信天主教,此改宗在牛津大學引起軒然大波,他也因此遭致開除處分。
吉本離開牛津之后,被父親送到瑞士,就學于加爾文教牧師巴維利奧,在此,他的人生之軌發生了重大轉折。在洛桑學習期間,吉本遍訪師友和圖書館,熟練地掌握了法文,廣泛閱讀了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等人的作品,還結識了法國啟蒙思想大師伏爾泰,進一步研究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許多古典名著,學業日有精進。在瑞士求學一年半后,吉本又再度皈依基督教新教。吉本在瑞士還遇到了他的白雪公主蘇珊·寇琇小姐。在他眼中,該女子“博學而不賣弄,談吐風趣,性情純真,儀態優雅”,不僅美麗,而且聰慧,乃難得之佳人。然而,吉本的父親卻以該女子貧窮為由,極力反對這門婚事,吉本孝敬其父,又無成婚的經濟能力,只有痛苦不堪的選擇放手。后來,蘇珊小姐嫁于法國財政大臣雅克·內克爾,因相夫有方而享譽上層社會。數年后談及這次戀情,吉本依然在無奈中無限唏噓:“作為一個情人,我只能嘆息;作為一個兒子,我只得服從。”這次戀情對吉本的影響極大,以致他抑郁不堪、終生未娶。
1764年,吉本初游意大利,親臨“露天博物館”——古羅馬廢墟,大發思古幽情。從他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羅馬留給他的印象:“我們在傍晚5時到達羅馬城。從米爾威亞橋上,我陷入了一場古代的夢中,直到后來被關卡官員打斷。”“我的個性不容易受到激動,而且我未感受到的激情,我一向不屑于偽裝。然而,即使25年后的今天,我仍難以忘懷,也無法表達,我首次抵達永恒之城時,內心的強烈悸動。”“經過一夜的輾轉難眠,我高睨闊步于廢墟講壇之上,剎那間,每個值得紀念的地點,羅慕路斯之蹤跡,西塞羅之音容,凱撒倒地之狀一一映入我眼簾。”對于一個古典愛好者來說,憑吊古羅馬遺址是一場非常具有震撼力的接觸。吉本在羅馬滯留期間,又數次造訪卡庇托山。卡庇托山是羅馬遺址中最重要的一個山丘,因而也更具吸引力。在其自傳中,吉本提到著述《衰亡史》的起因時說:“1764年10月15日黃昏時分,我佇立在卡庇托廢墟之中,聽到神殿傳來赤足僧侶的晚禱聲。我要為這座名城寫一部書的想法開始醞釀成形,這部書曾讓我著迷和幾乎花了我生命中的20年光陰。”
做一個大型系統的部署,遠非組裝一臺機器那樣簡單。起初,吉本對書的起迄和范圍均不明晰,創作的艱辛令他數次欲放棄先前的研究成果。后來,隨著思路的清晰和視野的開闊,他選定介乎枯燥的編年史和華麗的文告之間的文體,將整個羅馬帝國作為研究對象。吉本的設計遠超過先前的預設,以至后來他不無感慨地說:“我逐漸由期望到構思,從構思到計劃,由計劃到寫作,哪里會想到最后完成6厚冊,耗盡了我20年的歲月。”
吉本于1771年開始動筆構建其歷史巨著。第一章三易其稿,第二、三章二易稿件,此后就以“均勻輕快的腳步前進”。1776年第一卷出版后,立即收到了轟動性效果。吉本后來在《自傳》中回憶其暢銷盛況時說:“我不知道該如何描述這部著作的成功……第一版在幾天內即告售罄;第二版與第三版亦難以滿足社會需求;而書商的版權更兩度遭到都柏林盜版商的入侵。我的書出現在每張桌子上,甚至幾乎出現在每位仕女的梳妝臺上。”《羅馬帝國衰亡史》出版之前吉本在英國默默無聞,故該書的面世令英國藝文界有驚艷之感,一些主要文學期刊競相摘要刊登,以饗讀者。當時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賀拉斯·沃波爾贊譽吉本的史著為“一部真正的經典之著”。英倫三島的兩大史學泰斗大衛·休莫和威廉·羅伯遜也對《衰亡史》大加推崇,令吉本深受鼓舞。
學界的認可給予了吉本繼續創作的動力,1787年6月27日深夜,辛勤的吉本為他的煌煌巨著畫上了句號。他在記述完成這一長篇巨著的心情時寫道:“我擱下筆,在陽臺和樹木遮蓋的走道上漫步徘徊著,從這里可以眺望到田園風光,湖光山色。空氣是溫馨的,天空是寧靜的,月光的銀輝灑在湖面上,大自然萬籟俱寂,我掩飾不住首次如釋重負以及由此可望成名而感到的歡欣,但是,我的自豪之情迅即消沉,不禁悲從心來。想著我業已同一個伴我多年的摯友訣別了,不管我的著作將來的命運如何,歷史學家的生命必然是短暫和無常的。”翌年,吉本為之嘔心瀝血的《衰亡史》四、五、六卷同時出版,該著作的全部問世,博得了歐洲學術界的一片贊揚。亞當·斯密寫信向他祝賀,稱這部書使他可以列入當時歐洲文史書籍之首。吉本以近乎出世之心,全身心的經營自身獨創的史學大廈,以20年的辛勤汗水澆鑄榮耀之魅力光環。該書完成7年之后,吉本在倫敦逝世,終年僅57歲。
《衰亡史》全書六卷,作者在簡要回顧公元98年至180年間羅馬帝國的歷史以后,著力著述了公元180年至1453年的史事。全書囊括了后期羅馬帝國和整個拜占廷帝國的歷史事件,時間跨度一千三百余年,范圍涉及古代世界的三大洲,足可稱為體大思精的通史之作。羅馬帝國在18世紀的歐洲人眼中堪稱一代盛世,吉本獨具慧眼,選擇盛世之衰亡為題,最易引起讀者共鳴。吉本作為啟蒙時代歐洲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雖然僅著述一部史書,但卻為人類史學寶庫增添了一筆寶貴的遺產。如古奇所言:“吉本的著作在古代世界與近代世界搭起了一座橋梁;它迄今仍是各民族的通衢大道;并在羅馬帝國的其他建筑物都久已變成廢墟之后,仍然屹立著”。
理性主義思潮彌漫于整個18世紀的西方知識界,吉本正是這一時代的產兒。他崇尚理性、自由與歷史批判精神,無情的鞭撻羅馬君主,對他們的殘忍、迫害忠良和荒淫等丑事一一批判。即使如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之流的“明君”,他也毫不避諱他們的缺點,有時甚至稱他們為“暴君”。吉本的理性主義批判精神更主要地表現在反對基督教上,以辛諷手法譏嘲基督徒。如他在《衰亡史》十五章所講,基督徒“令瘸子走路,瞎子復明,病人痊愈,尸體復活,魔鬼遁跡,自然法則因此經常為了教會的利益而停擺”。吉本的作為在基督教界產生了強烈反響,也遭致基督徒的詆毀,但他對此并不在意,否則,他會在后來的寫作時寫得溫和一點。基督徒對吉本的書咬牙切齒,在聽到吉本的死訊后,基督徒莫爾小姐高興地說:“吉本的著作不知污染了多少靈魂,幸而上帝終于使他不再污染別人了”。
吉本借史學創作以自娛,以求批判與弘揚理性之用。但吉本深諳“無史學之真即無史學之用”的道理,論述嚴謹,絕不濫用歷史。他非常重視古典史料的運用,從小就閱讀和鉆研過希臘文與拉丁文的古典原作。在下筆之前,吉本已遍覽自奧古斯都至羅馬諸帝時期的文獻材料,并悉心研究古代文物,搜集古代貨幣,考證古代銘刻。他也重視17、18世紀史學家們所搜集的原始材料,并參照其他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他以如椽之筆,廣征博引,詳加考訂。我國著名羅馬史學者楊共樂教授曾對吉本所使用的大量材料做過認真的核對,發現吉本采用的材料皆有據可依,吉本的史學功底確實令人嘆服。迄今為止,《衰亡史》依然是一部權威之作,學界常將之與李維、塔西佗和普魯塔克等古典學者的著述相提并論,一再引征。
吉本在生前曾滿懷希望地預言,《衰亡史》一書將有“一個未來的命運”。該著作確實在他身后為其贏得極大聲譽。吉本建立在古典資料之上的生花妙筆使他的著作能夠雅俗共賞,不僅令史家為之傾倒,而且可以令一般讀者為之忘倦。《衰亡史》一書不僅擺在學者們的書齋里,而且也成為仕女們梳妝臺上的一道靚麗風景。如今,該著早已越出了英國的范圍,被譯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中文等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經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