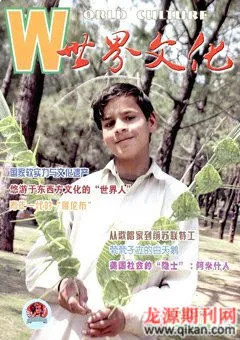悠游于東西方文化的“世界人”
任璧蓮(1955-)是繼湯亭亭和譚恩美之后風頭最勁的美國華裔女作家,迄今已出版長篇小說《典型的美國佬》、《莫娜在應許之地》、《愛妾》和短篇小說集《誰是愛爾蘭人?》,榮獲多種獎項,其中《典型的美國佬》還入圍美國文學三大獎項之一的全國書評小說獎。《愛妾》是任璧蓮的第三部長篇小說,被認為開啟了其“創作生涯的新階段”。
《愛妾》說的是美國波士頓郊區一個國際化的多種族家庭:1999年,這個家庭的男主人華裔電腦工程師卡內基·黃39歲;他的妻子賈尼·貝利(外號布朗迪,意即金發碧眼的白膚女子)45歲,有蘇格蘭、愛爾蘭和德國血統,是一家投資公司的副總裁;大女兒利齊15歲,是卡內基婚前收養的,可能是中日混血兒;二女兒溫迪9歲,是兩人婚后從中國領養的;老三貝利13個月,是他們的親生兒子。一年前,卡內基的母親黃媽媽去世,留下遺囑要把家譜傳給溫迪,但有一個條件:卡內基必須幫助一個中國親戚來美國照顧他的三個孩子。于是,46歲的老姑娘林蘭來到了黃家,布朗迪懷疑她是黃媽媽給兒子選的“愛妾”,從此生活不得安寧。小說的結尾非常出人意料:卡內基拿到家譜,發現林蘭是黃媽媽的親生女兒,自己只是養子。
任璧蓮在多次訪談中說,《愛妾》的創作靈感與她的兩個愛爾蘭裔-華裔混血子女有關。她的兒子和女兒都是白皮膚,五官相似,但兒子長著一頭黑色直發,常被外人當作是亞裔,女兒長著一頭金發,總被看作是白人,從女兒一降生,外人便常問她是不是任璧蓮的親生女兒,最令任璧蓮尷尬的是,每次她和家里的幫傭寄宿生、一個金發碧眼的德國女孩帶女兒出門,人們常常以為德國女孩是女兒的母親,而她是保姆。這個“積極的刺激因素”促使任璧蓮思考家庭這一概念中的種族和族裔因素、它對異族通婚的家庭造成的影響以及后者對它造成的沖擊。任璧蓮認為自己的家庭并非特例,美國社會正在出現越來越多的異族通婚的家庭、再婚后的混合型家庭、領養子女的家庭等非傳統家庭,它們所體現的家庭觀念與美國的立國理念是一致的: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的社會凝聚力不是血統,不是傳統的傳承,而是各種族、各族裔對于美國理想的認同,如果這個國家到處都是基于類似理念——主導的不是客觀因素和基因遺傳,而是家庭成員的自主選擇——而建立的新型家庭,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任璧蓮承認“美國實驗的這個新階段”極具挑戰性。換句話說,這些新型家庭模式是踐行美國理想的產物,從它們與傳統觀念相互沖擊的動態關系可以窺見美國理想與社會現實的矛盾與距離。在這一點上,《愛妾》與《莫娜在應許之地》一脈相承,區別在于前者關注家庭,后者著眼于個人。《愛妾》中,卡內基和布朗迪一手“創造……選擇”的家庭既存在跨種族婚姻,兩代人之間還存在跨種族、跨族裔的領養關系,在外人眼里,他們是“新型的美國家庭”,他們的混血兒子則代表著“美國的嶄新臉龐”。然而,在小說的結尾,布朗迪帶著貝利離家出走,這個家“在大部分時間里,分裂成兩個看上去符合傳統的家庭,有一分為二的清晰感覺。明顯失去了迷彩一般的絢麗色彩”。是什么原因使一個多種族的家庭分裂成兩個種族特征一致的家庭?
誠然,傳統家庭的一些問題也出現在這個非傳統的家庭里,比如正處于青春期的利齊叛逆心理很重,對母親尤其不尊重;溫迪接近青春期,也開始出現這個問題;卡內基和布朗迪都在外工作,與子女相處的時間有限;他們十多年的婚姻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平淡期;布朗迪比丈夫大6歲,已經出現近更年期的癥狀。但危害更大的是這個家庭特有的一些問題:其一,卡內基與布朗迪的異族婚姻自始至終遭到黃媽媽的反對,黃媽媽不能接受白人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也想阻止卡內基娶了白人妻子之后不被同化,她控制不了兒子,便安排林蘭來照顧三個孫輩,“這樣的話,孩子們最起碼會說中文,不像卡內基”。黃媽媽可以說是小說中種族意識最強的人物,非常看重族裔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兒媳婦在她的眼里不是兒子的愛人,更多的是一個種族符號“布朗迪”,即便兒媳婦會說中文,曾在大學學過一段時間的“東亞研究”專業,她的異己身份也無法改變。其二,由于黃媽媽罹患老年癡呆癥,“逆子”卡內基不僅意識到了自己深愛著母親,還產生了身份危機。黃媽媽遺忘得越多,卡內基失根的感覺就越強烈,母親逝世后,他發誓要學中文,在互聯網上了解中國文化,悉心保存母親的遺物,不顧布朗迪的反對仍執行母親的遺囑,甚至懷疑因為沒有娶一個亞裔女人為妻,他可能錯過了很多。從拒斥中國文化到拒斥做純粹的美國人,卡內基的文化認同幾乎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這使得他情不自禁地接近林蘭,卻拉開了與布朗迪的距離。其三,盡管布朗迪將利齊和溫迪視如己出,但在戴著種族有色眼鏡的外人眼里,她們看上去不像是母女,這使得兩個女兒產生情感認同的障礙,尤其在貝利出生之后,盡管布朗迪對她們的愛沒有變化,兩個女兒卻認為血緣關系決定了養母更愛親生兒子。歸根結底,這個家庭特有的問題都與族裔身份、文化認同、血緣關系等密切相關,隨著林蘭的到來,這些問題進一步激化,家庭成員之間開始分派結盟:誰最像誰?誰屬于誰?就連以思想開明自詡的布朗迪也為自己不能免俗感到懊惱。如果說她曾為收養異族女兒、挑戰世人的種族眼光而感到自豪,她也不禁為親生兒子遺傳了她的種族體貌特征而感到歡喜,她甚至發現“認為愛和價值觀也許比基因更重要,這是多么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啊!”在卡內基的生日晚宴上,布朗迪注意到“所有那些長著黑頭發的腦袋,只有兩個長著金發。……隨便什么過路人都會以為卡內基和林蘭是這家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而我和兒子貝利是客人”。黃家最終的分裂,罪魁禍首不是哪個人,而是社會話語和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種族范疇。如果家庭成員忽略彼此共同的人性,放大彼此的種族和文化差異,他們之間的愛和親情怎能持久?
在《愛妾》的結尾,心臟病突發的卡內基正在接受手術,布朗迪、林蘭、利齊、溫迪和貝利都守在候診室里。在“不光用眼、還用心在觀察”的溫迪眼里,對卡內基的愛和關切最終戰勝了彼此的族裔差異和紛爭,他們凝聚成一個整體,變成了患難與共的一家人。當得知卡內基脫離了生命危險時,“我們全家人一起不停地歡呼”,但這種歡樂能否持續呢?溫迪沒有給一個明確的答案,只是注意到“突然之間房間怎么變得這么黑暗”。顯然,與《莫娜在應許之地》頗為樂觀的結尾相比,《愛妾》結尾傳達的信息要含混得多。對于非傳統家庭能否完全排除種族和族裔因素的干擾,任璧蓮也許缺乏十足的信心和把握吧。在任璧蓮看來,小到家庭,大到美國這個國家,種族和族裔差異都是舉足輕重的問題,如果讀者能夠透過黃家的經歷思索美國的種族和族裔問題,她的寫作意圖也就實現了。
在《愛妾》中,任璧蓮對敘述技巧進行了大膽的實驗,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卡內基、布朗迪、林蘭、利齊和溫迪交替擔任第一人稱敘述者,常常是你一言我一語,你一段我一段,一個人的話語最多能占上四五頁,偶爾會有十頁。任璧蓮把這種特殊的敘述方式形容為“一家人接受長時間的集體心理治療,只是沒有治療師,而且每個人都有自說自話的自由”。由于《愛妾》融合了莎士比亞戲劇獨白和小說的元素,任璧蓮稱之為介于戲劇和小說之間的雜合文類,在一定意義上形象地再現了《愛妾》中雜合的種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主題。另外,任璧蓮采用第一人稱敘述者,是因為用這樣深入內心的方式塑造人物,“在探討種族和族裔屬性的同時,能夠牢牢抓住每個人物的個性特征……如此近距離地追蹤人物的視角,我也許能夠超越當代小說的常規,塑造出更為豐滿的非主流人物,同時又不會失去主流讀者的共鳴”。而如此多的敘述者可以體現現代生活的紛繁復雜,作為作家,任璧蓮愿意傾聽所有不同的聲音和看法,她的這一考慮與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值得關注的是,《愛妾》的場景大多數設在美國,但繼短篇小說《鄧肯在中國》之后,任璧蓮在這部長篇小說穿插了不少中國故事。第一部第六章“溫迪”完全可以改稱為“卡內基、布朗迪和利齊在中國”,講述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一家三口轉道北京去南方的一座小城市領養溫迪的所見所聞,其中還有布朗迪對大學時在香港學中文的一段插敘。但與鄧肯不同的是,黃家三口人是名副其實的游客,他們為長城等北京的景點名勝而傾倒,壯著膽子品嘗蛇、鰻魚、兔耳朵等中國美食,但難以忍受中國人多、擁擠、酷熱、衛生條件差等生活狀況。令他們最不能忘懷的是在帶著溫迪回賓館的路上遭遇的車禍:卡內基出于人道主義,想送傷者去醫院,向導和司機卻不愿惹麻煩,怒火中燒的當地下崗工人掀翻了他們乘坐的車輛,后來他們才得知這其中夾雜著民族主義、仇富主義的情緒。從布朗迪的視角來看,在中國的經歷的確具有“異國情調”。但表面的“異國情調”背后,是任璧蓮借助自己的跨文化視角對中美兩國文化的批評:與中國“第三世界”的生活條件相對照的,是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美國人的“養尊處優但意志薄弱”;與黃家人遭遇的車禍相對照的,是獨立島上令杰布喪生的火災,而中國下崗工人的民族主義、仇富主義情緒與獨立島上那些白人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相比,誰更該遭到譴責呢?除此以外,大部分的中國故事由林蘭給利齊和溫迪講述,后者再轉述給布朗迪和卡內基。林蘭大多講述自己和親戚朋友的真實經歷,還有關于孝順等德行的中國文化故事,按溫迪的說法,“有些故事是正常的,但很多都很怪異”,比如扼殺女嬰、文革迫害等。任璧蓮非常清楚,盡管這些故事都是她親耳聽來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主流社會的東方主義話語,置林蘭于他者的處境:“當我的虛構牽涉到一種我熟悉但并不完全屬于我的文化時,我的心安理得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說,我意識到林蘭所講的一些故事使得她成了主流讀者眼中的‘他者’;作為一個作家,知道自己把她塑造成這個樣子,我會感到非常不安”。換句話說,任璧蓮把這些故事放進小說里,出發點不是為了滿足主流讀者的獵奇心理,而是直面中國歷史的同時,對美國主流讀者的心理稍做揶揄。布朗迪一向講究“政治正確”,竟然到了忌諱“怪異”一詞的地步,林蘭講述的“怪異”故事被她說成是“迷人的”故事,無怪乎利齊總說布朗迪“虛偽”。任璧蓮反異國情調和東方主義話語的立場始終如一,只是與以前相比,她的策略有所變化,不妨稱之為表面逢迎,暗里批判,而且,她的批判往往是雙向的。
2002年,任璧蓮來到北京師范大學做富布賴特訪問學者,這是她生平第一次主動尋求來中國體驗生活的機會。任璧蓮視這次中國之行為“尋根之旅”,坦言她“作為一個作家的權威(已經樹立),它顯然不是源于我對中國的了解”,因此她無須擔心主流讀者會質疑她的美國屬性,有了這樣的安全感,她可以放心地訪問中國,學中文,了解家族的歷史,創作中國故事。這樣的“尋根”無疑能使任璧蓮更新她的知識儲備,最大限度地擴展自己的跨文化視野,背倚中美兩種文化獲得更寬廣的話語空間,這對她的創作生涯有百利而無一害。在《愛妾》中,任璧蓮讓筆下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物跨越國界,置身于不同世界之間探討文化差異和族裔身份,這既符合全球化的世界現狀,也能幫助作家本人以悠游于東西方的“世界人”身份,客觀公正地審視不同的文化。由此我們也許可以瞥見任璧蓮未來作品的走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