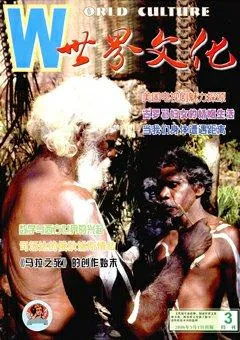永遠的夢露
夢露的誕生,使男人對女人多了一種夢幻。她的美艷激起男人的不是邪惡,而是憐愛;不是占有的沖動,而是朦朧的快感。夢露屬于那種世所罕見的,可將男人的低級欲望變成審美通感的女人。
然而1962年8月5日,夢露不再是夢露,她只是停放在美國西海岸洛杉磯的一間陳尸所的一具女尸,依然美麗卻冰涼僵硬。于是,人們的所有關于夢露的詩意想象,瞬間即被這具女尸無情地拉回塵世。
死亡與夢露聯系在一起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她的周身溢滿了大自然所賜予的厚愛,只要你葆有一顆健康的愛美之心,無論你是男是女,或老或幼,面對夢露(即使是照片)你都不會漠然視之。她是那種我們無意間在某個場合見過一面而終生不忘的女性。這樣的場合包括掛歷、畫報、影照、書刊。世界公認她象征了一種高級性感,而引起性感又并不由于裸露。
她因此而成了美麗的焦點。她的姿色是一種自然資源,總會吸引形形色色的開發者。她最初不知道珍惜。因為孤苦無依的日子實在太久了,像一片瑟瑟抖動無處尋根的落葉。夢露既是遺腹女,又是私生女。母親長年住在精神病院。幼年始寄人籬下,遭人歧視,甚至有一次被奸污。8歲時逃進孤兒院當洗碗工。她16歲那年,為離開孤兒院的非人待遇而同21歲的飛機工人吉姆·多爾蒂結婚。婚姻的不幸使她曾試圖自殺。為生計她當過攝影模特,后長期被好萊塢的制片人把她的美色當作搖錢樹。他們專門安排她在一些電影里扮演淫亂放蕩的女人角色,以她的美貌傾倒了各國觀眾,也引起了巨商、政客、名流甚至美國總統的注意。她知道許多人只對自己的性感表演有興趣,這使她漸生厭倦。一個晚上,她回憶拍攝影片《安娜·克里斯蒂》的情景時深感難過:那樣的表演她覺得皮膚似乎在脫落,內心的感情也似乎裸露于世。
有多少美艷就會有多少騷擾。這騷擾不僅來自好色之徒,社交界、新聞界也不肯輕易地放過她。1954年歲末,整個好萊塢的著名人士都出席了慶祝《七年的思考》拍竣晚會,這意味著他們最終接受了作為影星的夢露。而這晚,夢露卻從一片贊揚聲中隱去,套上黑色假發套,戴上墨鏡,更名改姓“逃”到了美國東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農場,與她的女友艾米·格林共度圣誕節。電話不斷地打來又被不斷地拒絕。之后,夢露和艾米如同兩個惡作劇的小女孩兒一般竟樂得在地毯上打滾。“名聲對我來說猶如曇花一現,那不過是僥幸得來的東西……當它一旦逝去,我已體驗過這只是一種輕浮而易變的東西,我并不靠她才能生活”。清醒如夢露者或許已經感到,對于她,名聲日增恰恰意味著安全感的遞減。
遺憾的是,超凡的美艷常常置她于諸多誤解之中。不少人僅僅視她為“性感明星”而拒絕給予理解,想當然地認為這樣的艷星只需要展示千嬌百媚即有市場,表演才能與之無涉。其實不然,只看美國“影星之家”創始人李·斯特拉斯伯格的評價就可以了:“我曾和上千個男女演員一起工作過,但我感到其中只有兩個人是出眾的,第一個是馬龍·白蘭度,第二個是夢露。”她出身貧寒,無緣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她卻表現了強于他人的自學熱情。她受益于許多書籍,包括傳記、歷史、詩歌。為中國讀者熟知的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一書也曾伴她度過旅途時光。閑來她還寫詩。就我有限的閱讀看來,她的詩歌水準不具多深的造詣。但意義顯然在于:從貧民窟、孤兒院走來的夢露,尚未被災厄頻臨、險象四伏的生活所扭曲。
夢露又是那般弱小。她坦言她“十分害怕孤獨地面對一切”,“在這個世界上我最需要的就是愛”。但很多權貴、要人僅僅將她視作獵艷的玩物,一旦釀成桃色新聞而公諸于眾便以犧牲夢露為代價潔身遠行。那一段日子她患了嚴重的抑郁癥,夜里需服鎮靜劑方能入睡。終于在36歲時的一個子夜,她不明不白地辭別了人世。她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團。美應該是永恒的,美的毀滅卻是那樣無奈。大自然生命規律難道不應該是存優汰劣嗎?
奇異的是,夢露并沒有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早亡成全了她的不衰魅力,說這話不免有些殘酷。倘若今日依然健在,夢露該是耄耋之年。請設想,那迷人的滿頭金發變得枯黃,“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雙眼昏花渾濁,鮮潤欲滴的嘴唇蒼白干澀,豐滿挺拔的胸部松弛萎縮,活潑歡快的女兒態已是垂垂老矣。而這一切尚未發生,夢露便凝固了永恒的風韻。
紅顏薄命,幸或不幸,誰人說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