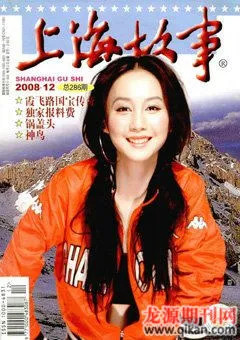神鳥
一、尋找
陳昊今年二十八歲,卻已是全市小有名氣的畫家了,有幾幅畫曾被幾家有名的博物館以近百萬高價收藏,最近又要出國深造。很多人對這位風光無限前途無量的青年畫家羨慕不已,而陳昊自己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目前正陷入一種從未有過的苦悶與煩惱之中,這種苦悶與煩惱持續了近三個月,已經到了令他幾乎難以忍受的程度。
事情的起因得從三個多月前說起,一天晚飯時,春風得意的陳昊端起酒杯對父親說:“老爸,我現在的名字也算叫得響了,作為您的兒子和學生,我還沒給您丟臉吧?”父親凝視了他一會兒緩緩地說:“你沒給我丟臉,但我對你還不滿意。”“為什么?我哪里還做得不夠?”陳昊詫異地問。
“我給你看一件東西。”父親說。
父親拄著拐杖站起身,陳昊跟著父親進了書房,只見父親從一只又笨又舊的老木箱子底翻出一幅舊畫,陳昊一看,這是一幅鉛筆速寫,畫的是一只在高空盤旋的大雕,可這雕只完成了頭部和一只翅膀,其余部分只是一個大致輪廓。“爸,這是你畫的?為什么只畫了一半就不畫了?”陳昊不解地問。
父親拍了拍自己右腿的殘肢,凝重地說:“你們只知道我這腿是當年在青海下鄉當知青時受感染鋸掉的,可你們都不知道這感染是怎樣來的,我今天就告訴你吧,要不是這畫上這只雕,我丟掉的就不只是一條腿,而是一條命。那是一個秋天的上午,我獨自一人在草原上畫這只在空中盤旋的雕,我被它那種空中王者的風范和孤傲的美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全神貫注地畫,完全沒注意到一頭惡狼正悄悄地從后面向我靠近。當我感覺到要起身逃跑時為時已晚,狼離我已只有幾米遠,我拼命地跑,可還是被它一口咬住了小腿,就在我絕望地掙扎時,只見一團黑影從天而降,一看,正是我剛才畫的那只雕俯沖而下,它尖利有力的雙爪一下抓住狼,巨大的翅膀激起一股疾風,一轉眼就把那狼抓到了空中,狼掙扎著掉了下來,可還沒來得及跑就又被這雕再次抓住,這次它啄瞎了狼的眼睛,撕破了狼的肚皮,然后抓起它展翅而去。我的腿因被狼咬感染而鋸掉,但這只雕救了我的命,只可惜,我沒有把它畫完,你要是真正能畫好一只雕,我就滿意了。”
陳昊聽完父親的講述,驚訝之余深為父親的那段遭遇和那只巨雕感動。他問:“這是種什么雕?”
“金雕,青海金雕!”父親莊嚴地說,“這是藏民心目中的神鳥,也是我心中的神鳥。”
“神鳥?”陳昊看著父親說起這鳥時那莊嚴肅穆無比崇敬的表情,心中不禁產生一種疑問,不就一大鳥嗎?有什么神的?
陳昊只用了兩天的時間就畫完了一只雕,當他把它遞給父親時,父親只瞟了一眼便毫不猶豫地把畫撕了。接下來的兩個月,陳昊又畫了幾十幅雕,全都變成了父親紙簍里的廢紙,這讓陳昊無比沮喪,他費盡周折,好不容易通過朋友的朋友看到了一只金雕標本,花了一周的時間,陳昊使盡渾身解數把這雕畫了下來,拿給父親看,父親看了兩眼,不屑一顧地說:“是只雕,但是只死雕。”說完又很干脆地撕了這畫。
我一堂堂畫家竟畫不好一只雕?這是種什么樣的雕?陳昊上網一查,得知金雕別名鷲雕,潔白雕,紅頭雕,隼形目,鷹科,雕屬,是雕屬中體形最大的一種。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它是墨西哥國鳥,也曾是古羅馬的權力象征。由于日漸稀少,它已被列入世界瀕危物種紅皮書。
無比郁悶的陳昊決定親自去青海,見識見識這曾救過父親一命,讓父親無限崇敬而自己又始終畫不好的大鳥究竟神在哪里。
于是,陳昊自駕車幾天幾夜千里迢迢來到青海。一踏進草原,他就被草原的遼闊雄偉深深吸引了,他抬頭仰望天空,只偶爾飛過幾只小雀,哪有什么金雕,他又在草原上遛達了一整天,連金雕的影子都沒見到一個。這不免讓他大失所望,他原以為在草原上隨便哪里一抬眼就能看見空中盤旋的金雕,沒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兒。于是,回到酒店后他便向服務員打聽哪里能見到金雕,可沒想到問第一個服務員時不但沒得到答案,反而遭來白眼。他又問第二個,這第二個沒好氣地說:“我都多年沒見了,別說你。”他問為什么,對方卻說這就要問你們自己了。陳昊搔著頭又問第三個服務員,這服務員問:“你找金雕干什么?”“畫畫,我想畫只金雕。”陳昊說。“哼!畫畫?千里迢迢跑來只為畫只金雕?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喲。”
陳昊接連碰了幾鼻子灰,弄得他莫名其妙。這些人都怎么啦?我不就是想看看這鳥畫畫這鳥嗎?怎么這么不友好?嘿!我就不信這邪了,只要這草原上還有金雕,我就一定要把它找到。陳昊一賭氣,買了一大堆食品和水扔進車里,開車進入茫茫草原。可轉了大半天,仍然沒看見一只雕,難道這雕都死絕了?
看看天色漸暗,陳昊正尋思這夜是呆在車里還是找個地方住下時,就看見遠處有個不大的村落,他徑直把車開過去,看見有一所“雄鷹希望小學”,便把車開了進去,熄了火下車正四下張望時,就見一位四十歲上下的教師模樣的藏族男人從一屋里走了出來,陳昊忙上前伸出手說:“你好,你是這兒的老師吧?我是路過這里的旅游者,我叫陳昊,天要黑了,我想在你們這里找個地方住一夜可以嗎?”
“你好。”這人握著陳昊的手,用略顯生硬的普通話說,“我是這兒的校長巴桑,如果你愿意,就住我家吧。”巴桑說著把陳昊迎進屋,熱情地招待陳昊吃了晚飯后,兩人聊天,陳昊又問在哪里能看到金雕。
“你——你是干什么的?你找金雕干什么?”巴桑臉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一雙機敏的眼睛警惕地盯著陳昊問。陳昊一看巴桑對自己懷疑的態度,索性把自己的身份證、名片、工作證、駕駛證一股腦兒掏給巴桑看,又講了父親被金雕救命的事和自己來草原尋找金雕的原由。“巴桑大哥,你能幫我找到金雕嗎?我會付給你報酬的。”陳昊最后懇切地問。
“噢——原來是這樣。”巴桑再次握住陳昊的手說:“在藏民的傳說里,金雕是神鳥,它從不會在人間留下尸體。當它知道自己將死時,會竭力飛向高空,直到被閃電劈碎;或者飛向太陽,直到被熱浪融化。我為你們父子感動,我很愿意幫你,可是,就連我這樣一直生活在草原上的人,這些年見到金雕也成了一件稀罕事了。”
“這又是為什么?”陳昊驚問。
“盜獵!” 巴桑憤怒地說出這兩個字,同時一拳砸在木茶幾上,把一碗酥油茶都震翻了,陳昊驚異地看著在桌上流淌的油茶,巴桑憤怒的臉上帶著沉重的悲涼。陳昊問:“盜獵盜得連你們都難見金雕了?有這么嚴重嗎?這金雕很值錢嗎?”巴桑說:“本地盜獵者賣出一只金雕也就五六百元,聽說如果偷運到廣州,在酒樓里能賣到上萬元,如果做成標本,聽說在有些地方可以賣到二十多萬元。在草原上空飛了千萬年的神鳥,就這樣成了那些貪婪者桌上的一道菜,成了有錢人屋內的一件裝飾品。我們祖祖輩輩崇拜的神鳥,眼看就要絕種了,唉——”巴桑說到這里時,雙眼閃著淚光。陳昊這才明白那些服務員為什么那么對他,原來把他當成買金雕的人了。他被這位純樸的藏族大哥對金雕的感情深深地感動了,這更堅定了他要親自看看金雕的決心,他誠懇地說:“巴桑大哥,請你務必幫我見到金雕,我非常想親眼看看這神鳥,看看我能為保護它做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陳昊和巴桑各騎一匹馬出發了,陳昊讀大學時就學會了騎馬,可在真正的草原上馳騁還是第一次,從鋼筋水泥的大都市來到寬廣碧綠的大草原,他感到心曠神怡,但他更期待的是能早點見到讓他神往的金雕。
巴桑帶著陳昊跑了好幾個他原來常見到金雕出沒的地方,可都撲了個空。“唉——難道這神鳥真絕種了?”巴桑嘆著氣帶著陳昊向另一個地方馳去,當他們來到幾個小土丘前不遠處時,巴桑突然指著天空興奮地喊道:“看,快看!”陳昊抬眼望去,見空中有兩個黑點由遠而近盤旋而來,他忙取出望遠鏡一看,果然是兩只金雕,它們各沿一圈狀線在空中滑翔,巨大的雙翅時不時地輕輕舞動幾下,自由地駕馭著氣流,在空中劃過優美的弧線,動作優雅無比,它們的羽毛在陽光下閃著金光,加上那雙俯視地面的銳眼,那俯瞰一切的姿態,儼然就是無可匹敵的空中王者。
陳昊完全被這兩只金雕的氣度征服了,他一邊嘆道:“王者!神鳥!”一邊忙不迭地取出照相機拍照,拍了十多張后,他又取出畫板和畫筆,準備來個速寫。正當陳昊剛落下幾筆時,他正畫的這只金雕突然一個俯沖直沖而下,消失在土丘后面。
“它下去捕獵了。”巴桑說。陳昊只得轉而畫另一只金雕,畫著畫著,忽聽巴桑大叫一聲:“不好!”就上馬急馳而去。陳昊扔下畫板,也翻身上馬跟上去,他不知道巴桑叫的“不好”是什么意思,只是一種不祥之感罩上心頭。
二、拯救
陳昊沖上土丘時,只見巴桑已沖了下去,正追趕著一位騎手,這騎手手上提著一個大編織袋。陳昊瞬間明白了這人一定是個盜獵者,編織袋里可能正是他抓獲的剛才那只金雕,他怒從心頭起,揚鞭催馬也追了上去。
陳昊和巴桑相隔十幾米一前一后向前追,可那盜獵者的馬真是匹良馬,把兩人漸甩漸遠,巴桑憤怒地吼叫著“停下,你這可恥的賊!”突然,盜獵者從馬背上的吊袋里抽出一支獵槍,回身就向巴桑開了一槍,這槍沒打中巴桑,可巨大的響聲把巴桑和陳昊的馬嚇得驚跳起來,兩人都被驚馬摔到地上,只能眼睜睜看著盜獵者揚長而去。
“唉——!”巴桑看著盜獵者遠去的背影捶首頓足,陳昊也只能無奈地嘆氣。他看見另外那只金雕在空中尾隨盜獵者一段距離后也無奈地沖向高空,振翅而去。
兩人躺在草地上,陳昊問:“巴桑大哥,你怎么知道有人在盜獵?”巴桑說:“一般金雕俯沖下去時,一定是發現了地上的獵物,比如野兔什么的,它抓住獵物后馬上會帶著獵物重新飛回空中,不管能不能抓住獵物,這時間都不會太長。盜獵者把逮住的野兔拴在捕獵鐵夾上,金雕只看見野兔,不知道那藏著的鐵夾,下來抓野兔時就會被鐵夾夾住。剛才我感覺到這金雕下來的時間過長了些,突然就想到了盜獵者,果然是這些喪盡天良的盜賊!”陳昊說:“金雕是國家的一級保護動物,又到了這種瀕臨滅絕的地步,我們不能這樣眼看著這只金雕被盜去,一定要設法救出它,巴桑大哥,你有沒有辦法?”巴桑站起身環視了一下說:“我生在草原長在草原,小時跟爺爺放牧時跟他老人家學過足跡追蹤,走,我們去找這盜獵者,一定要救回這只金雕。”
陳昊再次翻過土丘,回到剛才那地方撿起扔下的望遠鏡和畫板,兩人便牽著馬,沿著剛才那盜獵者逃跑的足跡追蹤而去。巴桑一會兒騎馬一會兒步行,一會兒又俯下身仔細地辨別草地上的足跡。
黃昏時分,兩人終于來到了一個帳篷附近,這時,他們看見剛才那盜獵者正從帳篷里出來,提著一瓶酒,邊喝邊唱地來到一叢草邊撒尿。巴桑悄悄地摸到他身后,突然從背后扭過他一只手,厲聲說:“你這混蛋,敢盜獵金雕?還向我開槍!把金雕交出來放了,要不然送你去派出所。”這盜獵者嚇得酒瓶掉在地上,巴桑又指著陳昊說:“這是國家林業部派下來調查金雕的陳科長,你要是不交出金雕,他一個電話你就馬上進大牢。”
這盜獵者嚇得趕緊從兜里掏出一把鈔票扔在地上說:“我——我把金雕賣給收羊毛的劉老板了,這是賣得的六百塊錢,我——我錯了,求領導寬恕。”
“你——!就為六百塊錢,你就敢盜獵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劉老板住哪兒?你馬上帶我們去,這樣還可以減輕你一點罪,要是找不回那只金雕,哼!”陳昊就勢裝起大科長的架勢,說罷看著巴桑笑了笑,心說你一下就給我封了個林業部的科長?
這盜獵者把巴桑和陳昊領到一個小鎮上的一家羊毛店門口時,趁二人不注意溜了。這時天已黑盡,他們便也沒去追他,兩人正商量用什么辦法進去探個虛實時,就聽里面傳來一陣喧鬧爭吵聲,巴桑把馬拴在旁邊一電桿上,然后輕輕一推門,門沒關緊,于是兩人便進了這屋,這是一個只放了幾個凳子和一些雜物的小間,穿過這小間,才是一個寬大的院子,只見院里亮著電燈,有三個藏族老人正和一中年漢族男人大聲爭執, 一老人大聲說:“劉老板,這是神鳥,你不能殺。”劉老板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花錢買來的鳥,是我的鳥,我殺我的鳥,又沒殺你們的鳥,你們憑什么來管我?”這話把藏族老人問得啞口無言。
陳昊看見了木籠子里關著的那只金雕,他突然站到那藏族老人身旁,大聲對劉老板說:“金雕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你購買金雕已經犯法了,你要是再殺這金雕,你的罪可就不輕了,違法犯罪的事人人都可以管,金雕是藏民的神鳥,憑法憑理這些老人都可以阻攔你殺這金雕。”
“你們——你們是什么人?敢到我家里來對我指手劃腳。”劉老板指著巴桑和陳昊說。“哼!”陳昊鄙視著劉老板不開腔,巴桑說:“這是國家林業部派來的陳科長。”
“林業部?陳科長?”劉老板大吃一驚,“請坐請坐,失敬失敬。”他連忙又讓坐又敬煙,然后對三個藏族老人說:“幾位老人家請回吧,我錯了,明天一早我就把這金雕放了。”藏族老人臨走時看著陳昊說:“唉——你們早就該來了。”
陳昊接過劉老板的一支煙點上,就勢裝起科長的姿態來到木籠旁仔細地觀察起這只金雕。這是一只成年的巨大的金雕,雖然它的雙腳被鐵絲捆在籠底的木條上,雙翅也被鐵絲拴在一起,但它暗褐色的頭卻高傲地昂著,當它轉過頭來看著陳昊時,陳昊驚呆了,只見它的眼珠又黑又亮,褐紅色的瞳仁像高貴的紅寶石,純潔透亮得不含絲毫雜質,眼里自然地透出一股俯視萬眾蒼生的王者之氣。如果它的翅膀展開,絕對超過兩米。它灰色的喙如同彎刀的一角,顯示出年輕與力量。它脖子上一圈金色的毛,在栗色的羽翅襯托中,盡顯王者風范。陳昊此時才突然明白為什么父親說他照著標本畫的那幅金雕是死雕,原來缺少的就是這股活生生的王者之氣。
巴桑看陳昊看呆了,他指著金雕的眼睛說:“藏人認為只有它的眼睛敢直視太陽,它是神鳥。”陳昊情不自禁地說:“我完全被它征服了,這是真正的神鳥。”
劉老板在背后突然說:“看來陳科長是第一次見這種鳥,請問陳科長是林業部什么部門的科長,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工作證呢?”陳昊回身看了看劉老板皮笑肉不笑的樣子,知道麻煩要來了,他伸手到衣袋里掏了掏,然后白了劉老板一眼說:“對不起,我的證件和行李都放在這位巴桑大哥家里了,我先把這鳥帶走,明天再把證件拿來給你看。”他說著就去搬木籠。
“哼!在我面前裝,還嫩了點,伙計們,上!”劉老板說著一揮手,突然撲上來三個壯漢,三下五除二便把陳昊和巴桑像捆粽子一樣結結實實地捆在兩把椅子上。“你——你敢捆我,你是不是想坐班房了?”陳昊大聲喝斥道。“我坐班房?哈哈哈——”劉老板大笑,“你說你是林業部的科長,可你根本就拿不出證件來,你這是冒充國家干部。你們未經允許就進到我家院子里來,這是私闖民宅。就憑這兩點我不能捆你們?天亮了我就把你們送到派出所去,看看誰坐班房,我這是見義勇為,我還要得獎呢,哈哈哈——”劉老板和他的三個伙計笑得前仰后合。
“你們——”陳昊剛吐出兩個字,劉老板一揮手,一伙計抓過兩塊破布,一人一塊把他和巴桑的嘴塞上。“你們兩個看好了,要是你們再跟我作對,我就把你們像這只鳥一樣做成標本。”劉老板說著叫伙計拿來一把榔頭和幾根長長的鋼針。
劉老板打開木籠,把捆住金雕雙腿的鐵絲從木條上解下來,把它抓出來,然后讓一個伙計抓住金雕仍被鐵絲捆住的雙腿,讓另一個伙計用兩塊木板夾住它的頭,陳昊看著這金雕掙扎了幾下,但雙腿和翅膀被捆住,頭被夾住,已完全動彈不得,唯一能動的是它那兩個眼球,陳昊看見它驚懼的目光里仍不失王者不屈的桀驁。接著,劉老板左手拿起一根鋼針按在它的頭頂,右手揮起榔頭“梆梆”兩下便把這鋼針釘進了它的頭顱,它的頭拼命地擺了兩下,又被木板緊緊夾住。“你還不服氣?”劉老板說著又拿起一根鋼針,“梆梆梆”幾下又釘了進去。為了做成盡可能完好的標本,盜獵者都用這種殘忍的方式殺死金雕。
看著這殘忍的一幕,陳昊和巴桑肺都要氣炸了。他們喊不出聲,但他們都同時哼著掙扎著帶著椅子往前移。劉老板使個眼色,兩伙計過來按住了椅子。劉老板把垂下了頭的金雕往地上一扔,哈哈大笑道:“不就是一只鳥嗎,又不是你們的親爹親娘,你們急什么呀?你們還口口聲聲說這是神鳥,神鳥能讓人逮住?神鳥連扎兩根針都經不起?笑話!”
劉老板說完,叫伙計從屋內抱出一箱啤酒,幾人坐到屋檐下喝酒抽煙。陳昊和巴桑看著躺在地上的金雕也只能無可奈何地搖頭。大約過了十多分鐘,陳昊突然發現這金雕又活動起來了。先是它的頭動了動,接著翅膀也動起來,甚至還試圖撲騰了幾下。“嗯—嗯—”陳昊哼著看著巴桑朝金雕揚揚下巴。巴桑一看,也激動地哼了起來。
劉老板也發現金雕在動,他走過來,一把抓起它的頭,“梆梆梆”又釘進去一根鋼針。“看你有多能耐!”他說著扔下再也不動的金雕過去繼續喝酒。陳昊看著劉老板的背影,恨不能雙眼像火焰噴射器一樣噴出兩道火把這畜生燒為灰燼。
半夜時分,劉老板進屋睡覺了,叫兩個伙計喝著酒輪流看守著陳昊和巴桑,兩人趁看守打瞌睡時悄悄把椅子移近,用椅子背的棱角磨繩子,凌晨時分,陳昊的繩子竟被磨斷了,他扯下兩人嘴里的破布,又悄悄解開捆巴桑的繩子。就在這時,他無意間又看了一眼地上的金雕,這一看,把他驚得差點跳了起來,他看見這只金雕竟然又動了起來,而且還掙扎著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它那寶石般的眼睛里竟又閃起了生機。“天啊!”陳昊和巴桑同時小聲地驚嘆出聲。這一驚嘆,驚動了打瞌睡的伙計,他起身走過來。陳昊朝巴桑使了個眼色,一下撲上去抱起金雕就往外沖,巴桑一拳打翻追上前的那伙計,也隨后沖了出來。
兩人奔到電桿旁,解下繩子,翻身上馬,疾馳而去。
三、絕食
陳昊一手抱金雕,一手握韁繩,和巴桑一起風馳電掣般回到巴桑的學校。陳昊看著金雕頭上的三根鋼針,不敢輕易取出,巴桑忙找到一名獸醫,獸醫也沒有把握取出鋼針后金雕不會死。巴桑說離這里五百多里外的市里有家野生動物救護中心。陳昊一聽,馬上抱著金雕上了車,臨走時他突然想起那劉老板,他叫巴桑打110報了警。
三個多小時后,陳昊把金雕送進了救護中心,工作人員看了金雕又聽陳昊介紹了情況后,全都驚得伸長了舌頭,馬上找來了高級獸醫師,獸醫師說這是一只成年雌雕,他先對金雕頭部進行X光透視,之后小心翼翼地取出鋼針又上了藥。
救護中心同意陳昊留下來和工作人員一起照顧這金雕。陳昊非常高興,他為這金雕取名“貴妃”,他要跟 “貴妃”親密接觸,要幫它把傷養好,要為它多畫幾幅像,然后再親手把它放回草原,讓它重新在長空搏擊。
可是,令陳昊萬萬想不到的是他的計劃第一步就遭遇了挫折,“貴妃”竟拒絕他給它喂食,當他把切成小塊的瘦肉遞到它嘴邊時,它轉轉眼珠看了看他,竟轉開了頭。陳昊把肉轉過去,它又把頭轉過來。來回多次它就是不吃。陳昊盯著它的眼睛說:“親愛的,那些喪盡天良的人害你,我沒害你呀,是我救了你,你就給我個面子,吃吧。”“貴妃”似乎聽懂了他的話,它不再轉過頭,可仍然不吃他遞上的肉。陳昊想可能是這豬肉不對它的口味,和工作人員商量后又專門弄來兔子肉,可“貴妃”仍然拒絕進食,工作人員又找來幾種金雕喜歡的肉食,它一概拒絕,有時甚至看都不看一眼這些肉,一連兩天都是這樣。
這可急壞了陳昊,他請獸醫師再次對“貴妃”進行了全面體檢,結果是它的那三處針傷已好了大半,這不是影響它進食的原因,其他各方面也沒有任何問題。“可它為什么不吃東西呢?”陳昊十分不解地問醫師,醫師思量了好一陣,又看著它的雙眼仔細地觀察了好半天,最后終于得出一個令陳昊驚訝不已的結論,“它這是絕食,它在主動絕食。”
“絕食?!一只鳥像人類一樣主動絕食?這可能嗎?”陳昊眼睛瞪得像銅鈴。醫師說:“有這可能,我們不能低估鳥的智慧和情感,尤其是這種經過數千萬年的進化成為空中霸主的大鳥,這次被捕和被扎鋼針的經歷不僅傷害了它的身體,而且還傷害了它的心理,這應該就是它絕食的原因。”
陳昊聽了醫師的話,他再一次湊近看“貴妃”的那兩只寶石般的眼睛,他果然看出它的眼神時而堅毅時而散亂,時而又飽含一種深深的令人心碎的憂郁。陳昊看著看著情不自禁淚流滿面,他雙手捧著它的頭,哽咽著說:“貴妃啊貴妃,你本是天空的主人,你在空中在你自己的家里自由自在地翱翔,你有你的愛人有你的孩子有你自己的生活,你沒招誰沒惹誰,可你卻平白無故地被捕被捆被殘害,要是我是你我也想不明白啊。是貪得無厭的人對不起你,我替那些沒良心的人向你道歉了。我求求你,你就吃點東西吧。”
“貴妃”仍一動不動靜靜地看著他。陳昊仿佛看到它眼里也閃著淚光,他趕緊又拿來肉喂它,可它又昂起了那高傲的頭。陳昊又端來一碗水捧到它喙下,“你不吃肉,那就喝點兒水吧,求求你了。”陳昊一連說了十多遍“喝點吧”,終于,“貴妃”像聽懂他話似地埋頭喝了幾口水。陳昊興奮地馬上把肉端到它喙下,可“貴妃”又一次揚起了頭,仍然拒絕進食。
陳昊無奈地坐在地上,看著“貴妃”搖著頭,朦朧的淚光中,他仿佛看見“貴妃”化為了一個罩著金光的天使,輕盈地飛向無際的天空。
不管陳昊和工作人員用了什么辦法,“貴妃”除了喝點水,仍然什么都不吃。一連七八天都是這樣,眼看它一天天虛弱一天天消瘦。陳昊心疼得要命,可他除了天天念叨著做無用功求它吃,天天為它畫像,他實在沒有別的為它可做。他知道它這樣堅持下去的結果,就會靜靜的死去,然后成為救護中心陳列室中的一具標本。陳昊希望見到的,絕不是標本,而是它在天空自由地飛翔。可遇到這么一只高傲的、無比倔強的、對人類已完全絕望的金雕,拿它有什么辦法呢?
陳昊想著想著,突然冒出一個想法:與其讓它這樣絕食而亡,不如讓它回到草原,回到它的家,說不定它還會重新燃起生的希望,在那兒重返天空。當陳昊把這個想法告訴救護中心的領導時,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于是,陳昊與救護中心簽了一份責任書,由他帶“貴妃”回草原,盡一切努力讓它恢復健康重返天空,如果實在不行,金雕死后也由他交到救護中心。
陳昊專門為“貴妃”做了一個大小合適的木箱,鋪上一層厚厚的棉絮,把已經無力站起身的“貴妃”抱到里面。開著車回草原的路上,陳昊思緒萬千,他想不到這次青海之行遇到這么一串讓他憤怒讓他感動讓他無奈的事情,他原以為他所生活的城市和他所生活的圈子就是五彩繽紛的整個世界,此時他才知道除了他那個小世界之外還有如此的大世界,除了那整天忙碌鉆營不堪重負的人的生命之外,還有充滿生機與希望、充滿情感與悲涼的動物的生命……
陳昊很快便回到了巴桑的學校。看到車子進了校門,巴桑和一群歡叫著的學生圍了上來,“那只金雕沒事吧?”巴桑握住陳昊的手急切地問。陳昊無奈地搖搖頭,從車里把木箱搬出來,巴桑看到奄奄一息的“貴妃”,憂傷地說:“怎么會這樣呢,救護中心不是專門救護野生動物的嗎?他們也沒有辦法?”
“救護中心醫好了它身體的傷,可沒法醫治它心靈的傷。”陳昊把“貴妃”絕食的情況告訴了巴桑。
“真有這樣的奇事?金雕絕食?”巴桑捧起“貴妃”的頭,看著它消瘦的樣子和散亂無神的目光,這位草原上的硬漢禁不住流下了眼淚:“神鳥啊,你犯了什么錯,為什么要遭受這樣的苦難?難道你就這樣等死嗎?你這又是何苦呢?”
四、報復
陳昊把放金雕回草原的想法告訴巴桑后,巴桑一下興奮起來,“我也正這么想呢,也許這是救他的唯一辦法,走,我們馬上就去。”說走就走,陳昊和巴桑開著車帶著“貴妃”又回到了第一次見它的那個地方。
兩人抬著木箱,翻過那土丘,來到那天“貴妃”被捕的地方,再把它從木箱里小心翼翼地抱出來放到地上。這時,陳昊再一次拿出肉和水喂到“貴妃”的嘴邊,它只喝了一點水,然后看了看它曾經翱翔的藍天,又無力地垂下了頭,對嘴邊的肉根本不理。陳昊和巴桑同時無奈地搖搖頭,把肉放在它身邊后,兩人回到土丘上坐下,遠遠地望著它,他們想不打擾“貴妃”,讓它重新感受草原,感受天空,也許它慢慢會燃起生的希望。
陳昊和巴桑坐在土丘上抽著煙,兩人都心情沉重,他們都不想多說話,只是一會兒盯著不遠處的“貴妃”,一會兒又抬頭仰望天空。“要是那天飛走的那只雄雕再飛回到這里來就好了,它是‘貴妃’的丈夫,它要是來了,‘貴妃’一定會放棄輕生的。”陳昊望著天上的白云,吐著煙圈說:“誰知道它會不會也被盜獵者捕走了呢,有人過來了。”巴桑說著指著下方說。陳昊一看,果然有一個藏族老人騎馬帶著一個四五歲的小孩經過這里,他們看見了地上的“貴妃”,便停下來奇怪地觀看。陳昊和巴桑忙過去,巴桑告訴了他們這只金雕的故事,那藏族老人氣憤得大罵盜獵者,他的小孫子輕輕地摸了摸“貴妃”的羽毛后,天真地說:“我去捉蟲子來給你吃。”陳昊和巴桑又向這位名叫達赤的老人請教有沒有什么辦法讓這金雕吃東西。
三個人蹲在“貴妃”旁邊討論著。突然,陳昊發現“貴妃”的眼球轉了幾轉,竟費力地抬起了頭,把目光投向天空。他也往天上看去,發現空中高遠處一黑點正向這里飄來,黑點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楚,看清了,那是一只金雕。“來了,它來了,‘貴妃’的丈夫來了,‘貴妃’有救了。”陳昊說著激動得跳了起來,他突然覺得鼻子酸酸的,眼睛也一下濕潤了。
三人連忙跑開,遠離“貴妃”,他們不能干擾這對經過生離死別的夫妻重聚。只見那只金雕越來越近,陳昊用望遠鏡一看,興奮地說“是它,真的就是它!”三人的目光像線一樣系在這越來越近的金雕上,只見它張著巨翅轉著圈觀察一會兒之后,便穩穩地落在“貴妃”身邊。可是此時的“貴妃”連抬起頭的力氣都沒有了,這雄金雕圍著它失蹤了近十天的配偶轉了幾圈,用他的喙為她梳理羽毛。陳昊期待著這雄雕能把“貴妃”帶走,或者能讓她吃東西。
突然,這雄雕一下躥起,直沖云霄,又在高空盤旋起來,陳昊估計它這次盤旋之后可能會再次下來,果然,它一個俯沖如箭般射下來。離地幾十米時它突然變為斜下沖,身體劃過一道優美的弧線沖向地面。陳昊、巴桑和達赤老人三雙目光直直地緊跟著它滑下來。可令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它這次沒有落到“貴妃”身邊,而是從它上方一掠而過,直撲不遠處正在捉蟲子的那小男孩,利爪猛一下抓住小男孩的后背,振翅而起。
這措手不及的襲擊令三個大人目瞪口呆,當三人回過神來時,雄雕抓住小男孩已飛到空中,向遠方一高丘飛去。“達娃——”達赤老人呼叫著撲向他的馬,翻身上馬朝著雄雕飛走的方向追去。陳昊聽父親說過金雕能抓起一只狼飛到空中,他原以為那只是傳說,如今親眼見到金雕把一個小孩抓到空中,這令他驚愣不已。反應過來后他忙拉著巴桑撲進車里發動車子也朝雄雕飛走的方向追去。
“這雄雕把這小孩抓去是報復人類呢。”巴桑說。“報復?可這小孩子沒得罪它呀。”陳昊大聲說。“是呀,可‘貴妃’同樣也沒得罪那盜獵者呀,唉——都是人類造的孽呀!”巴桑捶著自己的頭嘆道。
聽了巴桑這話,陳昊腦中仿佛一下閃過一道光,他覺得自己一下悟到了很多東西。他一直咬著牙,十多二十分鐘后,當他把車開到那高丘旁時,見達赤老人正跪在地上對著高丘叩頭,邊叩頭邊不停地用藏語念著什么。再看那高丘上,雄雕把已嚇昏過去的達娃按在利爪下,它的頭高昂著望著這邊。陳昊想都沒想就要沖過去,巴桑一把抱住他說:“不能去,此時要是激怒它,它往孩子臉上隨便哪里啄一口后果不堪設想。”
“這——那怎么辦?”陳昊急得直跺腳。巴桑只能目不轉睛地盯著那雄雕和它爪下的孩子。達赤老人不停地叩頭不停地念叨,而那雄雕則按住孩子呆在原地,它仿佛是要向人證明什么。
空氣似乎凝固了,偏西的太陽也停住了腳步,注視著草原上這一幕人與動物的悲劇。“哇——”突然一聲驚哭炸響,原來雄雕爪下的達娃醒了過來, 嚇得大哭。這一哭既把所有的人嚇了一跳,也把那雄雕嚇了一跳,它抓起他一下飛了起來,所有人的心一下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上。所幸的是它沒飛多高又在附近落了下來,也不知是它覺得這孩子太沉還是它還想與人們對峙,但令人揪心的是達娃仍在它爪下。
“天啊,佛祖啊,救救孩子吧。”達赤老人說著,雙手合十高舉過頭,向前踏一步,然后用合十的雙手碰額、碰口、碰胸,又雙膝跪下,全身伏地,額頭叩下。磕起了五體投地的長頭,磕一個長頭前進一步。老人這種最虔誠的方式向神祈禱,祈求他們的神鳥放了他的孩子。老人離高丘上的金雕和孩子越來越近,金雕還沒有放孩子,但它也沒有動,它只用它那深邃的目光注視著老人的舉動。
陳昊被眼前的情景震驚了,從未磕過長頭的他也學著老人一起磕起了長頭。當陳昊磕第十個長頭時,他看到那雄金雕突然放開孩子,展翅飛向天空,他們擁上高丘,抱起哭泣的孩子,又齊刷刷地對著高飛遠去的金雕跪下謝恩。
這一瞬間,陳昊的心劇烈地顫抖了。
五、尾聲
感嘆不已的陳昊這才想起“貴妃”,他叫巴桑上車,急匆匆地往剛才放“貴妃”的地方飛馳。到了近前一看,“貴妃”已斷了氣,它骨瘦如柴的身體已經僵硬,頭側在草地上,向上的一只眼睛還睜著,不知是對人類的殘忍死不瞑目,還是殘留著最后一絲對自由天空的無比向往。
陳昊眼里又充盈著淚水,他仰天長嘆:“天啊——這是為什么?”
突然,他看見天上有團黑影直撲下來,仔細一看,是那只雄雕。“快躲開,它又來了。”巴桑叫著拉著陳昊往后退。陳昊也正擔心這雄雕來報復襲擊他和巴桑,只見收著雙翅頭朝下的它在夕陽的殘照下如一枚閃著金光的炸彈直直地落下,“砰——”一聲落在“貴妃”尸體身旁。
驚訝萬分的陳昊和巴桑忙奔了過去,一看,這雄雕也已死亡。它為它死去的伴侶殉情而亡。
陳昊望著天空愣了好半天,他想起了兩句詩:“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然后他瘋一般從車中取出作畫工具,如癡如癲地畫了起來……
三個月后,陳昊放棄了出國深造的機會,發起成立了一家名叫“自由天空”的民間鳥類保護組織。
(責編/方紅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