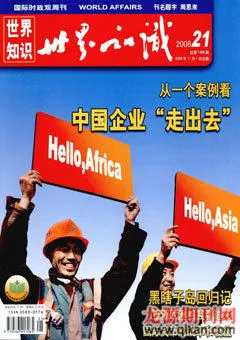好書過眼
國際社會的毀滅
《國家間政治
——權力斗爭與和平》(第七版)
[美]漢斯·摩根索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當政府官員的民主遴選和責任制摧毀了作為一個有效制約體系的國際道德時,民族主義也摧毀了道德賴以發揮作用的空間——國際社會本身。國際社會的毀滅是一個緩慢腐蝕的過程,這中間也曾遇到舊秩序的頑強抵抗,如神圣同盟。然而,曾把基督教君主和貴族聯合在一起的國際社會及其道德,則確定無疑地在19世紀臨近結束時衰落了。威廉二世曾企圖用戲劇性的空洞言辭來阻止這一衰落趨勢。他在1895年致信俄國沙皇評論法國人說:
共和派是天生的革命分子。在那個國家里,皇帝陛下們的鮮血仍在流淌。自那時以來,它還有過快樂和安寧嗎?它難道不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流血而變得舉步維艱了嗎?尼基,請相信我的話,上帝的詛咒已經永遠降臨到該國人民頭上了。我們這些基督教國王和皇帝擔負著上帝賦予我們的神圣義務,那就是堅持承蒙上帝恩惠的原則。
此外,美西戰爭前夕,威廉二世還曾構想了一項聯合歐洲列強支持西班牙君主反對美洲共和國的計劃。這一計劃流產了,但它違反時代潮流這一點卻使其顧問們驚愕不已。
不過,即使是到了1914年一戰爆發前夕,當志同道合的人們不得已而分道揚鑣、加入不同的交戰集團時,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許多聲明和電文中都流露著傷感的懊喪顫音。甚至德國總參謀部也在備忘錄中把迫在眉睫的一戰說成是“歐洲文明國家間的相互屠殺”。該備忘錄帶有憂慮和預感地說:“事態必定照此發展,除非,人們或許可以說,出現了奇跡,從而在最后一刻制止了一場將會使幾乎整個歐洲在數十年中文明蕩然無存的戰爭。”然而,這種奄奄一息的懷舊情調,再也無力影響人們的行動了。至此,歐洲各國統治者彼此間的共同點已自然少于他們與本國人民之間的共同點。不同國家的統治集團所隸屬的、為不同的國內社會提供共同框架的那種國際社會,已經被眾多的國內社會本身取而代之了。
當19世紀這種貴族國際社會瓦解為國家碎片的過程幾近完成時,民族主義的首倡者確信這種發展將會加強而不是削弱國際道德的紐帶。因為他們相信,一旦獲得解放的人民的民族愿望得到了滿足,貴族統治為民眾政府所取代,那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把世界各國分開了。意識到自己同為人類的成員并為自由、寬容與和平的同樣理想所鼓舞,他們就會在和諧中追求各自的民族命運。但實際上,民族主義精神一旦在民族國家內得以實現,就被證明是狹隘的和排他的,而不是普世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當17、18世紀的國際社會遭受毀滅的時候,顯而易見的是,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取代這個統一和制約的因素——一個凌駕于各個國內社會之上的真實社會。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旗號下的國際團結被證明是一種幻想,有組織的宗教傾向而非超越民族國家。因此,民族就成了個人效忠的最后參照物,不同民族的成員都有他們自己特定的效忠對象。
我們從凱恩斯勛爵筆下的克里孟梭看到了對這種新的民族主義道德的生動描述:
他對法國懷有如同培里克利斯(雅典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演說家——編者注)對雅典懷有的那種情愫——在他身上體現著獨一無二的價值,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他有一個幻覺——法蘭西;又有一個幻滅——人類,包括法國人,甚至他的同事。……民族何其真實,你熱愛其中之一,漠視或仇恨其他。你摯愛之國的光榮是一個渴望的目標,但一般總要以犧牲你的鄰國為代價才能實現。為慎重起見,口頭上認可一下與蠢笨的美國人和偽善的英國人達成的“交易”是必要的,但如果相信現實世界為諸如國際聯盟這種事物留有很大的余地,或相信自決原則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真是愚蠢了。自決原則不過是為本國利益重新安排權力均衡的一種奇妙方案而已。
先前具有凝聚力的國際社會分裂為眾多道德上自我滿足的國家社會,這些國家社會不再在一個共同的道德戒律的框架內運作了,這種現象不過是一場深刻變化的外部征兆。這場深刻變化在最近一段時期改變了普遍道德戒律與各個特定國家倫理道德體系之間的關系,它循著兩個不同的方向進行。這種變化削弱了超國家的普遍道德行為規則,使之完全失去效力。而在民族主義時代以前,這種行為規則曾把一套限制體系——無論它是多么脆弱、有多么大的疏漏——加之于各國的外交政策之上。反過來說,這一改變也大大加強了各國賦予它們特定的倫理道德體系以普遍適用性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