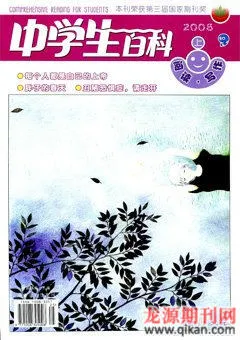失去的美好
隨著主人關門的聲音,廚房的兄弟姐妹開始活動起來。大家扭扭腰抖抖腿,嘰嘰喳喳地開始聊天。
我是一只調羹,我很喜歡我的名字,但大家都喜歡叫我“鐵勺”。我曾經(jīng)是一只渾身畫滿精致花紋的鐵制調羹,那時大家都叫我“調羹帥哥”,可是時間長了,我的身體開始生起了銹斑,怎么擦也擦不掉,于是,我被主人從餐桌上撤了下來。
我已經(jīng)習慣了沉默,當銀筷和盤子、碗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起晚餐如何鮮美的時候,我只靜靜地待在角落里看著她,她是白瓷調羹,腰身纖細,通身潔白,沒有一點瑕疵。主人只有在午后喝咖啡的時候才會用她,每每看著她的身體在香醇的咖啡里舞動,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想上前拉起她的手,和她一起翩翩起舞。
可是,我卻一直沒有勇氣,因為我是一只生了銹的鐵勺。
我就這樣日日悄悄注視著白瓷調羹,每當主人關上廚房的門,她總會爬起來,坐在咖啡壺旁用軟布擦拭著自己身上未干的水珠。如果發(fā)現(xiàn)她要抬頭或者挪動身體,我總會很快速地低下自己的頭,我很怕她看見我在看著她。
忽然,我看到銀筷不知什么時候湊到了她的身邊,我警覺起來,看著他。他輕輕走到白瓷調羹的身后,靜靜地看著她,我分明看到那眼里滿滿的愛慕。銀筷拍了拍她的肩頭,她放下手中的軟布,回頭,抿嘴而笑。
他們一起坐在咖啡壺的身邊低聲耳語,時而會看到她的臉頰飛起紅暈,笑容寫滿了幸福。咖啡壺知趣地轉過身去,用他龐大的身體將銀筷和白瓷調羹擋在了負后。
忽然,我的胸膛里有什么東西像碎掉了一般,頃刻間,滿地晶瑩。
此后的日子,我對銀筷變得很有敵意。我總會在銀筷和大家聊天的時候,故意在他身邊說著風涼話。我也只能如此。我深知論相貌我不如他,論背景,我一個鐵制調羹,還是生了銹的,又怎么能和他銀筷相比。
我能做的,可以用來表示我心中不滿和憤怒的,也僅此而已。
沒有人知道那個一向沉默、與世無爭的鐵勺為什么會忽然變得如此尖酸刻薄,大家討論的話題已經(jīng)開始以我為中心,我總會看到他們談話間不時地看看我,那種淡漠的眼神足以殺死我。這個時候,我會深深地低下頭去,像要低到土里去一樣,那樣卑微。
其實,我很想知道,在所有人都談論我的時候,白瓷調羹。她是不是也在談論我。
我還是恢復了我的沉默,可我依舊每天注視著白瓷調羹,只是更加地小心,我裝作在剝落我身上的銹斑,我裝作無意間望向她在的方向,我裝作無意間地轉頭,每個動作幾乎都是為了掩蓋我刻意看她的目光。
她還是那樣,坐在咖啡壺的身邊用軟布擦拭她身上未干的水珠,只是時而會不由自主地笑出來。笑著,并且在廚房里尋找一個家伙的身影。我多么希望她所尋找的是我,可事實終究不是。
她戀愛了,同時,我失戀了。
今天早晨我醒來的時候。大家都已經(jīng)在為早餐做準備了。銀筷悠閑地用手撫過自己的軀干,盤子和杯子也在互相清理著身上的細微灰塵,白瓷調羹和咖啡杯在說著什么,一臉微笑。
忽然,我感到莫名地悲哀,什么東西涌上來將自己包圍,透不過氣。
我忽然很想奔跑,很想發(fā)泄。
我站起來,很艱難地,因為我的腿由于長時間長銹斑變得不再結實。我看了看白瓷調羹,再看了看銀筷,起步,瘋跑起來。我跑過水池邊沿,穿過杯盤櫥,奔過調味櫥再奔向掛筷架……
銀筷沒有看到我向他奔去,他背對著我。我看著他的背影忽然像發(fā)了瘋般加速跑去,就在我要撞向他的時候,眼前閃過一抹白,那樣的熟悉又陌生。
然后,我只聽到一個清脆的聲音回蕩在廚房里,久久沒有散去。
大家都愣在原地,目瞪口呆地看著所發(fā)生的一切。連同銀筷和我,
她落了下去。我是說從一米高的櫥柜上落了下去,為了保全銀筷。她那柔弱纖細的身體怎么能受得了我使了全身力氣的撞擊,她就那么落了下去,粉身碎骨。
我慢慢爬向櫥柜的邊緣,看著地上的她,連碎片也是那樣潔白,瑕疵全無。
我想我是最該落下去的人,所以,我兩手一撐……
在我下落的時候,我才忽然想明白,原來,世間很多愛,不一定擁有了才美好,總要有一個人學會去成全。
編輯 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