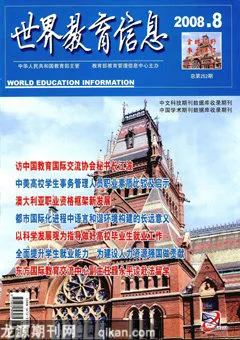淺論改進古典詩詞的教學
[摘 要] 在中職語文教學實踐中,學生往往將古代詩詞的欣賞視為畏途。如何走出這種教學困境?要摒棄單調乏味的字句疏通和死記硬背的老套路,遵循詩詞的創作規律和詩詞本身鮮明的文體特點以及學生的認知規律,采用活潑多樣的教學方法,結合多彩多姿的現實生活,才能激發學生學習古典詩歌的興趣,掌握詩詞欣賞的規律。
[關鍵詞] 詩眼 補白 想象 轉化法 比較法
在中職的語文教學實踐中,學生普遍地將古典詩詞的欣賞視為畏途,飽含古人情感和智慧,穿越千年時空和我們共呼吸的文學經典,卻絲毫不能引起學生情感上、思想上的共鳴。出現這樣的局面,主要以下兩方面原因:
首先,教材中的古詩,或悲憤滿懷,或慷慨激昂,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書寫人生際遇的長吁短嘆,因歷史久遠,寫作背景復雜,學生就不易體會作者的感情,因而把握不準詩的感情基調,充滿詩中的憂患意識難以與這些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長大的青少年的情感產生共鳴。讓他們領悟柳永在《雨霖鈴》中所抒發的哀怨纏綿的離情別緒,不存在太大的問題,但要他們進一步理解“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這幅無比凄清的曉風殘月里流露出的漂泊、無依、對人生對前途的那種迷茫、透徹心骨的凄涼,就很難了。李清照的《聲聲慢》,在一片殘秋的蕭瑟景色中,年老寡居的己愁、山河破碎的國愁,重重疊疊,沉重而凄涼,而對這一切,我們的學生卻無動于衷。
其次,是教學法的問題。在詩歌教學中,存在著輕視鑒賞技巧的風氣。重詩歌史知識傳授,重主題思想的分析,而忽視了鑒賞技巧的把握。由于引導上的不得法,原應鮮明活潑的個性化感受被單調乏味的字句疏通所取代,原應詩意盎然的品味淪為索然寡味的死記硬背。其實,離開了鑒賞技巧的把握,主題思想的分析往往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難以落到實處。有時,即使與學生交流鑒賞技巧,也只是支離破碎的,不具系統性,學生就必然將古典詩詞的學習視為畏途。
那么,如何走出古典詩詞教學的這種困境呢?總結多年來的教學實踐,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徑。
一、推敲“詩眼”
從詩歌的特點來看,語言的凝練是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詩歌的創作講究鍛字煉詞,它是提升詩歌品位的重要手段。從鑒賞評價這個側面看,如何抓住詩歌的詩眼,披文入情,品味作者當時迸現的情感,體會煉詞煉字之妙境,借一斑以窺全豹,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引導學生學會鑒賞古詩歌的有效方法。一首詩歌的詩眼,就像一個感情火山的噴發點。詩詞中的感情火山是處于睡眠狀態的,如果能引導學生恰當地扣住詩眼,層層深入,詩詞中的情感火山就會喚醒、噴發。
鑒賞詩歌要著力剖析詩中的關鍵詞語。如:宋祁的 “紅杏枝頭春意鬧”,其中“鬧”字使得境界全出,不禁讓人浮想聯翩:春光燦爛,萬紫千紅,紅杏滿園,充滿生命力的春天氣息迎面撲來。詩人以枝頭上春意盎然,展現一派春日勃勃生機的景象。這“鬧”可能是杏花爭春之喧鬧,可能是散著芬芳的紅杏同嫩枝綠葉、春風春雨的暢談,亦有可能是紅杏枝頭那勤勞的蜜蜂與翩翩起舞的彩蝶在采蜜爭春,時有鳥鳴其間……有聲有色,有動有靜,令人萬千遐思,百般回味,一字竟能演繹出一幕生機盎然且色彩綺麗之景。
又如,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是一個經常被引用的典型例子,多少年來傳為煉字的美談。這一詩句起初寫的是“春風又過江南岸”、“春風又滿江南岸”、“春風又入江南岸”等,最后才改成“春風又綠江南岸”,它究竟妙在何處呢?妙就妙在排除了春天給人帶來的其他感受——在感官上的聽覺、觸覺、嗅覺;在視覺上的其他顏色——紅色、藍色、黃色。在排除弱化的同時,強化了視覺上綠的感受,這種感受與詩人懷戀故鄉的情緒是融在一起的,詩人心底沉甸甸的懷鄉情緒原本是一種抽象的無著落的東西,這時他終于找到一個可以裝載這種抽象情感的器皿——“綠”,沉甸甸的“綠”,就是沉甸甸的鄉愁;滿目的“綠”,便是滿腔的愁緒。再比如,張先的“云破月來花弄影”,一個“弄”字將花擬人化,賦花以人的情感,仿佛一個美麗天真的少女在月光下顧影自憐,別有一番情趣。一首好詩,往往因一字之妙用,而使全詩生色。
一首詩的詩眼可以是一個實詞,也可以是一個虛詞。在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在這個詩句中,一個“初”字,寫盡了周瑜的年少有為,意氣風發。大喬、小喬是兩姐妹,是當時吳國有名的美女,大喬嫁了孫權,小喬嫁了周瑜,英雄美人,無限江山,君臣和諧,一個風流倜儻、少年有成的儒將就這樣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杜甫的《蜀相》頷聯也是虛詞煉得好的典范,“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這兩句的詩眼,不是什么“春”字“好”字,而是“空”和“自”這兩個虛詞,一方面突出人少,一方面感慨:草、鳥哪里知道人世間的感慨呢!這就用景的無情寫出人的有情,這里的碧草春色,黃鸝好音,因這兩個虛詞,呈現給我們的是無邊無際的荒涼寂寞,盡管階前草碧,盡管鳥鳴悅耳動聽,但此時的詩人卻似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那種無心玩賞,百感交集的情狀躍然紙上。
一首詩的詩眼還可以是一個詩句。例如,杜甫的《旅夜書懷》:“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句,詩眼是“危檣獨夜舟”,其余全屬烘托。這句詩勾畫了這樣一個境界:河邊孤零零地泊著一只小船,桅桿高聳;岸上只見小草,不見人家,簡直冷寂得很。在星空低垂、原野遼闊、月隨波涌、大江東流這樣的境遇中,一葉小舟顯得何等孤單、渺小,它的命運簡直可以聽憑大自然的擺布;而江水的奔流更使他聯想到時光的迅速消逝……這小舟的命運正是詩人命運的寫照。岳飛《滿江紅》中有一膾炙人口的千古佳句,“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這兩句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字里行間飽含著復雜凝重的思想感情:既有對自己屢遭排擠、壯志難酬的感嘆,又有對南宋王朝偏于一隅、不思北伐的憤懣,更有對中原失陷地區人民深深的摯愛。寥寥數語,一個胸懷磊落、不患得失、不計名利、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高大形象便凸現在讀者的面前。又如,《離騷》中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一句,反映了屈原剛正不阿,一身正氣。“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一句,表現他堅持真理,獻身理想的節操。“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反映他潔身自好、自我完善的思想。賞讀這些語句,就能更好的理解詩歌所表現的內涵和意味。
二、補白:展開想象的翅膀
中國古代畫論中有“虛實相生”之說。清代繪畫理論家笪重光說過:“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瘤。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所謂的“無畫處”,就是一種藝術的“空白”。從藝術的空白切入,可以品味出藝術中的無窮之意。在詩歌中,也留有大量這樣的空白。唐代司空圖在《詩品·含蓄》中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所謂“不著一字”,并非什么都不說,而是簡練傳神地勾勒幾筆,點到即止,富有暗示性,意在言外,使人反復吟詠想象而得之。古典詩詞的語言特別精警、跳躍、含蓄,“語不接而意接”,為讀者留下了很多的“空白地帶”,就是這種語言特點,使得詩歌含蓄蘊藉,產生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鑒賞詩歌時應引導學生通過想像,把作品留下的空白補充出來,使之成為完整的形象、情節或意境。
例如,杜甫《春望》首聯和頜聯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作者在安史之亂中見到國破家散的慘象,內心創傷不可言狀,然而這首五言律詩,感情蘊飽,寓情于景,為學生提供了廣闊的想象余地。“破”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樣子?花香鳥語本是怡悅神心、賞心娛樂之物,為什么“花濺淚”、“鳥驚心”呢?作者是采用擬人之筆,反襯出內心痛苦之至。結聯的“搔更短”、“不勝簪”是什么形象?是詩人老態龍鐘的自畫像。他飽經顛沛流離之苦,備受戰亂離散之怨,致使頭發疏而皤然;透過形象,探究其內心是什么感情?詩人憂傷綿綿,愁腸郁結,其中的多處“空白”就得用想象去填補,師生共同把作者那樣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描繪出來。
又如,賈島的《尋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這首詩的特點是寓問于答,這就是一種藝術空白。在引導學生鑒賞這首詩時,教師可以由此切入,由淺入深地提出三個問題:這首詩有幾問?都問了些什么問題?這樣寫有什么好處?這三個問題,可以激發學生通過聯想和想象,補出省略的內容,并領會寓問于答這種構思的妙處。
三、語言轉換法
閱讀,其實質就是進行語言的轉化。讀古代詩歌,把它翻譯成現代詩歌或散文的做法也是可行的。語言轉化同樣包含著創造性。通過語言轉化,把枯燥無味的被動理解變成了饒有趣味的創造性閱讀,學生可從中嘗到學習古代詩歌的甜頭。例如,賞析宋代名臣文天祥的《過零丁洋》時,老師將鑒賞詩歌的任務放手給學生,引導大家從獨特的視角以各種不同方法鑒賞此詩,稍加討論研究后,學生們各抒己見,或多或少都談出了自我獨特的感受。對“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有些學生以第一人稱角度寫道:“淚水已從臉頰滑落,窗外鉛色的天空越發沉重了,天地昏暗一片,海上波濤如怒,浪頭一個個掀上船板,我心也正如此水呀!山河已碎,我身陷囫圇,孤苦伶仃,被縛于此,零丁洋啊!零丁洋!你是否為我所生,憶少年豪氣沖天,有青云之志,可現在……,哎,雙眼已又朦朧,我該何去何從呢……”不難看出,這種方法,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理解和鑒賞能力。
四、比較法
古典詩詞鑒賞的比較法,就是把一些有某種關聯的作品拿來,從不同的側面,認真加以對照,或相近,或相反,或同中有異,或異中有同,從中找出規律性的認識。通過反復比較,學生學到的知識是完整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有聯系的,而不是孤立的;是靈活的,而不是呆板的。
賞讀同類題材作品中的相關詩句,去領略各有千秋的風格美。比如,教讀李煜的絕筆詞《虞美人》,當賞讀其名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時,為體會詞句抒情的巧妙,可讓學生在記憶中搜尋寫“愁”的詩句。學生找出的有:“自在飛花輕似夢,天邊絲雨細如愁”;“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飛絮,梅子黃時雨”;“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等。經過類比,學生深刻體會到李煜是巧用生花妙筆將抽象的愁緒形象化,他的“愁”思如春水般汪洋恣肆,長流不息,亡國帶給詞人的萬般愁情被蒙上了生動的質感。同時,通過采集、品賞諸多寫“愁”的詩句,學生感受到一腔愁緒經過不同詞人的點染,變得情態各異、生動感人。通過這樣的延展互補,學生擴大了知識面,增強了對其他同類作品的品賞能力。
比較對照風格,在求異或求同中評價作品。“風格”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作品的“個性”。以李白與杜甫的作品比較,例如詠月,李白是“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他怎么感覺,就怎么寫,感情直瀉而出;杜甫則曲折婉轉:“今夜 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他不寫自己身邊的月,而寫遠在妻子身邊的月,不寫自己對月的感受,而想象妻兒在月下的感受。兩相比較,不難看出:李白寫詩喜歡以我之情奪物之情,杜甫則善于體物入微、借物之情抒我之情,因而形成兩人不同的詩風。
在學習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時,可以把它和柳永的《雨霖鈴》進行比較,指導學生從詞的內容、情感基調、藝術手法、風格等幾個方面來解讀這兩首詞,從而領悟婉約派與豪放派迥然不同的藝術魅力。還可以把《念奴嬌·赤壁懷古》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相比較,同樣豪邁開闊的意境,氣勢磅礴的寫景,同樣追尋古代的英雄人物,但流露出來的卻是不一樣的情感。在蘇東坡的詞里,對古代英雄人物極盡完美的傾情塑造抒發的是渴望建功立業而不能的一絲失落,雖然激昂向上仍是其主旋律,但壯志難酬的苦悶在詞的結尾卻是十分明顯的;但在毛澤東的詞中,那些曾經照亮了歷史天空的古代英雄人物,都是“俱往矣”的過去式,“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詞中從頭到尾回蕩著一種舍我其誰、傲視古今的英雄氣概。在這樣的比較中學生能明白詩詞的風格和詩人的個性,擴大視野,慢慢地摸索體會到古典詩詞的學習方法。
參考資料
1 唐宋詞鑒賞詞典.北京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