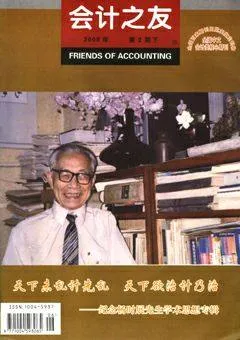效益十策
經濟效益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思想上、政治上是否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問題;由過去的主要根據產量、產值來考核一個企業,改為按經濟效益來考核,不是一個簡單的考核標準的改變問題,而是一個關系翻兩番的目標能否達到、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甚至簡單再生產能否繼續進行的問題,意義是十分深刻的。
這兩點好理解,爭論也不大。
不過,重要性不在于此。
重要性在于,今天來談經濟效益,主要已不再是一個生產領域里的問題,而是一個流通領域的問題。
經濟效益,歸根到底是直接和銷售掛鉤,而不是直接和生產掛鉤的。
銷售大,效益高;銷售少,效益低;沒銷售,沒效益。產品質量再好,成本再低,花色品種再多,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再高,而銷不出去,一切都等于零!
這一看法和我們過去習慣的看法出入很大,如果不改變過去的看法,經濟效益的問題就不好談。
這不是說:我們的今后就不必注意發展生產。相反,突出流通的問題,正是為了不但保證發展社會主義的簡單再生產,而且,是為了保證發展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
這是不是說:我們過去抓生產,抓多、快、好、省沒有抓在點子上。過去抓生產,抓多、快、好、省,今后還要大抓生產,大抓多、快、好、省,不過從經濟效益上說,如果這一切不落實到銷售上,一百倍的產量,一百倍的多、快、好、省,也毫無意義。
繼續不斷地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長期的、決不可動搖的根本任務。過去要發展,今后還要大發展。
不同在于:1.過去是不講經濟效益的發展,費力多,成果少;今后要改變為講效益的發展,要求費力少(有過去蓄積起來的力量可以利用,是理由之一),而成果大。因此,在抓法上,就必須應有的改變。2.過去不講或主要不講經濟效益,可以不注意銷售;今后要講效益,就一定要注意銷售。3.過去講包銷,企業沒有銷售的問題;今后不包銷,銷售的問題自然就突出。4.過去,老百姓家底薄,商品少,不愁銷;而今,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過,那怕是“皇帝的姑娘”也要打量打量,主動權在買方,不合買方的心意,說啥也白搭。
時代不同了,要求不同了,一切在變,我們的認識、策略也得變,變則通,不變則窮。本文說的就是:怎么變?
一、改變經濟工作的重點,由重產到重銷
這是第一條,也是最根本的一條。
不能把這個問題認為只是一個簡單的以銷定產的問題,這是一個經濟工作重點全面轉移的問題。
從經濟效益看,有一種產值,能很快銷掉的,叫有效產值;銷起來比較費勁的,叫低效產值;銷不動的,叫無效產值。提高經濟效益就是要提高有效產值,消滅無效產值。因此,就必須要求各經濟管理部門、各企業把主要力量用來安排和銷售有關的問題,比如:國內外市場問題、信息問題、預測問題、銷售方式、結算方式問題、售價問題、競爭問題、加速商品流轉問題,廣告、商標、商譽、專利權問題,當然,還有產銷配合、以銷售來帶動生產上的多、快、好、省的問題等等。一切政策、方針、措施、資源、人事都要從有利于促進銷售出發,過去重產,今后重銷;過去以產帶銷,今后,以銷帶產;過去,把產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產為主攻方向;今后,銷轉化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銷為主攻方向。
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有什么值得借鑒之處,那么,我倒認為:從利潤,從而也就是從銷售出發來抓經濟工作,倒十分值得注意。不妨認為:西方企業經營的精髓,正在于此。一切研究資本主義經營的人,也無不深感于此。
二、改變工業經營中的資海戰術作風為集約經營作風
30年來,我們發展工業生產,用的是“資海戰術”:投資1 000萬,產值上不去,就2 000萬:還不行,就5 000萬。辦一個廠生產上不去,就辦兩個;還不行,就三個。反正,投資多了,產值總要上,廠子的地位總要提高。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外延式的發展方式。花錢多,費勁少,廠長書記歡喜,老百姓不歡喜。我們是個資金貧乏的國家,一個錢該掰成兩半用,資海戰術,我們搞不起!
不但如此,用資海戰術來增產,行;用資海戰術來提高經濟效益,卻往往不行。甚至,往往還背道而馳。
產值的增加和效益的增加不是一碼事。從計算上說,有效產值起分子的作用,無效產值不算,固定投資是分母,效益是商。
有效產值的增加在比率上大于固定投資的增加,則經濟效益增;在比率上等于固定投資的增加,則經濟效益不變;在比例上小于固定投資的增加,則經濟效益減退。這是算得出的。
如果兩份固定投資,生產10份有效產值,則經濟效益是5;如固定投資增加到3份,有效產值必須從10份增加到15份,才能保持原來是5的經濟效益,如果有效產值沒有增到15份的把握,甚至沒有可能增加到15份,而貿然將固定投資增加到3份,那就連原來的經濟效益都保不住。
這就是說:過去追求產值,是固定投資越大越有利;而今追求經濟效益,是固定投資越大越難于見功。過去的口號是“增產節約”,今天的口號應該是“增銷節資”,這一點,我以為很重要。
這決不是說,固定投資對經濟效益是消極因素。一個因素是積極或消極的決定于你駕馭它的能力。固定投資也如此,你駕馭的能力強,則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能力不行,則趙括將兵,越多越糟。目前,在經濟戰場上,我們的韓信還不多,因此,對增加固定投資這個“兵”的問題,就不能不慎之又慎!搞不好就會把“兵”往虎口里送。
從我們的情況看,遠的不說,說這幾年。這幾年投產的固定設備,據估計,仍有1/3不能發揮原設計能力;有的剛投產,工廠就關門,有的剛投產,工廠就虧本。看來,對這個資海戰術感興趣,不惜把“兵”往虎口送的,還大有人在,不能不引起注意。目前,必要的“兵”還是要增,不但要增,且要保證。但與此同時,卻應多動動腦筋,使每個“兵”都能充分發揮其作用。使以后能不增“兵”卻增加戰斗力,今天,我們把這種增產方式稱為內涵式的增產方式。
用農業生產作比,今天不是一個一味擴大耕種面積,或者擴一片、丟一片的問題,而是一個釘住不動,埋頭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的問題,一個把農業的粗放經營改變為集約經營的問題。這是一條我們所不習慣的道路,但卻是一條提高經濟效益的必由之路,一條真正的新長征的道路。30年的老路,而今在提高經濟效益面前,已經是非改不可了。
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建議對全國的固定資產,比照人口普查,作一次徹底的清理,把固定資產的水分擰干,查明有多少是在正常運轉的,多少是可以由幾個單位配套起來使用的,多少是經過更新、改良才能起作用的,多少是對某一企業運轉率不高、基本、根本不起作用應該調出、出租、出借、出售、甚至奉送,讓它在另一單位發揮作用的,多少是老掉了牙、能耗大、維修費用高、精度差該報廢重置的。經過普查,把“分母”的問題徹底解決好,經濟效益才可以提高,算出的效益才可靠,才有可比性。
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各經濟部門、各企事業單位、科學實驗單位注意,把自己用不上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固定資產卡住不放,甚至還像過去一樣,盲目爭取固定投資,從經濟效益上看,是蠢事;不考慮市場容量,貪大求多,在國家計劃外肆意增加固定投資,是蠢事。
三、改商業經營的“合”為“分”
30年來,我國商店和服務行業的規模大而點少,經營過于集中,極不利于商品流通,試看:
大阪:每22人有一商店和服務行業;
香港:每75人有一商店和服務行業;
天津:每890人才有一商店和服務行業。
我國的商店,顯然就太少了,嚴重地影響貨暢其流。看來,在商業戰線上,今后應集中抓一個“分”字。
貨暢其流是多渠道的。“分”就是要使各渠道都暢通無阻。增加網點,只是渠道之一。
要“分”,網點就不能也不宜單靠國營來增,應鼓勵多種經濟形式,把商品盡速送到消費者手中。
要“分”,自然就不能搞“獨家經營”,搞“割據”,為了國家的經濟效益,要允許各顯神通,有生意大家做。
要“分”,銷售、結算的方式,就應靈活多變。賒銷、寄銷、代銷、展銷、郵售、分期付款、游街串巷、送貨上門,可以齊頭并進。
至于增加營業時間、改善服務態度、提高服務質量這些問題,本是與“變”無關,與“分”無涉,不應在話下的,可這些問題不解決,再“分”也白搭,消費者視上商店為畏途,還談什么“以廣招徠”,還談什么經濟效益?對這些問題,特別是服務態度惡劣的問題,我們的措施要得力,要堅決。
四、改工業經營的“分”為“合”
如果說,從經濟效益看,商業經營應分散,而我們過分集中了;工業經營是應集中的,而我們卻又過分地分散了。
工業集中經營,可以減低成本,比如手表:
年產3-4萬只,平均每只成本43元;
年產4-10萬只,平均每只成本30元;
年產11-50萬只,平均每只成本26元;
年產50-100萬只,平均每只成本19元。
生產的規模越大,固定投資的效率越可以充分發揮,成本自然越低,產品就越有上市能力。
而今,各行各業,小廠林立,重復建廠的情況十分嚴重。以廠數而論,棉紡廠已超過國家計劃的13%,毛紡廠35%,自行車、手表43%、縫紉機50%,而今哄上“新三件”,電視機的廠數已超過國家計劃的83%,還大有方興未艾之勢。電扇更突出,照我估計,照內外貿預測,有四個華生這樣的就夠了,而今,大小電扇廠1300有余!
小廠的產品,質次價高,很大一部分是無效產值。以之“交學費”則可,以之算經濟效益則等于零。不只如此,小廠靠近水樓臺弄到手卻又白白浪費的原材料,卻往往又是大廠生產急需、弄不到手,從而影響其完成內外貿任務、影響其經濟效益的資源,結果,兩敗俱傷。目前,以農副產品為原材料的企業、如煙、茶、糖、皮、毛、棉等等,都有這種情形。
為了避免這種情形,工業經營上一定要從全國一盤棋、地方服從中央、財政服從經濟這些基本原則出發,堅決實行同行業的“改分為合”的方針,堅決實行行業管理,實行托拉斯化。
同行業的“改分為合”又應和各企業中同一專業的“改分為合”結合起來,使每個廠子都成為大而專的廠子。小小一部縫紉機,零部件300多種,集中由一個大廠生產,效益就難于提高,分別改由一些高度專業化了的廠子來生產,效益就大不一樣。一些服務性作業,如電鍍、熱處理、鑄鍛、工模具,每個企業多少都要一點,分別由各廠自己經營,效益就差;集中由一個專業廠來經營,效益就高。10個棉紡廠,每個生產10種彼此型號相同的紗,就不如分一下,各自生產一種自己最拿手的紗。馬克思說,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過去,我們習慣于花大錢、做小買賣,今天講經濟效益,就應多考慮考慮這種辦法,如何不費分文而能使經濟效益大有提高。不費分文而提高效益的辦法多的是,要求我們的企業家結合本企業的具體情況去發掘。在這里,我們的優秀企業家是可以大顯身手的。
五、改把銷售的重點從城市轉向村鎮,打開廣大的農村市場
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從哪個方面看都這樣。要提高經濟效益,同樣也要把目光轉向農村。
對8億農民的消費能力,千萬不能低估,不只是為了經濟效益,尤其是為了我們的“政治效益”!
據手邊的資料,1978年我國商品零售額,8億農民只占52%,兩億城市居民占48%;1981年,農村就上升到56%,城市則下降為44%。目前,農民收入急劇增加,1982年的人均收入為270元,比1978年已翻了一番。1982年,出現了全村彩電化的農村;1984年3月止,出現了16個買飛機的農村,出現了買小臥車的農家。可以預料,今后,農村所占的商品零售額還將繼續上升,不但消費資料,還包括運輸、食品加工、糧食加工、建筑器材、文體教育設施等生產資料,如果上升到和城市一樣,應占總零售額的80%,而今還差的遠,前途未可限量。農村零售額增1%,照1982年的商品零售總額計,就是23.5億元,隨著零售總額的增加,這個數字還將不斷增加。今天,農民正沉浸在土改以后所未曾有過的喜悅里,我們在因此而歡欣鼓舞之余,不要忘記以更豐富、更多采的商品,更活躍的商品經濟,使農民的日子更紅火起來。
六、 改變產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發揮我國勞動力十分充實這個根本優勢,增產勞動密集型產品
勞動力十分充裕,是我們的“國家優勢”。
搞現代化而缺乏資金,是我們的“國家劣勢”。
因此,我們的方針就應該是充分運用我們的優勢來轉換我們的劣勢。
直接出口勞動力,在國外承包土建工程,是一種可行的方式,要大力抓。并應盡量通過承包項目來促進建材的出口和海運事業。這一點,我們做得還不夠。目前,還頗有肥水落入外人田的味道,十分可惜。
但勞動力的直接出口畢竟有限度,還有一個發揮勞動力充分優勢的方面,就是提高出品產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國外勞動力昂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產量少,售價高。去年在澳大利亞,看到在市上出售的藤心椅,每兩把400余澳元,折合人民幣700元;中等質量的沙發每套1000余澳元,折合人民幣1750元。勞動密集型產品是缺乏勞動力的國家不敢搞的,可人棄我取,正好為我利用充裕的勞動力,不費固定投資分文提高經濟效益創造條件,比如:出口全毛西裝面料一套,創匯不過14.5美元,加工成西裝出口,可創匯40美元,即使殺價50%,還可創匯20美元。除此以外,每出口1000萬套,還可安排就業4500人,從經濟效益看,合算得很。
有人認為,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四個現代化矛盾,沒有這回事。四個現代化,是目的,充分利用我們的充裕的勞動力來發展密集型產品,是手段,并不是矛盾。
有人認為,出口成品不如出口原料受國外市場歡迎,有這回事。外商當然不歡迎我們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擠掉他們的機制品的市場,只要我們注意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注意花色規格的不斷翻新,注意包裝,注意商標、信譽,注意不“自相殘殺”,使出口商品受到外國消費者的歡迎,外商一樣會歡迎。
七、改變能源政策,增加每單位能源的產值
照我國目前的工業結構和耗能的情況看,我們要在2000年使國民產值翻兩番,我們的能源也要翻兩番。可是,這不可能,充其量,我們的能源只能翻一番,除非,我們的勘探工作有重大突破。
能源將成為捆住我們手腳的一個嚴重問題。
怎么辦?
照我國目前情況看,平均說來:
生產10,000元重工業產品耗標準煤12.5噸。
生產10,000元輕工業產品耗標準煤2.8噸。
這就是說,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