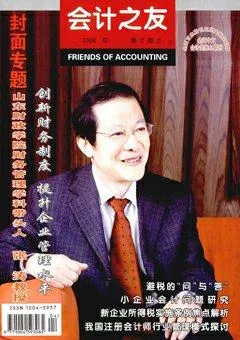避稅的“問”與“答”
【編者按】 作者蓋地是我國會計界頗有名望的教授,此稿是他針對避稅和逃稅的概念界定而寫的“問”與“答”。其中,“你”并非指具體人而泛指讀者。本文旨在增強納稅籌劃知識,以饗讀者。
問:你了解避稅嗎?
答:了解一點,但不是很多,也不一定準確,更談不上深刻。
問:如何理解避稅的“避”?
答:避稅的“避”應是規避的“避”,而非逃避、躲避的“避”。前者是在遵守稅法、尊重稅法(不影響、不削弱稅法的法律地位)規則的前提下,避重就輕、避虛就實、避負就無,追求納稅人最大的稅收利益;后者是通過違法稅法、挑戰稅法,以求稅收利益最大化,實屬偷稅、抗稅,遲早會受到法律的懲處。
問:避稅合法嗎?
答:國內外稅法中找不到根據。
問:避稅違法嗎?
答:國內外稅法中同樣找不到根據。
問:既不合法、又不違法,那屬于什么行為呢?
答:屬于非違法行為,即在法律上無法加以適用的“脫法行為”,其本質是利用稅法的漏洞和缺陷,當然還有差異等。
避稅就是避稅,無“合法避稅”與“非法避稅①”之分。既不必用“合法避稅”給自己壯膽,也不必用“非法避稅”嚇唬人。
問:你能理解納稅人的避稅行為嗎?
答:可以理解。納稅人避稅,除了作為“經濟人”具有逐利本性的內因外,還有導致避稅的外部誘因,如稅法規定的差異性、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的存在等。對政府來說,基于宏觀調控、資源配置等考慮,可能認為這是必要的,但對納稅人來說,感覺卻是稅收的不公平,稅收不公平就會催生避稅現象。另外,當稅負過重或稅收執法不嚴、不公時,也會導致避稅②現象的產生。稅收是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敏感神經,納稅人的本能反映也是對稅法、對稅收執法的一種評判。納稅人的異化反擊,既可以促進稅法的不斷健全和逐步完善,又可以促進稅收執法水平的不斷提高。
問:如果說避稅不違法,但也不道德,不是嗎?
答:“避稅”屬于法律范疇的問題,不應用道德標準去衡量。法律是下限,道德是上限。對納稅人來說,法律要求其依法納稅,即依法履行納稅義務,不以納稅多少論英雄;同時,依法享有納稅人權利──在不違反稅法的前提下,通過包括避稅在內的稅務籌劃實現稅負最輕、稅收利益最大。美國大法官勒納德·漢德有句名言:“稅收是強制征收的,而不是靠自愿捐獻。以道德的名義要求繳納更多的稅收,不過是侈談空論而已。”1935年,英國議員湯姆林爵士也曾針對“稅務局長訴溫斯特大公”一案指出:“任何人都有權安排自己的事業,以依據法律獲得少繳稅款的待遇,不能強迫他多繳稅。”
但作為社會人,納稅人也應該以公共利益為重,多盡社會責任──保護環境、珍惜資源、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等。只有勇于承擔社會責任,才能贏得社會尊重;只有認真履行社會責任,才能為構建“和諧社會”出一份力。
隨著我國社會文明的建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必將從可有可無的選項逐步轉變為必然的選擇。
問:避稅是不是有點像“臭豆腐”?
答:不,我認為像“白開水”,無色無味但有營養。
問:有人說,政府“不樂見”納稅人避稅,因此,避稅不屬于稅務籌劃。你認可嗎?
答:我不認可。如前所述,避稅是法律范疇的問題,當然應該以法律作為判斷標準。試想,如果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都以“樂見”、“不樂見”作為判斷標準,那就沒有任何同一標準了,因為每個人(不僅指自然人)的喜怒哀樂不同,真不敢設想那將會是一個什么結果。
問:政府“不樂見”納稅人避稅,是不是指避稅具有逆法意識、違背立法宗旨?
答:可能吧。但不要忘了,納稅人是普通人,不是立法者、執法者。“納稅人只負有依法納稅的義務。至于稅法宗旨的實現,則不是他們所應該也不是他們所能夠保證的。政府應該有一系列制度設計來引導納稅人的行為符合稅法的宗旨,做不到這一點,只能是政府的失職,而不是納稅人的責任。③”因此而帶來的損失,也只能由政府承擔。
問:如果納稅人因避稅而引起法律訴訟,如何進行法律認定?
答:根據“非禁即準”、“非限即許”的現代法治原則,應該認定為“合法”。
問:試舉例說明?
答:如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了稅前扣除項目,同時還規定了稅前不允許扣除項目。如果納稅人實際發生的某項費用支出,既不屬于稅法中規定的稅前扣除項目,也不屬于稅法中規定的稅前不允許扣除項目,納稅人就可以在稅前扣除。同理,在增值稅中,稅法規定了允許從銷項稅額中抵扣的進項稅額,也明確了不允許從銷項稅額中抵扣的進項稅額(不符合抵扣條件)。如果納稅人實際發生的進項稅額不是稅法中明確規定不允許從銷項稅額中抵扣的進項稅額,納稅人就可以進行抵扣,稅務機關也應該允許抵扣。
問:你喜歡或青睞避稅嗎?
答:那看我是誰。
問:你是誰?
答:如果我是政府,我當然不喜歡、不青睞避稅。很顯然,納稅人避稅就意味著我的收入減少(哪怕是暫時的、局部的);不僅是收入減少,而且要增加反避稅成本。政府的錢總是不夠用,誰不喜歡滾滾而來的錢呢?錢多好辦事嘛。但又應該理解納稅人的避稅行為,如果不能界定納稅人是偷逃稅款,那就應該不斷完善稅法。
問:如果你是納稅人呢?
答:我當然喜歡、青睞避稅。企業追求的就是利潤最大化,不,嚴格說應該是稅后利潤最大化④。試想,如果不繳稅,我的日子就會好過得多;當然,不可能(下轉第71頁)(上接第68頁)不繳稅。因為政府要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從利益交換的角度,我也知道應該納稅,但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公共性”決定了它不會與納稅人納稅的多少具有直接“配比關系”;既然如此,誰不希望通過避稅降低自己的稅負呢,而這又不影響我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問:目前理論界不是不看好“利潤”,認為收入、利潤易于導致會計(或財務)造假嗎?
答:我不否認收入、利潤易于導致會計(或財務)造假,但容易造假不等于都是造假。如果這個命題成立,那我們的千萬會計大軍不都成了“造假者”嗎?不能為了否定收入費用觀、推崇資產負債觀,而制造出這樣一個“假定前提”來。資產負債觀固然不錯,但收入費用觀也不是一無是處。以稅法導向的稅務會計肯定要堅持收入費用觀,即使在財務會計中,收入費用觀也不能說是作為資產負債觀的對立面,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只能說是現在重心轉移到資產負債觀。投資人導向的會計準則適用于公眾公司,即使對公眾公司,除了投資者,還有經營者、還有其他利益相關者呢。
問:避稅可是有代價的,你知道嗎?
答:我當然知道。任何財務行為都是有成本的,只要遵循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則,兩者差額越大越好。
問:避稅還有風險呢?
答:當然。不僅有風險,而且有諸多風險,如政策性風險、經營性風險、操作風險和執法風險等。
問:能夠絕對避免風險嗎?
答:不可能。但充分理解、認識風險并采取相應對策后,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
問:為什么會有風險?其實質是什么?
答:風險的產生源于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及我們對其認識的有限性。風險將導致避稅收益與成本的不確定,使稅務籌劃決策變得更為復雜。這些不確定性可以分為對稱不確定性和策略不確定性兩種類型,前者是指相關主體對等地獲得某一事件將來可能出現結果的相關信息,但這一信息具有不確定性;后者是指各相關主體并不對等地獲得關于未來結果的相關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出現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風險是結果差異引起的結果偏離,即期望結果的可能偏離。
問:為了降低避稅風險,有什么辦法嗎?
答:辦法當然有。(1)要熟知稅法、吃透稅法(包括稅收程序法、稅收實體法中各個層次的法規制度以及它的每一個變化),準確掌握稅法所規定的課稅要件,尤其是稅法中的禁止性規定,千萬不能去碰。(2)應采取比較穩健的籌劃方案,即要適度、適當,不可貪得無厭,不能得寸進尺;“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既要有嫻熟的避稅技巧,又要保持高度的理性,否則,很可能踏入偷逃稅款的雷區,要知道,合法、非違法與違法之間并沒有隔著明顯的鴻溝。(3)可以“外包”,即委托中介機構進行避稅籌劃,這樣還可以分散風險。
問:還有更穩健的方法嗎?
答:有。可以和稅務機關進行預約定價談判,據說這是唯一可以與稅務機關談判的內容。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企業可以向稅務機關提出與其關聯方之間業務往來的定價原則和計算方法,稅務機關與企業協商、確認后,達成預約定價安排。”如果征納雙方就關聯方交易事先達成了預約定價安排,企業與其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符合預約定價協議(APA)的安排,對納稅人來說,增強了可預期性,減少了不確定性,從而會大大降低避稅風險;稅務機關也可以降低其稅收征管成本。
問:若不與稅務機關進行預約定價談判呢?
答:主管稅務機關可以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如果認定“企業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減少其應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調整。”屆時,企業不但不能實現避稅目標,可能還會招致更大的損失。
問:有哪些常見的避稅方法呢?
答:常見的避稅方法有回避稅收管轄權法、價格轉讓法(亦稱轉讓價格法、轉讓定價法)、低稅區避稅法、成本(費用)調整法(會計政策選擇法)、融資(籌資)法、租賃法等。這些方法有的適用于國際避稅,有的適用于國內避稅,有的兩者均可適用。
問:能夠具體介紹這些方法嗎?
答:抱歉,限于篇幅,這次不能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