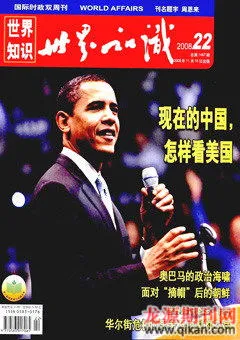混亂而充滿生機的年代
對許多日本人而言,倘加以回顧,緊隨戰敗之后的那幾年,的確構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混亂而充滿生機的年代。當時,對美國式政治模式的采納。看上去似乎比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更有希望,至少人們可以夢想未來日本將會在國際上占據一席之地,而不是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悄悄地重新進行軍備擴張。往日的苦難往往能勾起回憶,而有時懷舊的感傷會使回憶變得甜蜜。近些年來,這種個人記憶被日本國內絲毫未有衰退跡象的出版熱潮所支撐。書籍、文章、期刊專號,持續不斷地從任意可能的角度言說戰敗與占領時期的經歷,形式包括政策文件輯錄、全方位開掘的學術研究、日記、回憶錄、信件、新聞記錄、照片以至逐日的紀事年表。許多戰后時期成名的社會名流現在才剛剛謝世;而他們每一位的離去,往往會喚起對那個年代尖銳痛楚的記憶,雖然漸行漸遠,卻仍然與現實息息相關。試圖掌握租分享這些是一項令人畏懼的任務,大致說來。是因為總有如此之多可以講述,當然也有如此之多可供學習。
日本的某些特質使人們樂于封閉地看待它,而戰后的密閉空間,也極易使人將其夸張地視為“典型的”獨特的日本經驗。不僅是外來者傾向于孤立和隔離日本的經驗,其實沒有人比日本國內的文化本質主義者和新民族主義者。對國民性與民族經驗假定的獨特性更為盲目崇拜了。甚至是在剛剛過去的1980年代,當日本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宰出現時,也是其“日本”經驗的獨特性,在日本國內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盡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會通過強調差異區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區分,但是當論及日本的時候,這種傾向被發揮到了極致。
當然,戰敗后的幾年,確乎構成了一個逾常的歷史時刻。然而,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經描述過的宗教體驗那樣,在極端的困境中往往才能最好地暴露事物的本質。我發現了有關這整個國家重新起步的不尋常經歷的確切細節和脈絡,但是它們打動我,并非由于它們是外國的、充滿異國情調的,甚至也不是作為日本歷史或者日美關系中有教益的插曲而使我動心。相反,在我看來最吸引人的卻是,戰敗與被占領迫使日本人盡全力去奮斗,以異常艱苦的方式來解決最基本的人生問題,并由此反映出令人矚目的人性的、易犯錯誤的、甚至往往是充滿矛盾掙扎的行為方式。而這些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我們自身與我們這個世界的許多普遍訊息。
例如,絕大多數日本人能夠輕易拋棄15年之久的極端的軍國主義教化,這為我們在20世紀的其他極權主義政體崩潰中所看到的社會化的限制與意識形態的脆弱提供了教訓。(眾多王室被推翻而日本君主政體屹立不倒,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這本身就是一個富于啟示意義的題材。)再譬如美國的越戰老兵,如果了解到天皇的士兵戰敗歸國后是如何努力向普遍遭遇的鄙夷蔑視讓步的話,定會感到一種熟悉的震驚。同樣,對自身苦難先入為主的成見。使得絕大多數日本人忽視了他們對他人造成的傷害。這一事實有助于闡明,受害者意識是通過何種方式扭曲了集團和族群為自身建構起來的身份認同。對于戰爭罪惡的歷史健忘癥,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將之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有關群體記憶與神話制造的背景中來進行觀照,其記憶和遺忘的模式則更加寓意深長。近年來,這些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廣泛關注。在戰敗與戰后重建的混亂環境里,“責任”常常被提及,因而這并非只是日本這個島國所關心的問題。
當日本人在他們的歷史中仔細搜求,以便為他們的“新”情況作參照的時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礎、有原則地反抗軍國主義的事例,或者固有的懺悔和贖罪的表示等等,他們提出的例證自然是千真萬確。然而他們所做的,不過是任何人在面對創傷性的巨變時都會去做的。他們在發現——如果需要,甚至發明——某些可以依賴的熟悉的經驗。日常語言本身就是一座橋梁,使許多人不必完全經歷心理混亂,就能夠由戰爭狀態跨越到和平的彼岸。因為許多戰時的神圣詞匯、標語口號,甚至是流行小說,在戰后被證明可以完美地適應全新的闡釋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體。再者,將熟悉的語匯賦予新的意義,也是人們將實實在在的變化合理化與合法化的一種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