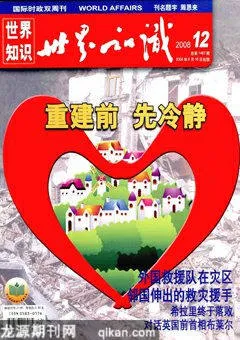震災呼喚安全的人口發展
穆光宗
法學博士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汶川地震災難使我們重新認識了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使我們認識到大自然的生態體系中存在著至少三類人類居住區,即人類居住環境適宜區、人類居住環境危險區和人類居住環境不適宜區。人口的合理分布必須考慮到人類活動對脆弱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以及脆弱的生態環境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制約。如果我們能依據生態整體主義和以人為本原則的雙重考量,根據歷史資料的文獻記載和環境科學綜合評估,建立起科學的、符合實際的人居環境評價體系,分出三類人居地區,從而有助于我們做出科學的人口居住規劃。
首先,人類居住環境適宜區。一方面,人類人口的分布和集聚不會遭遇到嚴重的環境制約和潛在的環境威脅,如地震等地質災害、水旱災害、颶風等;另一方面,人類要在一定的文化和管理下實現環境友好的生產、生活和活動方式。歷史上長期風調雨順、沒有災難的地方,就是我們理想中的“桃花源”。
其次,人類居住環境危險區。一方面,我們需要對生態敏感脆弱帶的人類活動提出環境警告,同時需要將人口適當疏散、外遷到人類居住環境適宜區。如,四川青川縣在本次地震中受到了重創,由于當地自然環境惡劣,無法妥善安置全縣所有受災群眾,縣委決定動遷三萬人。但由于這種環境難民式的人口遷移是政府組織的,因此帶有引導性甚至強制性,需要在充分了解民情、尊重民意的基礎上開展,高度關注這種特殊移民的環境與文化適應性問題,才能達到維護好民權和生態的雙贏目標。另一方面,我們要對無法外遷的人口實現“新安居工程”。過去通常所說的安居工程是指解決住房難問題,實現的目標是居者有其屋。新安居工程還必須考慮人居的環境安全,實現“居者有其屋,居者固其屋”。這次最讓人痛心的是,很多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地震,而是亡于危樓。那些被巨大悲痛包圍的家長們痛心地看到了一個事實:天災不可違,人為最可恨!據報道,吸取我國汶川大地震血的教訓,日本打算花費5億日元加固中小學校校舍,使之成為避難所。中國將來還會發生大地震,然而我們準備好了嗎?楊東平曾說,全國農村“普九”欠債高達500億元,那么不得不追問的一個問題是:全國中小學還有多少危房危樓讓人提心吊膽?!
再次,人類居住環境不適宜區。在理論上,我們需要24小時不間斷的環境監測預警;在人口對策上,最好的選擇是實施“零人口分布”。例如,面積廣大、處于高寒的可可西里地區歷史上一直就是無人區,但卻是我國珍稀動物藏羚羊的天堂。由于藏羚羊的皮毛有很高的市場價格,因此導致了一些反生態人口(盜獵分子為主體)的侵入。堅決實施“零人口分布”是維護脆弱生態系統中資源環境自我平衡的正確選擇。在地質災害頻乃、生態系統脆弱、環境需要維系原生態的情況下,規劃“零人口分布”,阻斷人類活動對脆弱生態的擾動,恢復自然的原生風貌和再生能力,應該是比較明智的做法。汶川大地震產生了一些次生災害,如在四川災區形成了30多處堰塞湖,一旦潰決,產生的次生災害將非常嚴重。所以,提前遷移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本次地震災難引發我們思考的第二個人口問題就是大批計劃生育家庭的結構損傷問題。筆者曾經提出計劃生育家庭四分類的觀點,即計劃生育家庭包括了至少有一個男孩的強勢家庭、雙女戶弱勢家庭、獨生子女風險家庭以及父母或者孩子傷病殘缺的殘破家庭,后兩類家庭的風險和困難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根據目前的數據,四川省遇難的師生人數約占本次地震遇難人數的12%,其中遇難的學生中不少是獨生子女,這再一次以殘酷的事實證明了筆者于2004年提出的“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這一判斷。親人的離去和傷殘,是地震帶來的難以言表的傷痛。在聚源中學,人們聽見一位媽媽在責備死去的孩子:“我們辛辛苦苦把你養大,你就這樣突然走了?!你怎么可以讓我們孤孤單單變老?”
人口學理論指出,在傳統社會,為了應對高死亡率,需要有高出生率來平衡,也就是說,需要補償性生育,這是人口轉變早期階段的高位均衡機制。以“一胎化”為主導的生育政策在突如其來的地震災難面前顯示了自身固有的脆弱性和風險性。我們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前進的道路上鋪陳著種種危難和風險。在面貌萬端的突發性災難面前,獨生子女家庭是最不堪打擊的脆弱家庭,其風險性就在于惟一性。獨生子女風險家庭可以在一瞬間變成悲苦的殘破家庭。
結合中國國情,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家庭和國家的人口損失,我們必須通過必要的生育儲備來建構人口安全發展的政策機制。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人口發展所遭遇的地震災難再次提醒我們,生育儲備戰略對于民族的繁榮、家庭的發展來說都完全必要。少生不等于獨生。如何事先規避計劃生育家庭的孩子成長風險,必須在生育政策的完善上尋求突破的契機。地震等風險事件再次提醒國人和政府,包含了人口安全訴求的“男女性別平等,城鄉統開二胎”的政策取向,才是符合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本質的人口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