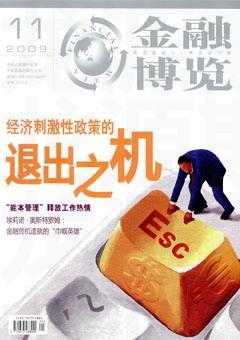明清金融業與政府的關系
孔祥毅
金融機構從商業中分離出來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由小到大,由簡而繁,服務內容越來越多,對社會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僅受到了商人們的歡迎,而且也引起了政府的關注。當然,貨幣商人穩定的經營環境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而政府也逐步發現民間金融機構有必要充分利用。特別是清代中后期,貨幣商人千方百計迎合官員與政府的需要,政府也先后經歷官款存當生息,官辦錢局管理調節貨幣、委托票號代理金融事務,以至自辦近代銀行的過程。
官款存當生息與錢商融資政府
隋、唐時期,就有官辦的放款取息的一種金融機構“公廨”,收入歸財政支配。不過隋朝公廨是地方官府直接經營,“回易生利,以給公用”,以解決地方政府公用經費不足。唐代的公廨,在諸州有“捉錢令史”,資金來源以稅錢充本,全部高利貸給有償還能力的“高戶”經營,謂之“捉錢戶”。官府不管具體經營,由捉錢戶以公廨錢為資本進行貿易,質庫、高利貸等經營。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世宗對宰臣說:“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為本,小民苦之。若官為設庫務,十中取一為息,以諸官吏廩給之費,似可便民。”隨后在中都,南京、東平,真定等處開設官辦質庫,稱為“流泉務”,制定了管理辦法,后推廣發展為28所。元代也有官辦當,質庫,稱廣惠庫或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明代商業發展,當鋪,錢莊增加,盈利頗豐,政府對當鋪錢莊征收稅捐,以充財政。清初有將財政收入借給商人生息的事情,后來備省效尤,將稅收存當生息,或直接開辦官當鋪。康熙三年(1 664年),政府向官辦商辦當鋪收取稅款,年稅銀5兩。
商人對候補官員放款,不僅利息很高而且加收“扣頭”,有時使得官員長期負債以至于貪污受賄。故乾隆十四年(1749年),政府禁止商人對選官放京債,但是實際上禁而不止。在外蒙古地區,按清朝定制,各王公要定期晉京納貢和輪流值班,開支費用浩繁,遠途攜帶也不方便,旅蒙商大盛魁等便為其提供信用貸款,其貸款的本息,習慣上由各旗按照所管轄地區人丁數目分攤。光緒十七至十八年(1891—1892年),外蒙古扎薩克圖汗盟長阿育爾公三次向大盛魁借用現銀8660兩,全部分攤各旗牧民償還。在王公晉京值班居留期間,其服飾、送禮、宴客、朝佛游覽以及生活事務,都由隨行的放印票賬人員代為辦理,大盛魁對此滿足供應,也攤派給所屬牧民,收賬時一并回收。如果屆時不能收清,轉為印票賬,按月行息,直到全部收回為止。因為這種信用貸款,借者要向資金提供者出具蓋有王公或旗署印信的借款憑據,故稱為“印票”。大盛魁印票莊除對蒙古王公提供信用貸款之外,還有信用貸貨,即賒貨放貸,商人馱著各種貨物到各部,旗,把貨物賒銷給王公、貴族或廣大牧民,按賒銷貨物的價款折成銀兩,作為放印票賬的本金,按月計息,到期以牛羊馬牲畜作價歸還欠款。印票上寫著“父債子還,夫債妻還,死亡絕后,由旗公還”的字樣,盟旗政府既已出具印信,商人的本利償還當然不會有風險。
清代,民間金融業行會也千方百計取信政府和官員,希望得到政府和官員的支持,而業務活動又千方百計不受政府制約,通過自己的行會組織,管理行內事務,約束會員避免內部爭斗,一致對外。例如清光緒十五年(1 889年),綏遠市場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錢,冒充法定制錢流通,為維護經濟秩序,當地銀錢業各商會積極配合當局,整頓貨幣市場,在三賢廟設立交換所,讓人們以同等重量的沙錢換取足值制錢,并將沙錢熔毀鑄成銅碑一塊立于三賢廟內,上書“嚴禁沙錢碑”,碑文寫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轍,稟官究治,決不寬恕。”同樣,南茶坊關帝廟內《整立錢法序》也記述了錢業行會寶豐社協助政府整理“短百錢”問題的歷史。
票號承辦政府金融
票號業務本以商號和個人為對象,但在19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其與政府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逐漸代理了政府金融。
清代財政制度規定,各省征收賦稅,存入公庫,在中央批準的開支內動用庫款,所余款項由中央調劑,運解中央者稱為“京餉”,運解入不敷出之省份者稱為“協餉”。京餉、協餉的撥付一律裝鞘運現,“不得假手商人胥役”。但是自太平天國和捻軍運動爆發后,交通常常被阻斷,京餉不能運現送達,政府不得不在同治元年(1862年)批準各省督撫將京餉覓殷實商號“設法匯兌”。當年有閩海關通過票號,匯兌三筆白銀20多萬兩。次年又有粵海關、湖北、江西等十余省關匯款66萬兩。在同治元年到光緒十九年(1862~1893年)的31年間,票號為政府匯兌京餉6159萬余兩。繼而各省協餉也照此辦理,據不完全統計,同治六年到光緒十九年(1867~1893年)共匯兌甘,新協餉達460余萬兩。票號還為洋務運動匯解經費款項和海防經費、鐵路經費輪船經費。自1 9世紀50年代開始,票號與清政府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步步升級,成為清王朝的財政支柱。此間,咸豐時期(1 851~1861年)為票號與政府的最初結托,同治元年到甲午戰爭前夕(1 862~1893年)是進一步結合,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1894—1911年)為票號與政府結合的頂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度支部在京各金融機構存款中,僅存大德通、大德恒,義善源存義公幾家票號的款項就達2064596兩,占度支部在外存款的30%,而存入國家銀行大清銀行為61%,外國銀行8%。票號吸收生息銀兩中,僅商部在上海合盛元票號就有53萬余兩。由于票號占有如此巨大的政府存款,不僅可以承辦巨額匯兌和墊匯,同時又可以對政府放款。據《大公報》報道,宣統三年(1911年)十月,經度支部大臣紹英向內閣大臣袁世凱請示批準,“向京師各票莊借銀五百萬兩,當外款(外債)議定后再行發還。”但當政府要員赴票號議商時,各票號均因“前欠各號之款已愈七百余萬,歸還尚無著落”,均裹足不前。
票號與政府及其官吏的最初結托,是通過三個門徑一是資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以至走馬上任。咸豐以后,“各省試子入都應試,沿途川資,概由票莊匯兌。川資不足,可向票莊借款。對于有銜無職的官員,如果有相當希望,是靠得住的人,票號也喜歡墊款,替他運動差事。既放外官,而無旅費赴任者,也由票莊先墊,寒儒窮士感激票莊濟急,一旦發達,則公私款項盡存于票莊。”二是代辦,代墊捐納和印結。清政府從咸豐朝起大開捐納,按虛實官銜等級定價,輸銀加封。“文官可至道臺,武職可待為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并賣虛銜,加花翎而寬封典。票莊乘機居問攬辦,得利優于其他匯款。”票號為其打聽消息,協助其打通關節。已放實官者,為了取得更高一級的職務,亦請票號代辦“印結”(印結是一種簽有印鑒的證明文書,官吏向上級辦理印結,可以由票號代理,由代辦捐納發展而來,后成為票號的一種普通業務)。因為捐納人直接向戶部交款,必有若干挑剔,或層層關卡剝皮,而票號上結尚
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分別等級行賄,逢年過節,必贈款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對王公大人,均在相公下處殷勤招待。當報捐者取得實官,自然對票號感激不盡,個人之私款,賄賂之橫財,盡存票號,票號亦代守秘密。三是票號財東與經理人員直接捐納報效,買取官銜和封典。咸豐六年(1 856年)正月初十咸豐皇帝對內閣指示:“山西太谷縣議敘員外郎監生覌億,著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并賞戴花翎;伊子議敘守備職銜魚不鋪,著注銷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陜西分缺先補用,并賞戴花翎,祁縣后選郎中孫郅,著以道員不論單雙月分缺先選;伊子監生孫中倫,著賞給舉人……太谷縣舉人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并賞戴花翎。”日昇昌票號的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經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亦均受封為“宜人”、“夫人”。據不完全統計,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山西各票號和賬局捐資以“鑄炮”共白銀34萬兩,錢70000吊,同年十月下旬,日昇昌,天成亨等十三家票號又捐銀6000多兩。1 852—1853年山西票號商人捐款共達267萬兩。票號分號的經理,大都與所在省份的督撫交往甚厚,總號調任分號經理也很注意與官吏的調任相協調。協成乾票號駐廣州分號經理無一任不與粵海關監督為磕頭之交,所以能夠長期經手粵海關稅款存儲及向國庫匯解業務。從同治四年(1 865年)以后,票號業務重心由內地逐漸向邊遠和沿海開拓,尤其是對外通商口岸,已經發展成為清王朝的財政支柱,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是代辦捐納匯兌公款。票號最初是充當政府捐納籌餉的辦事機構,后來爭取政府公款匯兌和解繳稅收業務。按照政府常規,公款上解,全系押運現銀,票號代匯公款,政府內部爭論不休,經票號多方努力,最終獲得通過,其理由如此:第一,農民運動使道路不靖,匯兌比解現安全;第二,解現費用昂貴,匯兌相對費用低廉;第三,南省款項由水運上解經天津入京須支付海運保險費,保費大大超過匯兌時的匯水,又有海盜威脅;第四,地方稅款所收銀兩成色大多不佳,不能上解,就地熔煉加工,又增開支,款項必有虧空;第五,由于地方稅款往往不能按時收訖,常常不能準時起解,不得不向票號借貸,票號只同意借墊匯兌,不借現銀上解。故咸豐同治以后,裝鞘解現日少,由票號匯兌日增。據不完全統計,同治四年到光緒十九年(1865~1893年),魯、贛、湘、鄂等各省及江海,粵海各關通過票號匯兌公款達15870余萬兩。同治元年(1862年)為10萬兩,光緒十九年(1893年)擴大為5250萬兩,32年增長到52倍半。
二是借墊京餉協餉。票號為各省關借墊京餉協餉,解救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急。諸如“西征薪餉”、伊犁協餉烏魯木齊月餉,奉省捕盜經費等等,本由戶部指派各省關將稅款直解用款地點。但因各省關收入困難,用款單位則“急如星火”,各省關不得不向票號借款匯解。據部分清檔統計,粵海關從同治三年到光緒十六年(1864~1890年)先后請協成乾,志成信、謙吉升、元豐玖,新泰厚票號借墊清廷指派“西征”軍費、洋務經費等款項142萬兩。其他如閩海、浙海、淮安、太平各關與廣東,福建,四川等省,均大量由票號借墊。光緒十年(1884年)福州將軍兼閩海關負責人穆圖善給皇帝的奏折說:“歷年所以無誤餉款者,全賴各號商通挪匯解。”云南省歷年鎮壓烏索、景東、開化、騰越、順之各處少數民族起義“緊急軍需……先后向各商號借用銀39.81萬兩,填給庫收,令付各省分撥歸還。”“滇省庫藏空虛,住特此商號二三家(天順祥云豐泰、乾盛亨票號)隨時通融,稍免潰之憂。”據左宗棠說,從同治五年到光緒六年(1866—1880年)的十四年中,其軍隊在湖北、上海、陜西向票號借款8323730兩,支付票號利息達到499591兩。
三是籌借匯兌抵還外債。據史料記載,阜康票號財東胡光墉為清政府鎮壓捻軍和西北回民起義,向怡和洋行、麗如銀行等外國商人借款,從同治六年到光緒七年(1867~188t年)先后六次,共計1595萬兩,均在上海辦妥,由票號匯往山西運城或西安,轉左宗棠軍隊提用。所借款項,以海關稅作抵,仍由票號經辦將各海關稅收匯往上海外國銀行還本付息。《馬關條約》簽訂后,對日賠款2億兩,接著又增加贖遼費3000萬兩,當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尚不足8900萬兩,為籌還賠款,被迫三次舉借外債,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國借款,折合白銀1.12億兩,以蘇州、松滬、九江,浙東貨厘及宜昌、鄂岸鹽厘擔保,每年計還本付息1 200萬兩,加上清政府的其他外債還本付息和開支,每年需還2000余萬兩。戶部將所增開支按省分攤,不管是用鹽斤加價還是地丁貨厘附加,必須按時將白銀匯往上海還債,由幾家票號包攬了各省債款匯兌四川省由協同慶,天順祥票號包攬,云南省由同慶豐,天順祥包攬,廣東省由協同慶票號包攬,廣西由百川通票號包攬,浙江省由楊源豐、源豐潤票號包攬,安徽省由合盛元票號包攬,江西省由蔚盛長票號包攬,湖南省由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票號包攬,陜西省由協同慶票號包攬,福建省由蔚泰厚、源豐潤票號包攬,河南省由蔚盛長,新泰厚,日異昌票號包攬,山西省由合盛元,蔚盛長、日昇昌,協成乾票號包攬。
四是代理地方金庫。票號代理財政金庫,最初僅僅是少數省關,以后互相效尤,大多交由票號代理。當時《申報》評論說:“無論交庫,交內務府、督撫委員起解,皆改現銀為款票,到京之后,實銀上兌或嫌不便,或銀未備足,亦只以匯票交納,幾令商人掌庫藏之盈虧矣。”后來票號直接為中央政府融通資金,據檔案記載:“倭韓事起,征兵購械,需款浩繁。本年(1894年)八月間,當經臣部(戶部)解派司員,向京城銀號,票號借銀一百萬兩,備充餉需。”接著戶部又要各省息借商款,解部備用,并訂有《息借商款章程》,日昇昌票號漢口分號曾為湖北省提供借款140萬兩。源豐潤票號廣州分號也為政府提供借款10萬兩。在江西,這種借款,“隨收隨交蔚長厚,天順祥兩票號匯數存儲,另立清摺計數”,聽候藩臺文批,發交該二號匯解。票號還為政府認購和推銷“昭信股票”,1 898年,清政府以鹽稅擔保,發行“昭信股票”,規定認購10兩以上者給予獎勵。清政府把辦理股票推銷業務的任務,交給了票號和幾家滿族人開辦的錢莊承辦,其中有百川通,新泰厚、志一堂(志成信),存義公,永隆泰5家票號和恒和、恒典、恒利、恒源4家錢莊。當時在京城的48家票號每家認購股票1萬兩,共計48萬兩。由于流弊太多,社會抨擊,被迫在同年停止了這種股票的發行。庚子事變中,票號承辦皇帝太后西逃財政事務,經太原時住山西巡撫衙門,慈禧宴請駐太原各票號經理,并請求借款。大德恒票號太原分號經理賈繼英帶頭,慷慨應允借銀40萬兩,事后賈繼英被召入京,賜穿
黃馬褂。
五是借墊匯解庚子賠款。光緒二十九年(1901年)九月,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辛丑條約》,規定付給戰爭賠款白銀4.5億兩,年息四厘,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9.8億余兩。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騰挪出一部分款項外,其余則全部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外國侵略者。票號僅匯往上海歸還“四國借款”和賠款就達9400萬兩,占到66.30%,龐大的賠款匯解、墊借匯兌,全部由票號承辦,由駐上海的票號集中交付匯豐銀行,德華銀行、華俄道勝銀行、法蘭西銀行、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等外國在華銀行,轉到外國侵略者手中。
由于票號商人與政府的密切關系,票號盈利迅速增加,如大德通票號四年一個賬期進行一次紅利分配,光緒十四年(1888年)每股分紅850兩,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每股分紅4024兩,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紅17000兩,利潤是甲午戰爭前的20倍。
政府創辦官錢銀局和近代銀行
清初,雖然官辦錢銀號已經開始,不過與后來的官錢局和官銀號是不同的。史料記載,康熙六十一年(1 722年),議將“平糶官米錢交五城市易以平錢直”。“康熙六十一年,大、宛兩縣設立官牙,議平錢價。”雍正九年(1 731年)上諭,“朕思錢價之不能平減者,因兌換之柄操于鋪戶,官府不司其事,是以小人圖利,得任意多取以便其私耳。若照五城減價糶米之道,將搭放兵餉之錢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設一局,兌換于民,照鋪戶之數,多換數十文,以銀一兩換制錢一千文為率。如此,則錢價不待禁約,自然平減,干民用似有裨益。”可見,當時只是為了平抑銀錢比價。乾隆十年(1745年)“以錢價漸減,奸民每以在京賤買之,官錢運至近京錢貴之地,興販射利,議將官局停止。”嘉慶年間,為傾熔銀錠事務的檢查,不使“稍滋弊竇,粵海關等曾設立官銀號”。“道光年間所設官號錢鋪五處,分儲戶,工兩局卯錢,京師俸餉照公費發票之案,按數支給,以錢代銀。”政府對官錢局的開辦,停止的交替變化,看得出其主要目標在于平抑錢價,調節貨幣流通。至于放款生息問題,康熙到乾隆中期雖然為增加收入,獎勵旗兵,但并沒有制度化。在乾隆中期以后則明顯地為了盈利而“發商生息”,甚至沒有本金向商借錢再發商生息。但是在太平天國運動以后,清政府中央與地方均開始設立官辦金融機構,不僅名稱有某某省官錢局、官銀號,而且官銀錢局職能和業務也發生變化,它們發行紙幣,兌換銀錢,調節銀價,熔鑄銀錠,代理省庫,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辦理貼現,匯兌,買賣生金銀等等,一步步趨向近代銀行。
鴉片戰爭以后,外國銀行陸續進入中國,到清末先后在中國設立機構的外資銀行不下40家。國內商人亦引進西方商業銀行的經營技術,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國通商銀行,綜合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結算等金融業務。在此之前,清政府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人提出創辦官銀行,但是直到1 905年才有戶部銀行正式成立。軍機大臣主持財政處的奕勖在給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說,“中國向無銀行,各省富商所設票號,錢莊大致雖與銀行相類,特公家未設有銀行相與維系,則國用盈盈之大局,不足資以輔助……現擬先由戶部設法籌集股本,采取各國銀行章程,斟酌損益,迅速試辦銀行,以為財幣流轉總匯之所。”兩年后又有交通銀行成立。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貨幣代理國庫,管理外匯,是中國最早的政府的銀行和發行的銀行,同時均從事普通銀行業務。
到清末,中國人無論在民間或者在政府,已經將金融業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