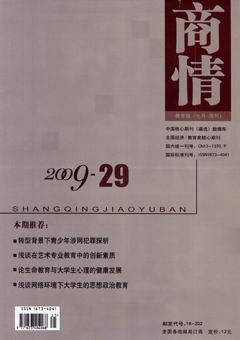“月亮”代表“我的心”
蘇芳菱
【摘要】毛姆童年多舛,冥冥中也影響了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細膩、敏感而又尖銳。在他的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中,主人公思特里克蘭德通過放棄社會生活、追求精神自由來擺脫困境。有人認為思特里克蘭德是個不負責任、道德敗壞的人渣;也有人認為他是個十足的惡棍、恩將仇報的混蛋;更有人認為他就是個只知道畫畫的瘋子、偏執(zhí)狂。那么毛姆為何要塑造這樣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形象?本文將結合毛姆生平簡要解析他的創(chuàng)作動機。
【關鍵詞】流浪 抉擇 夢想 現實
初見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不明白作者為何要把這兩個毫不相干的名詞放在一起做書名,于是帶著些許好奇開始了閱讀之“旅”。通讀幾遍下來,作者的用意也終于被我參透——月亮高高掛在天上,美麗卻觸手不可及;六便士再稀松平常不過,現實得人人都擁有。月亮和六便士分別象征著每個人心中的夢想和生活中的現實,然而這兩者卻不可兼得,究竟舍棄哪個保留哪個,是每個有夢想的人所面臨的問題和困惑。
一、流浪——讓漂泊的心找到精神的家園
主人公思特里克蘭德先是放棄在倫敦令人羨慕的家庭、事業(yè)、地位乃至一切,只身前往巴黎學習繪畫。然而這個浮華喧囂的藝術之都并不是思特里克蘭德的夢想之地,反而成了捆綁他精神自由的繩索。于是他又輾轉來到馬賽,在那里潛心畫畫,不問世事。之后,他再次離開馬賽,最終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小島找到了無限的創(chuàng)作靈感。在那里,他幾乎不與外人交往,也不為生活瑣事牽絆,創(chuàng)作了駭世驚俗的巨大壁畫。在他患麻風病臨死之前卻命令島上的妻子愛塔將他的尸體與巨畫一起焚燒,似乎他對內心完美精神的追求和探索會隨著巨畫的盤涅而獲得重生,重又開始追尋生命的意義和精神的完滿,直到永遠。可以說,思特里克蘭德是在流浪中尋找精神皈依,又在皈依中尋求精神升華。
在小說《月亮和六便士》發(fā)表時,也就是1919年,毛姆45歲,與西莉結婚已3年,但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因為西莉根本不了解毛姆,而毛姆對她的虛偽做作也極度厭惡,他們之間經常發(fā)生口角。當時的西莉喜歡邀請倫敦的達官貴人到家中舉辦晚會,毛姆卻不愿一個晚上接一個晚上地在晚會上消磨時光,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又起來寫作。這些均被生動地移入《月亮和六便士》中。思特里克蘭德的妻子阿美也很喜歡宴請文人墨客。唯一不同的是她從未和思特里克蘭德發(fā)生過任何爭吵,他們的家庭生活“平靜得像條小河”。在之后的情節(jié)中,毛姆也幾次借思特里克蘭德之口表達了他選擇流浪的原由。
……我發(fā)現勃朗什一點一點地施展起我妻子的那些小把戲來。她以無限的耐心準備把我網羅住,捆住我的手腳……唯一想的是叫我依附于她。
我不需要愛情。我沒有時間搞戀愛。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不再受任何阻礙地全心投入到我的工作上去……
無論是思特里克蘭德的妻子阿美,還是其情人勃朗什,都是毛姆妻子西莉的縮影。也正是為了擺脫西莉的控制和束縛,毛姆才在一戰(zhàn)爆發(fā)后志愿到法國參加紅十字會。在那里,他結識了年輕的美國勤雜兵杰拉爾德。那時毛姆已年過四十,杰拉爾德不過二十一二。毛姆口吃嚴重,而杰拉爾德能言會道,兩人在一起正好形成互補。這對同志在之后的幾年一起游歷了中國、印度、拉美等國家。毛姆從此徹底擺脫了西莉的婚姻枷鎖并重獲自由,得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文學創(chuàng)作。而思特里克蘭德從倫敦到巴黎,從巴黎到馬賽,從馬賽到塔西提的流浪生涯也正是為了擺脫女人、情欲等等各種與繪畫不相干的桎梏,最終找到精神家園。
二、抉擇——讓夢想照進現實
思特里克蘭德毅然決然地拋棄一切去巴黎學畫,他那義無返顧、棄而不舍的精神更是令人欽畏。那么毛姆為何要把思特里克蘭德刻畫成這樣似乎不識人間煙火、對繪畫如癡如魔、舉止粗野卻又令人不得不崇敬的人呢?
我很懷疑……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愛的環(huán)境里,淡泊寧靜、與世無爭,這難道就是糟蹋自己嗎?與此相反,做一個著名的外科醫(yī)生,年薪一萬鎊,娶一位美麗的妻子,就是成功嗎?
“……一個作家,不僅是坐在寫字臺邊才是從事寫作,終日他都在寫作,當他在思考時,在閱讀時,在體驗生活時,他都是在寫作。他所寫的是他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是他見到過的每一個人。他吃早餐時是在寫作,他求愛時是在寫作,這是一種無休止的工作。寫作占據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思。”
“你一心一意想的全是你的創(chuàng)作,你可以為它拋棄一切,不對嗎?愛情、寧靜、悠閑、幸福,為它你可以背叛一切,對不對?你的創(chuàng)作總是高于一切。你已經為它獻身;連你的靈魂都不屬于你自己了……”
毛姆和他筆下的思特里克蘭德,調侃的說,就是現實中和虛構中的兩個工作狂,本質是相同的——對自己所喜愛的事業(yè)永不停歇的追求。毛姆曾坦言說,他為自己的成功,哪怕是最微小的成功,都付出了代價。是的,因為10歲就成了孤兒、因為口吃、因為身材矮小相貌丑陋,毛姆從小就不被人疼愛,也不得不成為旁觀者。于是為了彌補童年時缺少的關愛和應有的尊重,他拼命地想要成功,想要得到大家認可。然而,傾盡一切所換來的,只是“二流作家的佼佼者”,毛姆曾多次在公共場合自嘲地說。這句自我評價,在我看來,和曹雪芹的“一把心酸淚,誰解其中味!”幾乎如出一轍。
不同的是,毛姆并不像思特里克蘭德那樣走火入魔般排除一切與繪畫無關的事物。他沒有、也不能完全擺脫現實物質利欲的誘惑。為了血洗幼年時因自身缺陷遭人白眼的恥辱,他竭力追求功名財富物質利益,以此來尋求物質和心理補償。因此當成功唾手可得,他卻反而更加覺得虛無貧瘠。現實和夢想就像水和火一樣勢不兩立。他越是想要奮不顧身地追求夢想,就越是擺脫不開生活的枷鎖,仿佛身陷沼澤,越用力掙扎反而越陷越深。所以他的矛盾和痛苦只能通過將思特里克蘭德塑造成不為塵世所牽拌、不為世俗所沾染的精神高尚的藝術家形象來發(fā)泄,從而實現另一個自己,另一個真實的自己。
參考文獻:
[1]陳果安.小說創(chuàng)作的藝術與智慧.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4.
[2]陳召榮.流浪母題與西方文學經典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羅賓?毛姆著,薛相林,張敏生譯.憶毛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
[4]毛姆著,傅惟慈譯.月亮和六便士.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