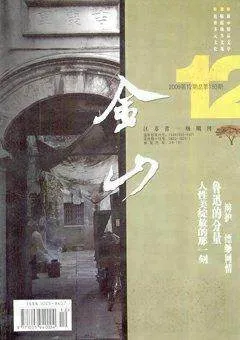下跪
余顯斌
許久許久,他醒悟過來,“咚”地一聲跪了下來,淚流滿面地用不太標(biāo)準(zhǔn)的中國話喊:“媽媽——”
戰(zhàn)敗了,他在逃跑,駕駛著一輛摩托車。車后,坐著他的長(zhǎng)官。
他感到風(fēng)聲鶴唳草木皆兵。
長(zhǎng)官曾經(jīng)告誡過他和他的戰(zhàn)友,在這個(gè)國家,只有燒殺掠奪,或者戰(zhàn)死,沒有第三條路走。“我們?cè)谶@兒殺的人太多了,這塊土地上,每一個(gè)軍人或居民抓住我們,都會(huì)將我們剁成肉醬的。”這話,如冰凌一般,刺得每一個(gè)士兵渾身發(fā)抖,不寒而栗。
因此,每一次,他們都帶著一種絕望的心情走上戰(zhàn)場(chǎng)。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表面上硬氣,骨子里,每一個(gè)士兵都是由于害怕,怕受到更殘酷的報(bào)復(fù),所以,才采取作戰(zhàn)到死,絕不當(dāng)俘虜?shù)淖龇ā?/p>
可他不想死,他想逃出去。
他的家里,有一個(gè)瞎眼的母親,慈祥得如山里的泉水。走的那天,瞎眼母親送他,一直送到村口,囑咐:“無論打到哪兒,兒啊,記住,母親都會(huì)在村口等你回來。”
他含著淚,點(diǎn)點(diǎn)頭,走了。然后,跟著大部隊(duì)離開櫻花之地,來到一衣帶水的這兒,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在這塊土地上,真的,他們作的惡太多了,有時(shí),在夢(mèng)中,連他也會(huì)不寒而栗。醒后,望著窗外一片潔白的月光,他會(huì)感到一陣迷茫:自己還是過去的自己?jiǎn)?還是櫻花樹下那個(gè)純樸的青年嗎?
這其中有一件事,讓他至今難以忘記。
一次,他們抓住了一個(gè)抗日分子,為了殺一儆百,他們把那個(gè)小伙子帶回了村子,捆綁在樹上。長(zhǎng)官命令,讓他用刺刀把那個(gè)人刺死。
那是一個(gè)三十多歲的漢子,靠在樹身上,鐵塔一般,瞪著雙眼。他舉起刺刀,無來由地竟有些心慌氣短。就在他的刺刀將要刺出去時(shí),一聲嘶啞的呼喊:“兒啊,你們不要?dú)⑽业膬?”隨著聲音,一個(gè)白發(fā)老人撲了過來,一把抱住那個(gè)漢子,哭著,哀求著他們。這一刻,他想起了自己的瞎眼母親。
“娘,不要求他們,他們不是人,是畜生。”漢子喊。
那位老母親仿佛沒有聽見,仍然不停地哭喊哀求道:“要?dú)?求你們殺我吧。”他回過頭,看到長(zhǎng)官眼中的濃濃殺機(jī)和狠狠下?lián)]的手勢(shì)。一閉眼,手中的刺刀狠狠地刺進(jìn)了那個(gè)漢子的心窩。
那位母親一身慘叫,暈倒在地上。
以后,在夕陽下,站在炮樓上,他常看到一個(gè)老太太,在夕陽下提著個(gè)籃子,一手拄著根棍子——就是那位母親。她的家也在那次被燒。她在夕陽下慢慢地走著,沿村乞討著。每次望到她,他的心中,總會(huì)產(chǎn)生一絲愧疚。
現(xiàn)在,他們敗了,他知道,這個(gè)村子的人也不會(huì)饒恕他們,如果落在他們手中,他們會(huì)活剝了他。
他駕著摩托,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飛奔著。身后,長(zhǎng)官在一聲聲催促:“快,快,后面的馬隊(duì)追上來了。”他聽了,心里更慌,心跳手顫,突然感到摩托一歪,撞在一塊石頭上,連人帶摩托摔在一個(gè)深溝里。
長(zhǎng)官咒罵著,連忙爬起來,抽出槍。他也抽出槍,兩個(gè)人趴伏在土溝里。
他們的敵人追上來了,已包抄了過來,同時(shí)喊話:“繳槍不殺,趕快投降!”長(zhǎng)官開槍了,喊話聲停了。過了一會(huì)兒,又傳來喊話聲:“如果不投降,我們就扔手榴彈。”
他的額頭流下了汗,他想起了家鄉(xiāng)村口的母親,想起母親的含辛茹苦。他站了起來,舉起了手。
“八嘎!”身后,一聲咒罵,長(zhǎng)官的軍刀一揮,帶著風(fēng)聲掃來。他聽到風(fēng)聲,忙一轉(zhuǎn)身,刀鋒劃過右臂,一道長(zhǎng)長(zhǎng)的傷口裂開,汩汩地流出血來。就在長(zhǎng)官第二刀揮出時(shí),對(duì)面槍響了,長(zhǎng)官晃了晃,倒了下去。
他也晃了晃,但仍咬著牙,捉著胳膊堅(jiān)持著:他可以做俘虜,但不可丟了皇軍的骨氣。
被軍醫(yī)包扎好,他被收歸俘虜隊(duì)伍。
那是一個(gè)雨天,他掛著繃帶,和其他俘虜一塊兒在泥地里蹣跚著,又一次經(jīng)過他們蹂躪過的小村。小村的居民們站在路邊,一個(gè)個(gè)望著他們。
他們都做好了被打,甚至被咬、被殺的準(zhǔn)備,可是,小村的人群一片寂靜一片沉默,沒有一個(gè)人想動(dòng)手報(bào)仇的意思。
突然,路的那邊,一個(gè)花白頭發(fā)的老人走過來,一手提籃一手拄著棍子。他心里一緊。認(rèn)出了她——那個(gè)被殺漢子的母親。老人蹣跚著,籃子里有一件夾衣。她默默地走過來,看著他們,看著他們行進(jìn)著,默默的。
經(jīng)過她身邊時(shí),他偷偷地低下了頭。或許由于冷,或許由于害怕,他微微地顫抖著。突然,老人向他走來。他鬼使神差地停了下來:自己作的惡,就讓自己來承擔(dān)吧。他閉上眼,倔強(qiáng)地?fù)P起頭。
既然災(zāi)難不可避免地到來,為什么不勇敢地面對(duì)呢?
老人沒有罵他,也沒有打他,而是撫摸著他單薄的衣服,許久許久,喃喃道:“哎,真是作孽啊,為什么要那么遠(yuǎn)跑來作孽啊?”老人的淚從刀刻般的臉上落下,顫抖著手從籃子里拿出衣服,披在他的身上,道:“孩子,要注意身體,不要讓家里的老娘擔(dān)心啊。”說完,拄著棍子,慢慢地走了,一直走向雨霧深處。
許久許久,他醒悟過來,“咚”地一聲跪了下來,淚流滿面地用不太標(biāo)準(zhǔn)的中國話喊:“媽媽——”
“媽媽——”身后,所有的俘虜在一剎那間都跪了下來,一個(gè)個(gè)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