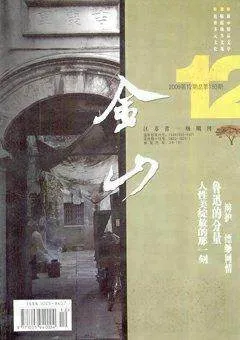吳承恩故居憶舊
鐘 敏
離開第二故鄉(xiāng)淮安快20年了,每次回淮安作故地重游,有兩個必到之處,一是去駙馬巷瞻仰周恩來故居;二是去打銅巷尋訪吳承恩故居。
今次重游淮安,我與老伴拜別周恩來故居后,走進了吳承恩故居,來到吳承恩的塑像前。老伴余耀中深情地注目這座栩栩如生的塑像:清瘦的面龐、睿智的雙眼、淡定的神情、飄逸的身姿,盡展歷史滄桑和大家風范。一部古典名著《西游記》,構思于他的腦海中,誕生在他的妙筆下。余耀中情不自禁地浮想起如煙往事,向我敘述著當年從吳承恩的頭骨到吳承恩的塑像這段故事:
那是1981年,余耀中時任淮安縣(現為楚州區(qū))縣長,在一次與幾個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閑談中,有一個鄉(xiāng)干部向他詢問道:“《西游記》作者是吳承恩,還有一個‘荊府紀善吳承恩,這兩個吳承恩不知是一個人,還是同名同姓的兩個人?”對《西游記》,對作為淮安人的吳承恩有點研究、有點了解的老余,當即談笑風生地告訴他:“兩個吳承恩,同是一個人。明朝嘉靖四十五年,吳承恩出任浙江長興縣丞,不久便蒙冤入獄,真相大白后,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將其釋放,補他一個級別相當的八品閑職官位‘荊府紀善。‘荊府的全稱是‘荊善王府,‘紀善負責管理王府宗室的有關事宜。明代各個王府的紀善都是正八品,吳承恩入獄前擔任的縣丞,是知縣的副手,主要職責是輔佐知縣,并具體管理糧、馬(馬政)之事,縣丞為正八品。”說到此,老余話鋒一轉,又詢問這位鄉(xiāng)干部:“‘荊府紀善吳承恩,你是從書上看來的,還是聽故事聽來的?”鄉(xiāng)干部風趣地說:“我一不是從書中看來的,二不是聽故事聽來的,我是從一塊棺材板上看到的。”老余覺得這話很有意思,便進一步詢問:“哪里來的棺材板?這棺材板現在哪里?”鄉(xiāng)干部說:“棺材板在我們鄉(xiāng)的一個學校的墻角放著呢。”為了看個清楚,弄個明白,老余第二天就和這位鄉(xiāng)干部一同來到學校,他看到棺材頭上的一塊板,上面刻有“明荊府紀善吳承恩之柩”的字樣,老余自是一番驚喜,他心中不禁盤算道:吳承恩于明朝萬歷十年(1582)以80高齡逝世于淮地,傳說中“葬在灌溝吳家先塋”,而究竟葬于何處一直是個謎。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啊,數百年來蹤影全無的吳承恩墓可能有了一點線索。再聽聽校方介紹這塊棺材板的來歷:因當時杉木緊缺,學校為了整修教室的門窗,當地的刨棺盜墓者,便將一口棺材賣給學校作修理門窗用,因棺材頭板又窄又短不合用,所以就剩了下來,棄于墻角。
為了尋找吳承恩墓,查明墓中陪葬之物,老余當即責成鄉(xiāng)干部,找到刨棺盜墓者,如數追繳墓中出土物件。兩天后,鄉(xiāng)里向老余匯報了盜墓者供述的全部過程:墓早已不存在了,只是一個與農田一般的平地,是在挖溝時碰到的,當晚在月色下,將棺材挖出,后將棺材蓋撬開,棺內除了尸骨,只有兩只碗,別無它物。盜墓者取出兩碗后,便將棺材來個底朝天,將尸骨倒進坑中,然后用土掩埋填平,將棺材抬走,后又賣給學校作整修門窗用。
一代古典名著《西游記》作者吳承恩的墓終于見了天日,為世人所知所見!從極其簡單、平常的墓葬,可見吳承恩當年晚景之凄涼。按照盜墓者的供述,縣鄉(xiāng)有關方面,實地查看了墓穴,經過盜墓者一番折騰之后的吳承恩尸骨已經破碎不堪,只有頭顱骨尚屬完好無損,后來由縣文化部門將此頭骨專程送往北京,以此來還原吳承恩的形象。
在今天的吳承恩故居內,我們深情注目的吳承恩塑像,就是二十多年前,以吳承恩的頭骨經過北京有關部門和專家用考古和現代科技還原的,使得吳承恩當年的形象和風采從歷史中走來,展現給世人。
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淮安楚州,正在繼往開來地建設發(fā)展“文楚州”、“景楚州”、“金楚州”。生在楚州、長在楚州、葉落歸根于楚州的吳承恩,故居重建了,墓地重修了,《西游記》名著橫空出世數百載傳遍古今中外了,這是無聲的告慰,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