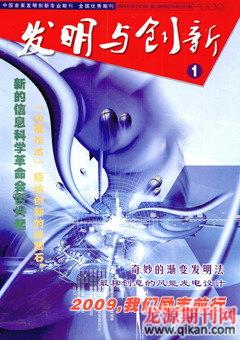勇闖科學險峰的拓荒人
劉云飛 徐 銓
地震科學家還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預報地震的理論和方法,這種追求是幾千年來人類認識自然、掌握自身命運努力的延續,要想讓這種努力在地震災害中見到曙光,真需要難以計量的時間和投入。而“地震預警假說”的作者呂子東先生則為我們帶來了黎明前的曙光。
現有知識框架無法接受
呂子東,1940年出生在浙江象山港畔的一個小山村。1959年到長春地質學院地質系學習,后曾師從喻德淵先生等導師,學習地質力學和天體物理學,期間跟隨唐敖慶先生攻讀分子軌道理論。到了畢業,此時行囊中已有“中微子的快子假說”,“地球史的自然序”及“物理學的時空觀等多篇提綱和初稿。其后幾年他把初稿中的難題切實梳理了多次。為了有充足的理論計算時間,20世紀80年代末,改行搞地方科普工作。如今作為北京前沿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專門從事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其后出版多本專著,特別是2007年9月公開發表的《地震預警假說》,它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依據,世界上還無人提出過。
呂子東先生的《地震預警假說》建立了兩個可以重復檢驗的物理學空間模型。為解決地震的能量從哪里來,地殼板塊之間為什么有相對運動,地球磁場為什么向西漂移。地球的內核為什么有加速運動,呂子東先生建立了地球內部的動力學空間模型,在理論上得到了5項可供地表實驗室檢驗的物理學數據,也得到地球內部存在著兩種(也僅有兩種)可測量的第一推動力和它的波長值。發生在地下的從數千米到數百千米的地震活動,就是這2種可測量的第一推動力造成的;為解決“準時、準地、準級別”的地震預報,呂子東先生建立了一個可供地表實驗室(包括近地應用衛星)測量第一推動力的運動學空間模型,也就是在孕震期可以用現有儀器和設備在地表測量第一推動力變化過程的4組數據,它包括:在孕震期出現的地球磁北極的緯度漂移,漂移量值與震級正相關;中子干涉儀在孕震期的計數率與本底的差值同震級正相關;寬帶狀地磁變率的走向與震中對應的緯度正相關,其垂直分量與震中位置正相關,量值大小與震級正相關:與地面引力波波長值相一致的,經巖石圈分子運動耦合后產生的甚低頻超低頻無線電波和極低頻聲波,與震中的地理位置正相關,強度最大值與發震時間正相關,也與震級正相關。
呂子東先生構筑的地球內部空間的動力學模型,卻是“現有知識框架”無法接受的,是和當今已公認的科學理論(包括相對論和量子理論,大統一的標準理論,地學理論,天體物理學理論,幾何學空間理論,及宇宙論等等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相沖突的,甚至在“現有知識框架”內連“質疑標準”都找不到。
整個系統工程只能由實驗來檢驗
據呂子東介紹,“地震預警”的實驗檢驗共有9大塊組成。這些搞基礎科學研究的實驗,是需要國家立項花大錢的實驗。早在2005年(在第二次相對論研討會上),就有與會記者向他提出過:“如果沒有實驗的檢驗,如果國內沒有這一類設備,如果國外對此不感興趣,這樣的理論可靠嗎?”呂子東回答很干脆:“20世紀的兩大科學理論,相對論和量子理論,就是靠‘借來的實驗才誕生的,‘地震預警假說的實驗只不過多‘借了9大塊。”“如果國內沒有這一類設備,國外有興趣嗎?”呂子東的回答同樣很干脆:“他們會非常樂意”。例如9大塊中有一組地面引力波波長值和地核表面的反引力波波長值,前者可用美國的LIGO引力探測儀(投資2.92億美元)和日本的“卡姆蘭德實驗”裝置(投資0.26億美元)。后者可用《c·O·w實驗》的“中子干涉儀”,他們曾經得到過這一類數據,并且他們很清楚這些設備是地球村居民的納稅款,何況這些數據背后潛藏著甚大的功利;相對論和量子理論存在著邊界條件的實驗誰不想做?測量“大統一理論”的4個物理學數據誰不想做?何況其中的一個數據還和“可控核聚變”相聯結;“龐加萊空間物理學模型”的5方面測量數據誰不想去重復檢驗?畢竟“龐加萊猜想”的最終證明已經向人類展示出了一個清晰的新世界,只要“地震預警假說”經過嚴密的認證,實驗的重復檢驗是明擺著無需擔心的事。
呂子東的理論能否經得起全部實驗的驗證,尚有時日。這項工作的啟示在于,從認識的根源處探索“現有知識框架”的局限性,力圖從整體上打開我們對物理世界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