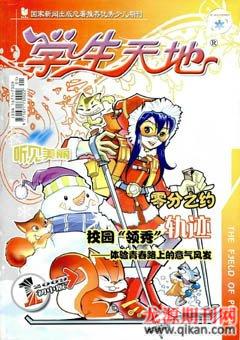在唐詩宋詞里與明月相逢
積雪草
小時候,一定要讀李白的《靜夜思》,這幾乎成了每一個中國孩子童年時代的啟蒙詩。簡單的幾個字,充滿優美的意境和情調。那時候,我覺得古人眼里的月亮,是一滴清冷的淚珠,是一縷冰冷的鄉愁。
長大了,漸漸明白了一些人和事,才知道,《靜夜思》中除了悠長的思念,還有無奈和濃郁得化不開的離愁。也知道了“故鄉”這兩個字在一個人心中的位置和分量:故鄉是根,旅人是葉,無論旅人走多遠,心都會落到那片植根的土地上。
“詩圣”杜甫筆下的月亮:“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其實,哪里的明月不照人?單單挑明故鄉的月亮最明,是詩人的心境使然。離亂、戰爭、憂國憂民之思,哪里還有一輪明月?有的只是懷念和遙想。和李白的浪漫飄逸相比,杜甫的詩更加凝重和蒼涼,而且杜甫描寫月亮的名篇要比李白留下的少。處境不同,感懷不同吧!詩人杜甫更加關注現實的境遇。
唐詩中吟月述懷的千古名句如繁星伴月,數不勝數,如張若虛筆下的“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被譽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山水田園派代表詩人王維筆下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博覽有識,崇尚儒、道的詩人張繼筆下的“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最憂郁、最悲傷的“千古詞帝”南唐后主李煜筆下的“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等等。
月亮還是那個月亮,但在詩人的眼里看卻各不相同。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重、王維的曠達、李煜的憂郁,月亮成了文人墨客抒懷寄情的對象。
蘇東坡也有一輪自己的明月:“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作為文學家的蘇東坡,一生抑郁不得志,夾在兩派政治爭斗中,左右不逢源。在佛家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之間,一會兒灑脫,一會兒消沉,他因而感懷:“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宋詞中的明月似乎不及唐詩中來得豐盈。蘇東坡除了那首《水調歌頭》外,還有一首《中秋月》:“暮云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相比之下,這首就不如《水調歌頭》的影響大。王安石的“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桿”和辛棄疾的“誰共我,醉明月”都不及柳永的“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更為后人所熟知。
唐詩宋詞里的明月,逾越千年,積淀成深厚的中華文化的沃土。故鄉的月亮自然與別處不同,中國的月亮自然與外國不同,雖然頭頂上是同一輪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