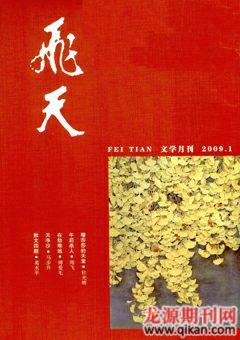稽莎莎的天堂
杜光輝
一
早上七點鐘,太陽就燦爛了海島城市。稽莎莎還睡在床上,眼睛都懶得睜開。枕頭旁邊的手機響,是馬曼麗打來的,問她起床沒有。她說沒有,不想起來,渾身沒勁。你有啥事情就說,我還要睡覺哩。
馬曼麗說上午到圣彼得堡喝咖啡,九點鐘見,不見不散。
稽莎莎就慵聲倦氣地說行,不見不散。收線后還是不肯起床,這個時辰賴在床上真是一種享受。突然,小區里喧起一陣女人吼喊孩子的聒噪,嗓門很粗,感覺是男人在吼,還吼了很長時間。稽莎莎煩得翻了個身子,把脊背對著窗戶,女人堅忍不拔的吼叫還是頑強地鉆進耳道。好幾分鐘后,女人的吼叫才停下。又爆起兩個男人的吵架,像兩個戰鼓在擂,感覺他們已經發生了身體接觸。周末的懶覺睡不下去了,又不想起床,還是賴在床上,過了好長時間心緒才平靜下來。樓上又響起刀在案板上剁的聲響,急促嘹亮,像是剁餃子餡。本來,誰家也不會一大早就剁餃子餡,但這個小區住的人都不按正常的生活規律過日子,自己怎么方便就怎么過,根本不考慮別人的感受。睡眠被徹底破壞了,還慵倦,還想賴在床上,期待瞌睡再一次到來,就閉上眼睛努力使自己睡著。不知誰家養的狗又狂吠起來,其聲洪亮,充滿陽剛,帶有逼人的殺氣。隨之,又亮起一只狗的響應,這只狗的吠聲尖細,但絲毫不失嘹亮。兩只狗像電視上的男女聲兩重唱,遙相呼應,聲聲入耳,迫使她不能繼續在床上賴下去了。
情緒被破壞了,只好起床,刷牙洗臉后就開始準備早餐。早餐很簡單,一杯牛奶放在微波爐里熱了,再熱一塊面包,煎上一個雞蛋,連做帶吃十五分鐘完成。吃過早餐,看了下手表,八點過一刻,就到化妝鏡前收拾讓別人看的臉。鏡子里的臉確實不年輕了,女人到了四十歲,又沒有陽光雨露滋潤,怎么能年輕?所以對鏡子里的臉就不怎么滿意,腦子里想起小說里的一句話,女人照鏡子一日不如一日。用在修補臉色上的時間越來越多,幾乎把所有的化妝品都用上了,那張臉還是像帝國主義一樣,不可阻擋地朝著沒落衰敗。
半個小時后,盡管還對經過千抹萬描的臉耿耿于懷,但又不得不走出房子,帶著無可奈何花落去而產生的那種淡淡的沮喪、淡淡的失落、淡淡的郁悶、淡淡的憂愁,走出了房子。樓道口,不知道誰堆了幾包垃圾,幾只半尺長的老鼠在饕餮,其中有只懷孕的老鼠,肚子鼓得好大。盛垃圾的塑料袋被老鼠咬破了,殘湯剩菜雞骨頭灑得滿地都是,散發著難聞的氣味。老鼠見她過來,似乎并不驚恐,慢慢地逃到一邊,躲在四五米遠的墻角,用賊亮的小眼睛看她。她忍著惡心,經過那堆垃圾的時候,有意識地屏住呼吸,盡最大限度地離遠一點。
小區的院子就是停車場,每個月收一百五十塊錢的停車費,但沒有固定車位,誰想停在哪就停在哪。稽莎莎是輛捷達牌轎車,前后左右都停了車,一輛大卡車死死地堵在捷達車的前邊。稽莎莎圍著轎車轉了一圈,發現就是把全世界最高超的駕駛員請來,也把車開不出去,就對著四周的樓房喊,誰的車把我的車擋住了?剛才還吵吵鬧鬧的小區,這陣卻異常安靜,她喊叫了十多分鐘,還是沒有一個人回答。周末正是睡懶覺的時候,誰愿意聽她的喊叫?突然,六樓窗口里伸出一個男人的腦袋,大聲吼你叫什么叫,你不睡覺別人還要睡覺哩。隨即,五樓窗口里伸出一個女人腦袋,也大聲指責她,我的孩子還在睡覺,你聲音小一點可以不?不知道哪個窗戶里傳出一個年輕男人的聲音,發情啦,一大早就叫春,要叫就到種馬場去,在這里叫也不管用!稽莎莎就委屈地喊,我的車被他們圍住了,我有急事要開車。立即有男人對她吼,誰的車擋你的路找誰去,在小區里大聲喊叫驚擾大家都睡不成。要不找物業公司,讓他們解決!
稽莎莎氣得滿臉通紅,眼睛里都有了淚水,就是沒有讓流出來。自己怎么和這種檔次的人住在一塊,連起碼的生活常識都不懂。她的車是下午六點鐘就停在這里了,后來停的車應該給先停的車留出通道。不能只顧自己停車方便,不管別人怎么辦。隨之又和自己是單身女人聯系起來,要是有男人在自己身邊,朝車跟前一站,誰敢辱罵自己?她又跑到另一棟樓下的物業公司,門鎖著里面沒有人,門上貼著作息時間通告,周六周日休息,周一至周五按國家規定的工作時間上班。
她氣憤地嘆了口氣,無奈地轉過身子。剛好有個保安經過,就無意識地說物業公司今天不上班?保安指著通告說上邊寫得很清楚,周六周日不上班。
她說應該有個值班的,業主有事情也好處理。
保安說國家規定節假日上班要發三倍的工資,咱們的物業管理費收得低,很多人還不交,公司開不起節假日的工資。
她不說話了,她和好多人聊天的時候說到物業管理費,相比之下這個小區的物業管理費是最低的。交那么低的物業管理費,還想享受周末的服務,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保安見她還不離開,就問你有什么事情,周末還找物業公司?她說我的車停在院子里,后來的車把我的車堵死了,我現在急著要開車。保安說要是這事情,我也沒辦法幫你,誰也不知道那些車是哪棟樓哪個住戶的。她就說你們物業公司應該在院子里畫出停車線,不能隨便亂停。保安說就是把線畫出來了,他們不按規定停還是沒辦法。就是現在沒有畫線,停車時要把公共通道留出來,這是起碼的常識,他們不遵守也沒辦法。他們這次堵你的車,你把他的車號記住,下次也堵他的車,一報還一報。
她苦笑了一下,又不能說什么,人家是為自己好,才給自己出這個主意。
一直到了九點十分,擋在她的車前邊的大卡車的司機才光著膀子,鼓著黑黢黢的肚子,從另一棟樓里走出來。他開車門的時候,稽莎莎跑過去,說你停車也不看看,把我的車都擋住了,我喊叫了半晌你都不出來,耽誤了我一個多小時。
司機看了她一眼,說我的車也經常被你們的車擋,也經常耽誤時間。她說我就沒有擋過你的車。司機說擋沒擋過我也記不清了,反正我的車經常被別的車擋,從來沒有找人家吵過架。她說我什么時候找你吵架了?司機說你現在正在找我吵架。她說看看你那樣子,配得上和我吵架。司機說你找個能配上你的人吵呀,何必找我配你,我還不想配你哩,像你這樣的老女人,五塊錢再打五五折,到人民天橋一抓一大把,不要錢我都不配你!司機不是善茬,惡心人的話像瓊州海峽的浪一樣,一波一波朝岸上涌。
你流氓,不要臉的流氓!稽莎莎從早上起床到現在的憋氣一下子爆發起來,沖著司機發泄起來。你怎么知道我是流氓,我流你身上什么氓了?
她和司機正吵著,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從樓里跑出來,對著那個男人吼你不趕快出車,和人家吵什么架?司機說我沒有找她吵架,我剛走到車跟前,她就跑過來找我吵,說我擋了她的路,還罵我是流氓!女人跑到她跟前,說他是我男人,你罵他是流氓,他把你怎么了?他要是真在你身上耍流氓,我收拾他。他要是沒有在你身上耍流氓,你也要給他個說法。大家都在一個院里過日子,不能讓他背著不清白的名聲,讓我戴一頂說不清楚的綠帽子。
四邊樓里的人聽見院子里吵架,都從窗戶里伸出腦袋觀戰。樓層低的干脆跑出房子,圍在他們四周看熱鬧,一會兒功夫就圍了四五十個人。有人惟恐不亂地喊加油,有人指指點點說說道道,也有人走到他們中間勸說。又折騰了二十多分鐘,司機的老婆才說看你那張驢臉,還好意思說我老公給你耍流氓,不信你到海秀路站一晚上,看有沒有男人問價錢?
有幾個老住戶出來了,對司機和他老婆說你們擋了人家的車,本來就不對,還和人家吵架。你們知道人家是干啥的,人家是公家的干部,當著辦公室主任哩!
看熱鬧的人聽他們這么一說,又都指責司機不對。司機才怏怏地鉆進駕駛室,開著車離去。司機老婆像離開主人的狗一樣,夾著尾巴溜回屋子。
二
圣彼得堡咖啡廳并不在俄羅斯的涅瓦河畔,在這座城市最繁華的國貿大道。進門就是彼得大帝騎著駿馬、手持寶劍的雕塑,很是威武,很是陽剛,渾身上下充滿霸氣。樓梯的兩側,全是裸體的俄羅斯女人,身材都高挑,乳房都豐滿,腰部都纖細,五官都端正。過往的男人女人都要看上幾眼,男人目光里流露的是欣賞,女人目光里流露的是嫉妒。還有裸體的俄羅斯男人,身體高大偉岸,胸肌發達,腹肌性感,裸露的生命之根自然下垂,雖然沒有勃起的跡象,但讓人感覺一旦堅挺起來,肯定所向披糜,無堅不摧。過往的男人女人同樣要看上幾眼,男人目光里流露的是嫉妒,女人目光里流露的是欣賞。
咖啡廳的墻壁上,懸掛著歐洲的名畫,盡管是摹本,但臨摹技術相當高超,就是擺到商店也價格不菲。走進大廳要經過一道小橋,小橋旁邊有座假山,造型秀麗逼真。山上有個亭子,亭子里的人都活靈活現。山上曲曲彎彎流下一道瀑布,從小橋下流過,給人清新涼爽的感覺。小橋的另一邊支著一座鋼琴,一個穿著白色衣裙的少女在彈琴,琴聲叮咚,悅耳動聽。稽莎莎知道這個咖啡廳是這個城市最高檔的約會場所,價格的高貴使一般人望而止步,只有收入不菲講究情調的人和上流社會的人才到這里消費。
十點多鐘是咖啡廳最清靜的時候,大廳稀稀疏疏地坐著幾個人。無論男人女人都穿著世界級的名牌,擺出高貴優雅的派頭,聲音很低地說著話。她一走進咖啡廳,胸臆中就騰升出高貴的情愫,行動上就有了高貴的舉止,走路放輕腳步,挺胸抬頭,目光正視前方,一只手自然地撫在挎包上,另一只手自然擺動。她覺得,只要走進這個場所,就是憋了滿肚子的氣也會克制著不能發作。馬曼麗已經早到了,坐在靠窗戶的一個桌子旁給她招手。她給馬曼麗擺了下手,盡量使動作優雅高貴。
服務生見她走過來,快步走到她跟前,替她把椅子朝后邊拉了一下,待她坐好后又恭立在旁邊。馬曼麗小聲問怎么遲到了一個小時?我以為出了什么事情。
她小聲說別提了,還吵了一架!
馬曼麗說什么事情值得一大早就吵架?
她把吵架的事情講述了一遍。
馬曼麗說莎莎不是我說你,你怎么還在那個小區住?這個城市里除了過去的家屬院,再沒有比那低檔的住宅區了。你們小區都住的什么人,進城的農民工,下崗工人,退休的一般干部,剛畢業的大學生,社會閑雜人員,在那個環境里不想吵架都不行,人人都不講道理,也不懂得道理,你講道理就活不下去。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氣,只有經常吵架才能發泄出來,要不非憋出癌癥不可。像這個咖啡廳,坐的都是上流社會的人,都講究自己的品味和休養,注意在公眾場所保持形象,想吵架都沒人和你吵。你以后要是交上了男朋友,人家問你住在什么地方,怎么好意思說住在那個小區?就像我們今天聊天,人家知道我們在圣彼得堡喝咖啡,就知道我們的檔次。我們要是在馬路邊喝老爸茶,人家會以為我們是什么檔次的人?
馬曼麗把她開導了一陣,把酒水單推到她面前,又對服務生招了下手,說你喝點什么,自己點。稽莎莎就翻酒水單,只要是咖啡類,沒有低于100元以下的。茶水相對便宜,但最便宜的龍眼紅棗茶也是80塊錢一壺。她翻了好大功夫,還沒有下決心點,又不好意思給馬曼麗說這里的東西太貴,琢磨了半天才說來一壺龍眼紅棗茶咋樣?
馬曼麗說莎莎你是惡心我哩,咱們兩個女的喝那么大一壺龍眼紅棗茶,不脹死咱們?這里有最低消費,一人最低消費不能低于100塊錢。她說完就對服務生說,給她來杯哥倫比亞咖啡,我來杯英國皇室咖啡。稽莎莎就看酒水單,哥倫比亞咖啡一杯198元,英國皇室咖啡189元,兩杯咖啡加起來差不多400塊錢。就轉了個彎說這里的消費真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
馬曼麗說這里的檔次就是通過價格體現出來的,要是人人都能進來的老爸茶坊,就沒有這里的品味了。在這里消費有這里消費的價值,在這里認識的朋友和在老爸茶坊認識的朋友,就有天地之別。我和現在的男朋友就是在這里認識的,我要是天天泡老爸茶坊,認識的只能是下崗工人和進城農民。
挎包里的手機一陣蜂音,稽莎莎取出手機,回答對方說我在圣彼得堡咖啡廳。其實,她完全可以說我在外邊,沒必要說那么具體,但她覺得說出圣彼得堡的時候,胸中就有一股自豪和得意。馬曼麗見她收了線,說你現在給對方說在圣彼得堡咖啡廳,感覺就不一樣吧。
稽莎莎點了下頭。
馬曼麗又說莎莎,我上個星期搬家了。稽莎莎問搬到什么地方了,馬曼麗說我在帝都花苑買了一套164平米的房子。稽莎莎驚訝地問帝都花苑?馬曼麗說是帝都花苑。稽莎莎說那可是全海南島最貴的房子,兩萬多塊錢一平米。馬曼麗說兩萬一千零九十八塊,一分錢的折都不打。連裝修費算下來,花了四百五十多萬。
稽莎莎看了她一眼,不再說話了。四百五十多萬對于她來說,是個不敢想象的天文數字。
馬曼麗又說莎莎,吃過中午飯,到我的新家看看,體驗一下上流社會住宅區的感覺。我們過去老說世外桃園,什么是世外桃園,帝都花苑就是世外桃園。走進帝都花苑,立即感覺到一派鳥語花香,空氣清爽,精神舒適,自覺做了神仙。我從搬到帝都花苑以后,再和朋友們交往,感覺就是不一樣。別人聽說我住在帝都花苑,給我說話的口氣都發生變化,就像我們給香港的李嘉誠、美國的比爾蓋茨說話一樣。在那個小區居住的人,素質就是高,行為都是那么高貴講究,待人接物都彬彬有禮。就連人家養的狗,都高貴漂亮,清潔衛生,不亂吼亂叫,和這些人住在一塊本身就是一種享受。莎莎,你又沒有負擔,攢那么多錢干什么,干脆在帝都花苑買套房子,哪怕買套小點的房子,也不能再在現在的小區住下去了。
稽莎莎說曼麗你是飽人不知饑人的可憐,帝都花苑一平米兩萬多元,哪是我們這些人住的?攢的那點錢連裝修費都不夠!稽莎莎知道馬曼麗被一個香港老板包養了,那個香港老板有良心,和馬曼麗交往了三四年都沒有拋棄她,不像現在的很多男人,有了新歡就拋棄舊人。人家馬曼麗有大老板包養,自己卻連個男朋友都找不著,沒有額外收入,靠自己一個月兩千多塊錢,一年的工資才能買一平米房子,住帝都花苑只能是夢想中的事情。
馬曼麗又問莎莎你存了多少錢?可以在帝都花苑按揭一套房子。稽莎莎說大約有三十多萬,還是離婚時分給我的財產。稽莎莎是十年前離婚的,一個女兒給了男方,男方有個中等公司,在公司里給她撥了二十五萬,她這些年又省吃儉用使銀行存折上數字不斷增長。馬曼麗又說三十萬交首付款夠了,你一個人也不需要太大的房子,有四五十平米就可以了。你要是住到帝都花苑,就能結識住在那里的男人,那里的男人可是男人中的精品,事業有成,到時候會幫你換成大房子!
稽莎莎琢磨了一會兒說,我不指望那些狗屁男人,毛老人家都說自力更生豐衣足食,我自己能養活自己。就是在帝都花苑買房子,月月的按揭還是能付得起的。
馬曼麗知道她說的不是心里話,就說莎莎你這是何必哩,女人天生就是靠男人過日子的。你長得又不差,就是心情不愉快,加上長期得不到男人的陽光雨露,臉色顯得干枯。你住進了帝都花苑,再結識一個威猛有錢的男人,用進口化妝品一打扮,隔三差五地瘋狂一夜,能一下子年輕二十歲!
稽莎莎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說咱們就在這里吃套餐,吃過飯就去帝都花苑看房子。馬曼麗說再著急也不在這一會兒功夫,人一輩子啥都可以將就,就吃飯睡覺不能將就。中午咱們到俄羅斯餐廳,那里的西餐最正宗。說完就對旁邊的服務生招了下手,說埋單,從挎包里取出錢包。稽莎莎也急忙取出錢包,說我來。馬曼麗說你歇著吧,就你那點工資,要是一會在俄羅斯餐廳的消費也埋單了,這個月你就別吃飯了。
稽莎莎苦笑了一下,說也是,就那點工資,要不是你請,哪敢到這些地方來?
三
下午的時候,稽莎莎開車回到小區。小區門口的保安給她放行的時候,物業公司的經理也站在那里,跑到她車子跟前,還給她哈了下腰,恭敬地說大姐,上午讓你受委屈了。我已經狠狠批評了那些人了,胡亂停車怎么行?你是老住戶了,又是國家干部,不要和那些人一樣見識。那些人都是進城的農民,腿上的泥巴還沒有洗干凈,和他們生氣降你的身份。
經理很會說話,稽莎莎從他的話里感覺出自己在這個小區還是很有地位的,自己是這個小區不多的國家干部之一,也是這個小區最早開上轎車的住戶,從來不欠物業公司的管理費、水電費,自己開車進門出門,保安都給敬禮。有幾次她沒開車出門,經過小區門口的時候,發現保安并不是給誰都敬禮的,對那些卡車根本不敬禮,就是對轎車也是選擇性的敬禮。能讓保安敬禮的車主,無疑是小區的高等住戶,是小區的頭面人物。
她把車開進院子,早上和自己吵架的卡車司機剛停好車從駕駛室跳下來,看見她的車進來,走到她跟前很不自然地說,大姐,我不知道你是國家干部,早上冒犯了你。上午物業公司的人找我談話,我才知道你是國家干部。你大人不記小人過,以后需要我們做啥事情,就打個招呼。卡車司機正說著,老婆也從房子里跑出來,手里拿著兩個木瓜,跑到稽莎莎跟前,臉上的笑能流出蜂蜜,說大姐你是國家干部,不要計較俺這些農民。他這個人成天在外邊跑,性子野把你得罪了,俺兩口子都給你賠不是。這木瓜是俺家自己種的,沒有上化肥沒有用農藥,味道不一樣。你拿去嘗嘗,要是覺得好吃,俺以后回家再給你帶。
稽莎莎胸臆中殘留的氣憤一下子被洗滌了,反而覺得不好意思,急忙說都在一個院子住著,發生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早上的時候,我的脾氣也不好,以后咱們互相幫助。木瓜你們留著自己吃,你們在城里生活,啥都得掏錢買,也不容易!司機老婆等她從車里鉆出來,硬把木瓜塞到她手里,看著她走進樓里,才慢慢離去。她能感覺到人家看她背影的目光都流溢出尊敬。
稽莎莎的車再沒有被別的車堵塞過。有好幾次,她早上上班,開車的時候看見那輛大卡車停在很遠的角落。小區里的進城農民,遇到她都恭敬地打招呼,不論年齡大的小的都稱她為大姐。好幾次她下午開車回來,司機老婆不是抱個西瓜,就是提一篼紅薯,要不就是一袋西紅柿,硬要送給她,都說是自家種的,沒用農藥沒用化肥沒有污染絕對生態。
稽莎莎所在的檔案館搬家,館長叫稽莎莎負責這件事情,雇一輛大卡車,再雇十個民工,關鍵是要認真,每搬運一件都要做好記錄,檔案這東西連一張紙都不敢丟。稽莎莎馬上想到小區里的大卡車司機,晚上回到小區把車停好后沒有馬上進樓,站在院子里朝司機住的房子張望。司機老婆看見她,立即從房子里跑出來,老遠就叫大姐你回來啦!
稽莎莎問你老公回來沒有?
女人就朝著房子喊,阿燦,大姐找你!
司機穿著大褲衩跑出來,也是老遠就大聲問大姐找我啥事情?
稽莎莎說我們檔案館要搬家,需要一輛卡車十個民工,工錢都好商量,不知道你能不能做這事情?
司機立即說能能能,我們就是攬到活了才有飯吃,攬不到活就沒有飯吃,不知道大姐需要多長時間?稽莎莎說最少得一個月,一個檔案館幾十間房子的檔案,不是一天兩天能拉完的。而且裝檔案的時候要登記,卸檔案的時候也要登記,花費的時間就長。
司機說沒問題,你們雇我的車,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稽莎莎說還需要十個民工,手腳要干凈,干活要認真,丟一件檔案都是坐牢的罪過。
司機說這個更沒有問題,我現在就給俺村子的人打電話,叫來十個年輕小伙子,人品絕對沒問題。
稽莎莎說你的卡車一天多少錢,人工一天多少錢,我回去好給領導匯報。
司機說大姐你看著給,給你干事情就不能講錢。
稽莎莎說不是給我干活,是給公家干活,是公家給你工錢,你該要多少就要多少,說啥也不能讓公家占了私人的便宜。你們進城做事,掙點錢多難。
司機說你們包不包油錢?
稽莎莎就說我們啥都不管,我們一輩子就雇這一次車,哪個省的檔案館也不會經常搬家。
司機說車連司機和油錢一天按600塊錢算,民工一個一天按80塊錢算,如果你們解決住宿可以按70塊錢算。
稽莎莎覺得要價不高,就對司機說我明天上班給領導匯報一下,領導同意后就給你打電話,你就通知你們村子的民工趕過來。
連續四十多天,稽莎莎指揮著大卡車和民工搬運檔案。晚上回到小區,早回來的司機和民工就聚在院子里,都給她貢獻出滿臉的諂媚,大姐長大姐短的獻殷勤。還有的拿出從家里帶來的土產,死活要送給她。她又從他們那里感受到自己的高貴和尊嚴。
四十多天以后,檔案搬完了,稽莎莎在工單上簽過字,又讓館長簽過字,把他們領到財務室,看著他們領過工錢,又把他們送到大門口。司機和民工對她千恩萬謝之后,才歡天喜地地走了。
晚上她回到小區,司機和民工又聚在院子里,司機拿著一沓子錢,走到她跟前小聲說,大姐這是你的收入。
她驚詫地看著那沓子錢,說我有什么收入?
司機說你給我們攬的這個活,我們得給你回扣,這是規矩。他們一人給你五百,我給你五千,加起來是一萬,司機說著就把錢朝她手里塞。
稽莎莎急忙把手縮回來,說這錢是你們掙的,我怎么能拿你們的錢?
司機說要是沒有你,我們哪能掙到這些錢?
其實,她也聽說過現在做啥事情都有回扣,回扣的多少看對方獲得利益的多少,有的人把工錢算得很高,讓國家多出錢,把錢付給對方后,對方再返給管事的人。盡管這樣,稽莎莎還是不好意思拿這筆錢,但司機和民工死活要她拿這筆錢,推來推去只好拿了一半。
這些民工沒有再回農村,就在這個小區租了房子,在城里找工作應付生活。稽莎莎成了這幫民工心目中的女皇,小區的人見這些五大三粗的漢子都對稽莎莎恭敬,見到她也就格外客氣。
以后,檔案館有了需要雇用卡車和民工的事情,她就讓司機和這些民工去干。這些人在她那里得到了好處,對她更是恭敬萬分。
四
又過了四個月,稽莎莎在帝都花苑買的房子裝修好了。她把這邊小區的房子租給了別人,還是租用這個卡車司機的車,還是雇用那十個人,把家朝帝都花苑搬。
把家具朝樓下搬的時候,司機和進城的農民就問她,干部大姐你在這住得好好的搬家干什么?我們住在一個小區,有事情也好照應。這些進城農民又把她叫干部大姐了,在他們心目中,干部是最有權勢的人了。
她給他們解釋,那邊的環境要好一些,朋友也住在那里。說話的時候看他們難受的樣子,又說我經常回來,我的房子租出去了,要回來收房租。
司機老婆說干部大姐,你回來前給我們打個電話,我把飯做好咱們一塊吃。就連平時沒有來往的住戶也出來看她搬家,也和她打招呼,她感覺出他們對她還是很高看的。在這個小區,像她這樣身份的人還是不多的。
她開著自己的捷達,大卡車跟在捷達的后邊,民工們坐在大卡車上,浩浩蕩蕩地開到帝都花苑。卡車在帝都花苑一停下,民工們還沒有從車上跳下來,就喧嘩起來,哇,世上還有這么好的地方,恐怕中央委員都住不上這房子!又有一個民工說比城里的公園都漂亮,干部大姐以后天天都住在公園里了。他們又圍著稽莎莎問,干部大姐,你在這里買的房子多少錢一平米?稽莎莎說兩萬一千多一平米。民工們睜大眼睛說天爺,兩萬多一平米,我們一年掙的錢不夠買半平米,把我們村賣了恐怕買不了一套房子。還有的民工敬佩地說干部大姐,你真厲害,能買起這么貴的房子。于是,他們再看稽莎莎的眼神中更增加了敬佩的成分。
稽莎莎興奮到了極點,剛搬到帝都花苑,人還沒有住下來,高檔住宅區的效益就顯示出來了。就很大度地對他們說,你們先不忙搬家,把這里好好看看,以后想進來看就不行了,這里實行入內登記制度,一般人是進不來的。
民工們真的不忙搬家了,在花苑里轉來轉去地觀看。沒過三分鐘,一輛摩托車開過來,在他們身邊停下,一個穿保安服的人從摩托上下來,問你們是干什么的?盡管態度溫和,但他們還是感覺出來人家的警惕和對他們的懷疑。民工們都不說話了,也不知道該怎么說。
稽莎莎走過來,說他們是給我搬家的。人家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停在樓邊的捷達一眼,問你住哪套房子?稽莎莎說了自己的房子牌號,人家哦了一聲,聲音還拖得很長,隨后又對她說搬完后讓他們馬上離開小區,這里不許閑雜人員進入。
保安離開以后,稽莎莎很長時間沒有說話。她從保安的話中聽出,人家對開捷達車的自己并不多么尊敬,甚至還懷疑自己不是這里的住戶。于是,朝樓邊的停車場瞅了一眼,停在這里的大都是奔馳、寶馬、原裝奧迪,還有幾輛法拉第、勞斯萊斯,根本沒有捷達這類檔次的車。
大卡車司機又問稽莎莎,干部大姐停在這里的車都是很貴的?
稽莎莎心里就有了失落,情緒也有了低沉,不想回答他的問話。又覺得不回答不禮貌,人家問這話沒有惡意,就說肯定很貴,都是世界上的名牌轎車,哪一輛都是一百多萬,有的還值一千多萬。
稽莎莎的話又引起他們一陣驚嘆,一千多萬一輛,恐怕把錢堆得跟車一樣高都買不來。
稽莎莎給他們說人家買車根本不帶現金,都帶支票,到銀行轉個賬就行了。卡車司機自覺聰明地說一千萬恐怕能裝半卡車,咱們這些人點數都得多半天。一個民工接著說多半天都點不過來,咱們這些人沒有經過點錢訓練,點著點著就點錯了。
他們把家具朝房子搬的時候,進門就又說起來,干部大姐你這房子太小了,比你在咱們小區的房子差遠了,這么小的房子住著多憋氣?
稽莎莎沒有回答,心里卻說兩萬一千多塊錢一平米,要不是按揭我還買不起這房子哩。
他們見稽莎莎不再說話,也就不再說什么了,忙活著把家具按稽莎莎的要求擺。
民工們走后,稽莎莎把小物件擺放好,連晚飯都沒吃就睡覺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九點多鐘起床。剛剛洗漱完畢,就聽見門鈴響,從貓眼里朝外看,是小區的保安,就打開門。保安站在門口給她敬禮,說這是你的停車證,上邊有你的停車位置。如果你需要,我現在可以帶你去看一下具體位置。
小區給她劃分的停車位置在最偏僻最不容易倒車的地方,要是有輛車擋在外邊,自己的車就沒有辦法開出來。她想到自己原來被卡車堵著出不來的教訓,就對保安說能不能把我的停車位置調整一下,這位置太偏僻了,出入不方便。
保安很禮貌地說不好調整,只能這樣了,停車位很緊張,就這也是想了很多辦法擠出來的。
稽莎莎輕輕嘆了口氣,又把停車的位置看了一遍,問停車費多少?
保安說一個月300塊。
稽莎莎心里噓了口氣,一個月的停車費就300塊錢,簡直是敲詐!但是,她什么話都沒說,能住進這個小區就不能為這點錢和保安論長短,要是叫人知道了會笑話自己的。
保安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接著說你的停車費是最便宜的,因為這個位置最偏僻,出入也不十分方便,所以只收300塊錢的停車費。位置好的要收600塊錢,好多車主都想朝便宜的位置調換哩。
稽莎莎在心里算了一下賬,停車費300,物業管理費每平米8塊,45平米就是360塊,還不算水電費就得支出660塊,自己原來那套房子的房租才收600塊,還不夠交物業管理費和水電費。
十點多鐘的時候,馬曼麗來了,先在房子里轉了一圈,轉完后說莎莎你也真是的,換了房子不換家具,新房子配舊家具,要多難看有多難看。依我的意見,把這些家具全扔了,再買新家具。
稽莎莎苦笑了一下說,你說得容易,買家具不要錢?我從哪里弄買家具的錢?就是付的首期購房款,我還借了一萬多塊錢哩!
馬曼麗說也是,到帝都花苑買房子,也難為你了。人住在這里,拼的就是錢,你住多大的房子,裝修的檔次,開的什么車,雇的什么保姆,辦的什么公司,當的什么官,連養的什么檔次的二奶和狗都不能落在別人的后邊。要不就會被人瞧不起,盡管人家嘴里不說啥,但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說完又說莎莎也不著急,等以后有錢了先把家具換了。我估算了一下,把這些家具全換成高檔的也就是10萬塊錢。再等以后有錢了,把房子也換了,起碼換個250平米的,要躍層式。再養一只名貴狗,最好是阿富汗犬,像歐洲女人那樣高貴,牽出去也讓人敬佩。要是傍上了這里的男人,這些計劃就可以提前實現。
稽莎莎苦笑了一下,什么都沒說,心里卻琢磨你以為我是世界選美小姐,這么大歲數了哪個有錢的老板會要自己?
馬曼麗在房子里轉夠了,也沒有在沙發上坐下來,說不管怎么說你也是喬遷之喜,我也沒有東西送你,就請你吃個午飯,算是對你的祝賀,你說在什么地方吃?
稽莎莎說你喜歡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我聽你的。
馬曼麗說俄羅斯餐廳怎么樣?檔次又高,環境又好。
稽莎莎說俄羅斯就俄羅斯。
馬曼麗說咱現在就走,到了那里先喝茶聊天,到了中午再吃飯。
她們走到停車場,馬曼麗問稽莎莎你的車停在什么地方?
稽莎莎就指了下自己的車。
馬曼麗說他們怎么給你安排這個位置?這個位置好長時間都沒有安排出去,誰都不肯要這個位置。
稽莎莎說咱是新來的呀,不愿意又有什么辦法?人家還說了,好的停車位置收費就高,有的位置一個月要收600塊錢哩。
馬曼麗說他們說的沒錯,這里的一切都是論質付費。我那個停車位置也不怎么樣,一個月都收450塊錢。她們說著就走到稽莎莎的捷達跟前,稽莎莎掏出車鑰匙,按了電子開關,隨著一聲細響,車燈閃了一下,表示車門已經打開。稽莎莎就要朝進鉆的時候,馬曼麗擋住她,說你就不要開車了,這種車在你原來的小區不顯得低檔,到了帝都就不行了。你看這個停車場,有幾輛這種檔次的車?
稽莎莎用目光極快地朝停車場瞥了一下,真的沒有一輛這種檔次的車。
馬曼麗說以后把這車換了,最不行也得換個寶馬、奧迪,開出來也不丟人。
稽莎莎又苦笑了一下,心想我這是搬進帝都花苑的第一天,你就讓我換家具換房子換車,這幾樣換下來沒有五六百萬能行?我去哪弄五六百萬,就是搞腐敗也沒條件,憑自己一個辦公室副主任,人家送紅包想都不會想自己。自己唯一能搞的腐敗就是給公家買東西,花了300塊錢開上350塊的發票,還不敢多開,要是讓領導發現了,辦公室副主任都當不成了。指望幾個月多開50塊錢的發票換房子換車換家具,就像讓自己去競選世界小姐一樣不切實際。
五
下午三點多鐘,南中國海島的太陽還是十分暴烈,但帝都花苑到處都是樹木花草,樹木遮罩了太陽的暴烈,也過濾了太陽的酷熱,使小區到處都是樹陰和涼爽。小區最中央是運動區,有游泳場,一個可供比賽用的標準池,一個練習池,一個兒童池,還有一個溫水池。池水碧綠,一派潔凈,有人在池里戲水。在游泳池的旁邊,是棟三層高的運動樓,樓里有健身房、體操館、羽毛球館、乒球館。在運動樓的旁邊是網球場,四周豎立著很高的鐵絲網。稽莎莎午睡起來,站在窗戶前看了一陣這些風景,就有了到里面看看的欲望,也有到游泳池玩上一陣的念頭。她看到在比賽池里游泳的幾個人的姿勢都不標準,顯然沒有經過專業訓練。她上中學的時候曾經被市游泳隊看中,訓練了三年,就是不出成績被淘汰了,但無論如何也比一般人的游泳姿勢標準。就從床頭柜里找出游泳衣,簡單收拾了一下,走出樓門。
她經過網球場的時候,里面沒有人打網球,誰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打網球。經過運動樓的時候,她想先進去看看里面的設施,剛走到健身館門口,站在門口的保安很有禮貌地伸出一只胳膊,也很有禮貌地說,您的票?
她停住腳步,才知道就是這個小區的業主要在這里鍛煉還得交費,就裝成毫不在意的樣子朝樓口的售票處走去。售票處有一個很醒目的標牌,上邊寫著各項運動的價格,進入游泳池的價格是30元人民幣。她朝標牌上看了一眼,心里琢磨游一次泳就要收30塊錢,一個月要是游上10次泳,就得300塊錢,自己那點工資連收的房租加起來供房都緊張,哪來的閑錢游泳,心里就有了沉悶。
回到家里又無事可做,就坐在電視機跟前,拿著調控板不停地翻著頻道,也不知道哪個頻道的節目好看。
傍晚的時候,太陽墜落到西邊的海面上,消失了白日的酷熱,光線極為溫柔。有海風吹來,海面上有一波一波雪色的浪花,還有一波一波的海浪朝岸上撲吻。不遠不近的海面上,有幾艘歸家的漁船,很緩很緩地在海面上移動。海風帶來了涼爽,撫摸著人的膚肌,使人的肉體和精神都感到展脫和清爽。
稽莎莎走出房子,在小區里散步。前邊有一座小橋,橋下有一道小河,河水很清澈,能看到河里有魚在游戲。小徑和小河的兩邊全是樹木,她叫不出這些樹木的名字,但覺得這些樹木的造型很好,估計是名貴樹種,一般的閑花野草絕對不會被栽到這么高檔的花苑。在小徑的旁邊有亭子,亭子里坐著四五個年輕女人,一個比一個漂亮,都牽著很漂亮的狗狗,狗狗臥在她們腳前。
稽莎莎走到她們跟前的時候,才看清她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漂亮,無論身材、臉蛋、氣質、談吐都具有超群的漂亮。她想起馬曼麗說的帝都花苑的男人養的二奶,都參加過世界小姐的選美比賽,隨便哪一個都是某個城市的魁首。本來,她散步的路線要經過她們身邊,但她覺得自己走到她們面前,充其量給人家當個襯托,快到亭子跟前的時候就轉了個彎,朝另一邊走去。但是,她的身后還是傳來她們的聲音:這個女的是才來的;看樣子是個單身;我中午在樓上看了,她開的是捷達車;你看她穿的那身衣服,從上到下都是假牌子;她的停車位置就在那個角落,誰都不要的位置;那個位置便宜唄,一個月節省300多塊錢哩;她住的房子才45平米,在那棟樓的拐角,現在還有好幾套沒有賣出去;天哪,45平米,怎么能住,人進了房子到處磕碰,我住的房子200多平米,都覺得還小,45平米相當我的一個臥室;她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連裝修花上一百多萬,不如在別的小區買套大房子,住起來也方便;冒充富人唄,誰都知道住帝都花苑的都是巨富;巨富能冒充嗎,富人的氣派是用錢堆積起來的,沒有錢做鋪墊,只能是虛張聲勢。
稽莎莎看到迎面走來一個男人,離那個亭子還有五六十公尺,眼睛就直直地盯著那幾個女孩子,連余光都不肯分給她一點,好像根本沒有看到她一樣。
稽莎莎覺得心里像鋸齒在一下一下地拉,臉上燃燒出一團一團的火焰,胸腔中蔓延著劇烈的羞恥,再沒有散步的心思了,想匆匆回家,又怕這樣急急走開更讓她們笑話,裝成根本沒有聽見她們的說話,故意慢慢地朝回走去。把房門關上的時候,眼淚就控制不住地流出來,跑到沙發跟前,痛哭起來。
晚上,馬曼麗打來電話,說她想過來聊天,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稽莎莎的情緒已經好轉了,說我一個人住在這里,有什么不方便,你啥時候想來就啥時候來。
馬曼麗說萬一有個小白臉在你房子,說不定正在做刺激的事情,我要是貿然去了,你會恨死我。
稽莎莎說你看我都多大歲數了,哪有那份雅興?
馬曼麗說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還要鼓一鼓,當代人的營養好了,七十歲還有欲望哩!
馬曼麗進門以后,稽莎莎把傍晚散步的事情給她說了。
她思謀了一會兒說,這幾個女人真的參加過世界小姐的選美比賽,有的還闖過了好幾關。那些老板包養她們,年薪都是上百萬,房子都是兩百平米以上,開的都是寶馬奧迪。你不要計較她們,誰讓人家有掙大錢的本錢哩。咱們要是拿到了世界選美大賽的冠軍,年薪都得上千萬。
稽莎莎不再說話了,但住進帝都花苑的自傲感卻消失得沒有一點,代之的還是住進這里的屈辱。
馬曼麗見她情緒不好,又說她們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被人包養的東西嗎,一旦人家不要了,恐怕連咱們還不如。
稽莎莎沒有說話,她知道這些世界選美小姐,不可能沒有人包,像優績股樣搶著包。聽說有些老板為包養這些小姐,明爭暗斗使盡了手段。要是有老板玩膩了,只要說轉讓她們,馬上就有人拿著大筆的轉讓費排隊走后門。
馬曼麗長嘆口氣,說其實人家也幫那些老板賺了不少錢。
稽莎莎驚奇地問她們能幫老板賺錢?
馬曼麗說當然能幫老板賺錢,老板包養她們不僅僅是為了玩,要是僅僅是為了玩,一千塊錢到五星級大酒店的咖啡廳隨便找一個,長相不一定比她們差,何必花一百多萬養她們?老板包養了她們,和人談生意的時候就帶上她們,能包養世界選美小姐的老板絕對不是一般的老板,生意就好做。什么是品牌,這就是品牌。你聽誰說過哪個大老板把黃臉婆帶上談生意的,帶的都是美女!要是一個大單簽下來,幾千萬幾個億,包養她們的用處大著哩!
馬曼麗這么一說,稽莎莎心里的屈辱、不平就消泯了。人家憑著自己的臉蛋、身材、氣質,幫老板賺了那么多錢,牛逼一點也是應該的。自己沒有人家年輕,沒有人家漂亮,就沒有讓大老板包養的本錢,就不要眼紅人家。心里想通了,話也就多起來,對馬曼麗說你晚上要是沒事情,咱們一塊到西海岸公園散步去。
馬曼麗說今天不行,我一會兒就要回去。我們約定好了,今天是他在我這兒住的日子。
稽莎莎就說那你快點回去,不要人家都到了你還在我這兒。
馬曼麗說他不會來得這么早,一般都到了十一點以后。
稽莎莎又說你也得回去準備一下,洗洗澡化化妝。
馬曼麗說那能花多長時間,我在這再陪陪你。過了一會兒,馬曼麗又說莎莎你也該買條狗養,一個人過日子多孤獨,有條狗作伴感情也有個寄托。
稽莎莎說我現在連自己都養不起,哪有力氣養狗,月月都得付銀行的貸款,剩下的剛夠吃飯,連件衣服都不敢添。
馬曼麗琢磨了一會兒說,你說的也對,要是養狗就得養名貴狗,超過她們養的狗。但名貴狗一條都得好多萬,最好的狗比一輛奔馳車都值錢,咱們也養不起。
六
稽莎莎吃過早餐,到停車場把自己的捷達倒出來,準備朝出開的時候,有輛奔馳600朝出倒車,竟然對著她的捷達倒過來。她急忙摁響喇叭,企圖制止司機倒車。司機就好像沒有聽見她的喇叭,也好像沒有看見車后還有一輛捷達,繼續朝著她的捷達跟前倒,撞上捷達后還沒有停車,竟把捷達推著朝后邊倒。稽莎莎鉆出汽車,沖到司機跟前大聲喊,你沒看到我的車?我給你不停地打喇叭,你還朝后倒,把我的車都撞壞了!
司機從車里鉆出來,走到她的捷達跟前,把撞破的漆皮瞥了一眼,用腳在上邊輕輕踢了一下,說這也叫車?這是車嗎?是玩具!
稽莎莎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司機從車里取出皮包,在皮包里拿出一沓子錢,拍在捷達的引擎蓋上,說拿去,這些錢可以把你的車全部噴一遍漆!
稽莎莎氣得眼淚都差點流出來,說你這是欺負人!
司機嘿嘿一笑,說我怎么欺負你了,我倒車撞了你的車,負責給你賠償還不行?你要是不服氣,我把車停在這里,你用你的車朝我車上撞,撞成啥樣子我都不放個屁!
保安跑過來了,她像見到救星一樣,跑到保安跟前訴說自己的冤屈。奔馳車司機根本就不看保安一眼,鉆進車里做出準備開車的樣子。保安聽完她的訴說,從捷達的引擎蓋上拿起那筆錢塞到她手里,說人家王總把你的車撞了,一下子就賠你這么多錢,你還有啥不滿足的,要是我睡覺都能笑起來。這點漆,花不了兩百塊錢就補好了,剩下的就是凈賺的,多劃得來。要是我,巴不得天天有人撞我的車,天天都有這么多的收入!
保安又跑到奔馳車司機跟前,連著給人家鞠了幾下躬,說王總別生氣,快上班去吧。
奔馳車司機哈哈一笑,說她值得讓我生氣?
稽莎莎看著奔馳車毫無聲息地滑出了停車場,眼淚一串一串地涌出來。
七
下班以后,稽莎莎開車回到原來住的那個小區。她給租房子的客人說好了,今天是收房租的日子。她的捷達剛開進院子,卡車司機在窗戶里看到了,對老婆說干部姐回來啦。兩口子放下手上的活,朝著捷達跑過來。住在這個院子的民工,也看到了稽莎莎的捷達,都從房子里跑出來,把稽莎莎圍在中間,搶著叫干部姐,你回來啦!稽莎莎也高興地問候他們,最近可好。他們又七嘴八舌地回答,還行,咱們這些人能在城里扒拉一碗飯吃,餓不死就行,也不指望發財。發財是你們城里人的事情,咱這些農民一輩子要是能開上小轎車,就是祖宗燒了高香,老天爺保佑我們發財了。
卡車司機的老婆擠到她跟前,問干部姐你吃飯沒有?
稽莎莎說剛下班,還沒有吃。
卡車司機老婆就說你要是不嫌我們這些人骯臟,就在我家把飯吃了,省得回家再做飯。這么熱的天,做飯真是受罪!
稽莎莎不好意思地說怎么能在你們這里吃飯,我一個人好對付,隨便在街上買點吃的就行了。
司機老婆就說外邊的東西吃不得,就是大酒店的東西也沒有咱自己做的干凈。我在大酒店的餐廳干過幾個月,菜都不好好洗,隨便用水沖一下就行了,根本就沒有洗干凈,還貴得不行!卡車司機也給稽莎莎說,你就在我們這里把飯吃了。你一個月都不回來一次,回來一次就好好聚聚,大家都想著你哩!
稽莎莎見大家都這么說了,也就不再推辭了,心里覺得有種親情在滋生、蔓延,盈滿全身,精神和肉體都覺得安逸。
卡車司機見稽莎莎不再推辭了,趕忙對老婆說你快回去再準備幾個菜,讓干部姐好好吃一頓。又從褲兜里取出一張百元大票,塞到一個民工手里說,你騎車到超市買只文昌雞。又有一個民工對稽莎莎說干部姐,你就不要上去了,我們上去叫他把房租送下來。這么熱的天,爬一次樓出一身汗。說完就朝樓里跑去。卡車司機又對另幾個民工說,你們跟著他一塊上去,他們要是給干部姐下來送錢就算了,不下來就收拾他們。
稽莎莎急忙對著他們的背影喊,千萬不要打架。
卡車司機笑著對她說打不起來,我們這么多人,他敢和我們打!
卡車司機老婆把燉好的文昌雞盛了滿滿一大碗,端到稽莎莎跟前,說咱也沒有啥好東西,這碗雞肉你吃了,電視上都說雞肉很補養人!
稽莎莎看著滿滿一大碗雞肉,知道人家把大半只雞的肉都給自己了,就給司機老婆說你把肉分出來,大家都吃些。
司機老婆說我們這些人又沒病沒難的,身體壯實得跟水牛樣,吃了也是浪費。你們當干部的用腦子,用腦子最傷身體了,要好好補養一下。干部姐,你沒時間燉雞,我以后燉雞了給你打電話,你過來吃就行了,你有車過來很方便!
碗里的雞肉雞湯冒著騰騰熱氣,稽莎莎覺得眼睛一片模糊,不知道是雞肉的熱氣撲的還是淚水蒙的,停了好大功夫才說,等這邊房子的合同期滿了,我還要搬回來住。
在帝都花苑住了半年以后,稽莎莎發現在這個高檔花苑,自己的職務是最低的,房子是最小的,車是最低檔的,服裝是最差的,可能連存款都是最少的,停車位置是最偏僻的,在單身女人中的年齡是最大的,長相是最不行的,用的香水是最低劣的,男人走過去的回頭率也是最低的,沒有一樣比得過人家。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就是人家不說自己什么,自己都感覺低人一等。何況這里本來就是一個比拼金錢比拼享受的地方,自己沒有比拼的基礎硬要和人家比拼,受傷的只能是自己。
稽莎莎搬到帝都花苑以后,她們再聊天的時候就不到圣彼得堡了。馬曼麗都跑到稽莎莎那套四十五平米的房子,她提前在稽莎莎那里放了一筒臺灣的高山云霧茶,聊著喝著自有一種感覺。
這天,稽莎莎把茶泡好,給馬曼麗的杯子里倒了,說曼麗我準備搬回原來的房子住。
馬曼麗一愣,問你在這里住得好好的,為什么要搬走?
稽莎莎說你看這地方是我這種人住的嗎?硬要住在這里,是自己給自己找罪受。
馬曼麗琢磨了一會兒說也是,以你的收入和綜合條件確實不適合住在這里。你搬走以后,這套房子怎么辦?
稽莎莎說轉讓了,就是虧點錢也轉讓。我算計了,有了轉讓這套房子的錢,后半輩子過得綽綽有余,何必月月付貸款住在這里受罪?
稽莎莎把搬家選在周末的上午,還是那輛大卡車,還是那幫子民工。馬曼麗也跑來幫忙,把稽莎莎在這里受的委屈給民工們說了,民工們搬東西的時候,故意把號子喊得山響,故意弄出一些很大的聲音,為他們的干部姐出氣,也消除自己心理上的不平衡。
責任編輯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