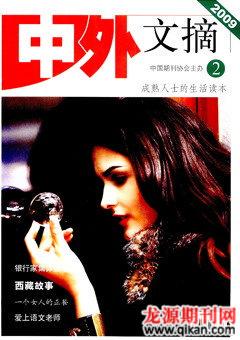舊金山暗夜的馬車
豬柳蛋
1869年的金發少年
少年邁著100年后他的同胞阿姆斯特朗登月時的太空步伐,往西走,進了杰克遜街。今天,他滿18歲了,第一次碰了酒,下場就是一次爛醉。此刻,街邊一溜華人店鋪在他看來都在虛軟地搖晃,小小的建筑們跟小小的中國人很相似,低低矮矮,黃黃瘦瘦,老老實實。草藥鋪,古董店,茶葉坊,瓷器行,中餐館,洗衣房。店面閃著窮酸的金字招牌,高懸油膩的紅綢燈籠。少年抱著一打母親交給他的衣物去給中國人洗。白人在1869年的時候,是把自己洗衣服當成一種恥辱的。路過一間中藥鋪的門口,少年看到了這樣的一幕情景。一個中國男人把一只黃狗用繩索套了,系緊脖子,再把繩子另一端拋到門框上頭。男人來到大門外,猛然拉下繩頭。門內傳來狗因被吊起而驚惶窒息的尖叫,幾分鐘后,聲音沒有了。少年回來時,中藥鋪里的大人和小孩都聚集在院子當中,沉默地熱鬧著。狗皮被利索地扒下來沖洗著,狗肉很快被切碎,連同土豆、胡蘿卜、香菜,和各種他們自制的神秘香料一起放進容器。中國人什么都吃,這不足為怪。奇怪的是他們從遠洋的貨輪偷渡而來時,小心翼翼地左手抱一只小公狗,籃里裝一只母的,你會以為他們是因為真心的疼愛才將寵物帶來,而事實是,疼愛只是為了讓狗繁殖更多的狗,留著以后解饞。
舊金山的冬季夜晚,少年站在馬路對面嘔吐。那戶中國人家已知趣地關上了大門。中國人總是比別的民族更有自知之明,更不愛惹是生非。來關門的是一個女孩子,穿著紅色的棉襖,梳著一條長長的辮子,像黑色的泉水。在因嘔吐而斷續的觀察里,少年看見她哭了,她是為了那條大狗而悲傷嗎?在一秒鐘內,他確認了這件事,就算她不承認,她那雙烏濃的黑眼睛也沒辦法說謊。
悲傷的中國眼睛
從那以后,少年替母親送洗衣服的差事就變得熱情起來。抱著一打家人的衣物,走進杰克遜街的深處,他的心里常常懷有某種希冀是關于一雙悲傷的中國眼睛。
終于,在第7次送衣服回來的路上,少年叫停了馬車。他走進漆黑的中藥鋪,學大人樣地坐在那磨得發亮的藤椅上,享受了一杯藥鋪太太沏的茶,等待藥鋪主人來把脈。這當兒,春天剛剛來到舊金山,海風吹拂之中,一切都在溫暖地泛潮。藥鋪主人松開扣在少年手腕上的三根手指,皺皺眉毛,心想小子,你健康得跟頭牛似的,來看什么病呢?但精明的中國人從不放過到手的生意,這是一次賓主盡歡的診療,少年和藥鋪主人都把沒病當有病,蝎蝎蜇蜇地交談后,少年在門口有幸遇見了那女孩兒。中國人家的女兒,是不會拋頭露面給人看見的,即使他們漂流到了異國也是如此。此時她正和同伴有說有笑地跨進門來,兩個酒窩在臉頰上深淺不一地浮現著。
“你好。”少年說。
“走好。”她說。
他們第一次的交談,以相逢開頭,以分別結尾,沒什么啰嗦,就像他們的年紀一樣簡單。但這談話所帶來的別的種種,可遠沒有談話本身好解釋了。他走出幾百米遠才發現他的心臟一直在狂跳不止,而他也記得她臉上酒窩的靜止,和隨之而來的臉頰泛紅。
任何年代都有一見鐘情
他們第一次約會,是在舊金山的某處海邊。那時,海邊還是純粹的海邊,除了他們倆以外,就是沾滿白色鳥糞的礁石。任何年代都有一見鐘情的男女,只是一見鐘情之后,不同年代的人會做出不同的反應。2008年,一男一女若是一見鐘情了,他們也許馬上上床,下了床如果發現跟對方廝守的難度過大,他們也會很懂事地決定無疾而終。可是1869年的男女不這樣想,100多年以前的人大多數是一根筋。即使那一年的他們只有18歲,他們考慮的也是如何共度此后全部生命這種長遠的大事。金發的白人小子,將一塊扁平的石頭投進海里,黑發的中國少女,抿緊了嘴唇盯著她的愛人。如果當時有人將這一幕入畫,我們也許會在多年以后發現他們當時所站立過的位置,正是如今的漁人碼頭。
“你愿意嫁給我嗎?”
“我愿意。”
這么說定了以后,他們開始籌劃一場前所未有的出逃。那時候,橫貫美國東西海岸的鐵道剛好接軌,他們想,1776英里的直線上,在任何地方下車,都有方興未艾的農場等著他們,都可以下車,勞作,定居,生活。少年從家里偷了一些錢,買了兩張去往鹽湖城的車票,當然,那里可能只是去往田納西或新奧爾良的轉折點。
他等在車站的人群里,數人,數到第279個姑娘的時候,他看到了翠珊。那是他父母給他訂的未婚妻,他從沒喜歡過她,因為她除了長得像一頭粉紅色的小豬以外,還極其嘴饞。但這一切的缺點在她旁邊的那位男士看來,顯然都可以忽略。翠珊拿著兩只幸運餅同時在啃,興奮使她的臉放光發亮。少年目睹她跟隨那個男士上了火車,這條大鐵路成全了多少年輕人的私奔啊!少年覺得一陣釋然,幾個月前被父母強迫訂婚而郁悶大醉的那次,此刻看來毫不值得。翠珊有翠珊的意中人,她遠沒他想的那么不可救藥。
可是他等的姑娘卻一直沒有來。老中醫有中醫的安排,他運籌帷幄女兒的婚事,保護掌上明珠的最好方式,就是讓她早點嫁人。
王的慈悲
家人給女孩安排的是隔壁中餐館王家的長子,那是個很好的年輕人,無論才能還是品格都被唐人街里的男女老少稱贊。但是女孩跟王見面的第一次就告訴他,她不愛他。
“你還沒有和我相處過,為什么就不給我機會呢?”
“我已經是他的人了。”
一百多年前,就算是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上的中國男人也還是拿女人的貞操很當回事的。他把寫有兩人生辰八字的庚帖在距她面孔幾寸遠的地方撕毀,先撕成兩半,再四半,她不敢去看他,不敢面對那雙無辜的眼睛,她唯一想做的就是把他手里那把紙揚散,替他完成他的憤怒。
50年以后的一天清早,她跟她的先生一起坐在窗前喝咖啡,吃早餐,欣賞庭院里新結出的葡萄柚,偶爾會想起那雙撕紙的手。粗壯的手指因為憤怒而一再地失去準星,到最后撕不動越來越厚的紙了,他就大叫起來,“我要殺了你們,我要殺了你們!”但卻也正是這個要殺人的人,成全了她一生的幸福。王后來成為華人中少有的百萬富翁之一,他一直寫信給她,但她從未回復,即使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后。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夜晚,她和她的金發少年約好再次私奔。這次她準備得很細致,包括刺繡的針線都裝在小包袱里了。幸好她不是小腳,不然,那段從藥店后門到火車站的路將格外艱險。饒是如此,她也事先練習過——在房間里練,因為他父母把她鎖了起來。
可以開鎖進去看望他的,除了父母,就只有王。“求求你放我走吧”,“沒有他我無法活下去”,“我會感謝你一輩子”,這些哀求的話在她嘴邊打轉,卻一句也沒說出口,她用的還是那句最無情的威脅:如果今晚你不放我走,我就死給你看。
光明不僅是馬車上的燈
王甚至幫她叫了一輛馬車。那馬車的車頭有兩盞燈,在暗夜的路上,那是唯一的光亮。坐在她身邊的王,很沮喪,但在她的記憶里,他的沮喪始終和光明有關。人性的光亮,是暗夜燈火。王把她親手交給了他的情敵。誰說一百年前在舊金山的中國男人都是梳長辮子、委頓自卑的小移民?王就讓她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她忽然有那么一點后悔,這后悔不為人知,也不能讓自己品得太透,她抬起頭看著王,聽見他正用英語對他的情敵說:請你要一直愛她,因為她是我一直愛著的。
她從來不知道,早在她第一次光臨王家的珠寶店——她十四歲,或者十五歲的夏天,她就被他愛著了。她光試不買,把翡翠白玉紅寶綠寶玩個遍,覺得滿足,笑到發顛。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就看到她在玩這最沒出息的游戲,但他全盤接受。他想,這也許就是愛,她咯咯咯小母雞一樣的笑聲,很俗氣,但他覺得好聽。那么,就愛吧,他對自己說,娶她,好好待她,聽她小母雞一樣笑。
他最終沒有做到跟自己的這份承諾,把她放跑了。但又確實做到了他所承諾的,愛了她一輩子。這君子承諾,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