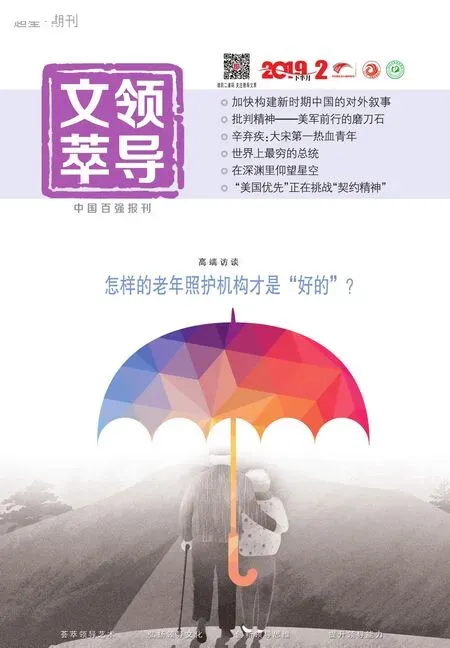筆桿子的決戰
[澳]雪兒簡思
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國第一次形成了全國范圍內的共識,日本的軍刀終于撕開了中國士大夫傲慢的外殼。但即使涵蓋范圍極廣的戊戌變法,也沒能如明治維新那樣進入“深水區”,滿清小團體將維護自身利益的準則包裝成了對改革的穩健持重,這進而導致了改革成為一場野心家的鬧劇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劇。
中國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燾曾認為,在洋務方面,李鴻章“能見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楨“能盡其實”。身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的確在提倡西學、實行洋務方面十分扎實細致。但對體力勞動的鄙視甚至滲透到他的管理中,盡管他十分注重科學技術,但多停留在書本學習上,他和他的團隊很少深入到船舶設計和建造的第一線身體力行,科技的應用成為領班工長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伊藤與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國留學的三個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當時伊藤病得甚至差點喪命。明治時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學德國學習法律時,居然還涉獵醫藥、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啤酒、紙幣、地毯等的制作,動手能力很強。
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成為兩國知識分子乃至兩國國家特性的分野。中日兩個民族在甲午戰爭中的首次對決,不僅是軍事PK,也是立憲制度與專制制度的PK,更是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PK。
實行了君主立憲的日本,雖然天皇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但戰爭的發動還是更多地取決于以伊藤博文為首的內閣。日本知識分子成為政權的核心力量,有足夠的權力對全國資源進行動員和運用。反觀中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辦事者”,卻不得不在正面抗敵的同時,還要在背面應對以翁同 為代表的“評論者”的冷嘲熱諷乃至落井下石,而在最高統治者看來,“將相不和”從來就不是壞事。更為驚心的是,中日戰爭似乎演變成了日本與北洋的戰爭,戰力尚在的南洋艦隊袖手旁觀,更別說執行清議所夸夸其談地揮軍直搗日本本土,演一則圍魏救趙的好戲了,西方報道就曾略帶尖刻地指出甲午戰爭其實是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
日本從執政團隊到前線的中高級軍官,幾乎是清一色的“海龜”團隊,即使沒有留過洋的一些陸軍將領,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軍事訓練,受過近代教育。中國方面則從李鴻章開始,多是從未跨出過國門的“土鱉”,這導致雙方在國際形象塑造上大相徑庭。日本的決策層年富力強,伊藤博文時年五十四歲,而中國決策層相對老邁,李鴻章當時已經是年逾七旬的老翁。這簡直就是旭日帝國挑戰老大帝國的生動寫照。
日本盡管有內爭,但“民主集中制”執行得很好,鬧歸鬧,朝野還是一心對外,甲午戰爭令日本國內各階層空前統一,明治維新、西南戰爭等造成的隔閡,迅速被彌和。而中國方面,清議擾擾,說風涼話的、下拌子的、瞎起哄的,應有盡有,甚至還有乘機誣陷李鴻章父子通敵賣國的,令李鴻章憤怒異常。
甲午戰爭的海戰戰場,則成為雙方新一代“海龜”將領的角斗場。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的不少軍官,多有留洋的經驗,有的甚至是同學或校友。同樣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樣的歐洲產鐵甲軍艦,同樣的完全用英語進行的戰場指揮,背后較量的就是軍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艦隊之敗,實在非戰之罪也……
硝煙尚未散盡時,伊藤與李鴻章在馬關開始談判。在國家利權爭奪外,雙方也涉及了很廣泛的話題。伊藤建議大清“必須對明于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留英時期的好友羅豐祿、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鴻章側后。當年的英倫同窗,如今一方貴為國家元首,另一方卻還側身幕僚。據說李鴻章對此亦深有同感,回國后奏請將羅、伍二人起用,分別出使英、美。但終其一生,二人與昔日同學伊藤在功業上終究難比。這種個人命運的差別,正是兩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戲劇性對照。
當李鴻章用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情感牌”來和伊藤套近乎時,伊藤一邊用“中堂之論,甚愜我心”順勢化解,一邊將一個沉甸甸的話題扔還給李鴻章:“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甲午戰爭后,中國士大夫果然被震驚了,但所掀起的第一波浪潮,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將責任悉數歸咎到李鴻章“賣國”,拒簽馬關條約、請誅李鴻章的呼聲響徹朝野。
隨后,知識分子再度淪為政爭工具和犧牲品,而民間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緒大爆發則導致破壞力巨大的義和團運動;逃亡海外的所謂改革者,迅速地將悲情變為斂財乃至大交桃花運(看看康“圣人”在海外的“人財兩得”)的道具;而無論海內外的知識分子,從此也認定了“槍桿子”強過“筆桿子”,握筆的手開始紛紛拿槍,其殺傷力竟是武夫們自嘆不如的。
甲午戰爭也同樣對日本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曾經的平民主義者全都在勝利,尤其是巨大的戰爭紅利帶來的激情中消失,國家主義成為日本主旋律。
梁啟超認為無論是地位還是功勛,伊藤都遜色許多,但有一事卻占足上風:他“曾游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梁啟超認定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實,梁啟超還是沒能看透或有難言之隱:只要看看李鴻章出訪歐美的精彩對談,以其才干和閱歷,怎會不知“政治之本原”?但勢禁形格,李鴻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同樣是梁啟超所記,中俄伊犁之戰時,李鴻章征詢前來拜訪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意見,戈登說:“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權以大加整頓耳。君如有意,仆當執鞭效犬馬之勞”。
李鴻章聽罷,“瞿然改容,舌矯而不能言”。不知當日李中堂與戈登有否青梅煮酒,或許中堂大人也希望有驚雷掠過而落箸吧?
(摘自《先鋒國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