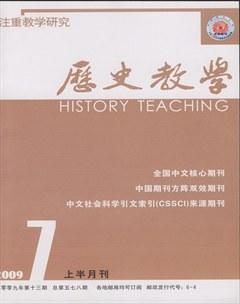再談對“過程”目標化的理解
陳志剛
[關鍵詞]過程與方法,課程理論,學習思維
[中圖分類號]G63[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0457—6241(2009)13—0038—04
拜讀了李惠軍老師的《“過程”目標化,值得慎思!》《“過程”目標化,值得深思!》(下簡稱二論)之后,我深深欽佩李老師的執著探索精神,也為他淵博的學識所打動。正如李老師所說,我與他的許多看法并無分歧,尤其是在“過程”的重要性認識上。然而雙方為什么會得出不同的認識呢?實際是分析問題所站的角度不同所致。
細讀李老師的“二論”,不難看出他對該問題的論證均是立足于史學研究的角度。,雖然所論有據,但對于“過程”目標化問題,僅從語義學概念或史學研究的方式去理解、分析,就過于片面了。
“過程與方法”目標,是此次課改的一個亮點與創新。“過程”目標化,是面向基礎教育所有學科,立足于學生的學習,借鑒了當前世界課程理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不同學科教學中,“過程”目標化的實施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由于“過程”目標化的確立不是單純針對歷史學科教育而設計的,因此,我們不能僅從史學研究角度去理解與實施,必須清楚課程改革的背景,了解相關的課程與教學目標的設計理論。下面筆者談一點-'hA對此問題的“參悟”,與各位老師共享,希冀能夠解答李老師心中的疑問。
第一,三維目標提出的理論依據。
課程改革提出三維目標的理論依據,主要來源于布盧姆的目標分類學說和斯騰豪斯的過程模式理論。
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的一些教育學家和心理學家,倡導用可觀察和可測量的行為來陳述教育目標,旨在為教學及其評價提供具體的指導。其中,美國教育家布盧姆等人的目標分類學有著較大的影響。布盧姆等人將教育目標分為認知、情感、動作技能三個領域,每個領域的目標又由低到高分成若干層次,以行為結果為目標分類依據,創立了教學目標分類理論、掌握學習理論和教育評價理論。這些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初引入我國以后,引起了較大的反響。由于我國基礎教育長期受凱洛夫教育學的影響,老師們在備課過程中,習慣于從“教”的角度出發,揣摩學生學習的基礎、設計教學目的。這種教學設計缺乏科學的理論依據,具有主觀性,不利于教學目標的實現。因此,此次課程改革提出的三維目標,各科課程標準在許多方面都沿用了布盧姆目標分類學的思想,力圖使教學目標的設計具有可操作性。
布盧姆教育目標理論實際是一種行為主義學習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學習過程是一種漸進的“嘗試與錯誤”,直至最后成功的過程,它側重知識、技能的學習,認為強化是學習成功的關鍵。“行為目標”的設計簡單明了、易于把握,具有精確性、具體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當教師以“行為目標”的形式陳述教學內容時,有助于教師有效控制教學過程,對于一些相對簡單的教育目標的達成非常有益。但由于教育的真正價值,是使個體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而不是僅僅形成一些可以觀察到的行為,因為人的許多高級心理素質(如價值觀、理解、情感、態度、審美情趣等)是很難用外顯的、可觀察的行為來預先具體化的。如果試圖用行為方式陳述所有課程目標,顯然容易扼殺學生學習的主體性。
針對行為目標的種種缺陷,英國課程論專家斯騰豪斯等人受杜威“教育即生長”思想的影響,提出了教育的過程模式,強調教育目標的生成性。他認為學校教育主要包括三個過程:“訓練”是使學生獲得動作技能的過程,“教學”是使學生獲得知識信息的過程,“引導”是使學生獲得以知識體系為支持的批判性、創造性思維能力,使學生進入“知識的本質”。斯騰豪斯認為,教育的本質是“引導”,即引導兒童進入文化知識之中進行探究。因此,與批判性、創造性的思維能力相比,技能和知識信息都是次要的和工具性的,故“訓練”和“教學”理應服從于“引導”的過程。斯騰豪斯實際上是用“生成性目標”取代了“行為目標”。“生成性目標”是在教育情境之中隨著教育過程的展開而自然生成的課程與教學目標,它是人的經驗生長的內在要求,強調學生、教師與教育情境的交互作用,注重學生批判、反思能力的發展,學生主體性的培養被看做是目標,而教師主體性的發揮則是手段,是目標得以實現的保證。“生成性目標”取向消解了“行為目標”取向所存在的過程與結果、手段與目的之間的二元對立。這種取向下的教學目標,就是學生在教育過程中、在與教育情境的交互作用中所產生的自己的目標,而不是課程開發者和教師所強加的目標。運用“生成性目標”就意味著教師要能夠與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要求學生主動發現探究。
此外,美國課程學者艾斯納認為課程計劃中存在的兩種不同的教育目標:“教學性目標”和“表現性目標”。“教學性目標”是在課程計劃中預先規定好的,明確指出學生在完成學習活動后所應習得的具體行為,類似于行為目標。“表現性目標”是指每一個學生個體在與具體教育情境的種種“際遇”中所產生的個性化的創造性表現,它不是規定學生在完成學習活動后獲得的行為,而是描述教育中的“際遇”:指明兒童將在其中學習活動的情境,將要處理的問題、從事的活動任務,但它不指明兒童將從這些“際遇”中學到什么。使用“表現性目標”,人們期望的不是學生反應的一致性,而是反應的多樣性、個體性,旨在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強調個性化。對“表現性目標”的評價不能像行為目標那樣,追求結果與預期目標的一一對應關系,對學生活動及其結果的評價應該是一種鑒賞式的批評,依其創造性和個性特色檢查其質量與重要性。
此次課程改革創造性地提出了“過程與方法”目標,力圖在課程與教學目標設計上吸取發達國家課程研究與實踐的精華,消除基礎教育教學中單純追求行為目標所產生的缺失。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過程”目標就是指上述的“生成性目標”和“表現性目標”,因為它們注重課程實施的過程,尤其是“生成性目標”。“過程”目標對教育價值的追求更符合教育的精神。它把教師和學生看作教育過程、教育情境的共同創造體,學生是自己發展的主體,教師是發展的評判者、指導者。課程改革強調“過程”目標,并不是說目標設置不應該追求具體性和可操作性,而是說對具體性和可操作性的追求,不應以犧牲學習者自身價值特性為代價。
可見,“過程”目標不是我們傳統習慣理解的結果性或行為性目標,也不是一種結果。如果認為“目標是指要達到的結果,‘過程怎么能是結果呢?這不是犯了邏輯錯誤嗎?”就會對“過程”目標產生誤解。對于“過程”目標化問題產生的背景性知識,《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語焉不詳,各種課程標準又是教學大綱的翻版,內容過于教條化,均未加以解釋,遂有老師們的種種誤讀,例如,有的老師認為“過程與方法”既指老師“教”的過程與方法,又指學生“學”的過程與方法。實際上,教師的“教”的過程與方法只是實現三維目標的手段。
對于“過程”目標化的質疑與紛爭,也并非歷史學科教育中才有,所有學科在課程改革實施初期均遇到同類的問題。由于李老師在對“過程”目標化的分析中,未能從課程與教學設計的相關理論出發來理解過程性目標,故有將“過程與方法”改為“理論與方法”的認識。所以,筆者才說李老師可能“不太了解有關課程與教學設計的相關理論”。但這一說法必須從上下文邏輯分析來理解。有中學老師在自己的博客中稱筆者此句是“文革式的批判”,實在是有些斷章取義了。
第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為什么一定要將“過程與方法”確定為教學目標呢?很多學者均從“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形象比喻出發進行解釋:這是學會學習的需要。聶幼犁教授就是從這一角度進行闡釋的。李老師在“二論”中將此論述歸功于我并加以批評,雖然筆者完全贊同聶教授的分析,但不敢冒功,特此強調。教學行為的展開是一個過程,教育活動的教育性就貫穿在這個過程中。知識的獲得需要思考,具有不確定性,學生的學習領悟能力也因人而異,所以教師在“過程與方法”中,要把自己確定的知識通過對話、提問等方法來還原知識的不確定性,要求學生進行探究。學生探究歷史的過程,就是獲得知識、構建歷史認識的過程,經過自己的理解,實現對知識與技能的內化。這種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探究的自主學習,委實是授之以“漁”,旨在提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自為能力。學生只有掌握了學習方法,才是掌握了終身學習的法寶,得以實現可持續性發展。聶教授的文章對此論述詳細,筆者不再學舌,建議李老師在了解上述三維目標提出的背景依據后,重新反思聶教授的深刻分析,相信會有新的體會。
第三,“過程”目標化強調的是實際的“過程”實施,而非表面化、形式化的活動。
“所謂過程是指讓學生經歷知識形成過程,在體驗、活動、探究中進行學習,方法指掌握各類知識的學習方式與策略,學會學習,學會反思,學會創造,能對自己的學習過程及其結果進行有效監控”目。“過程與方法”目標提出了兩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學生掌握學習的方法,即學生能夠學會運用多種手段獲取信息,并對信息進行加工,對學習內容、過程和方法進行反思和調控,提高自主學習的能力;二是掌握歷史探究的方法和形成問題意識,即要求學生經歷知識形成的探究過程,進一步掌握探究中常用的、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未來探究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并在此過程中養成問題意識的習慣,提高思維能力。
當我們把上述要求視為教學的。目標時,顯然強調的是學生獲得歷史認識的“過程和方法”,也就是學生通過自己的親身實踐,積極參與到歷史學習的“過程”中來,通過種種“親歷”行為,實現“會學”“自學”的目的。這種“過程”實施的目的不是追求教學中學生活動行為形式化,而是提高學習者自身的價值特性。李老師批評的當前歷史教學中的問題格式化、互動庸俗化等現象,實際是一些老師沒有理解“過程與方法”所追求的實質,以為只要采用問答、小話劇等活動方式,使學生記住課本上的知識內容,就是“過程與方法”,這些致使“過程”教學展開不充分、不到位,走向了形式化。事實上,在“過程”中,老師們要特別注意關注知識、技能形成過程,重視知識技能學習方法與策略的指導,并在這一過程中發展能力、培養情感。“具體地講:(1)改變知識呈現、講述、評價方式,使知識動態化、過程化;(2)讓學生經歷知識形成過程,在活動、實踐、探究中體驗知識的豐富蘊涵,獲得知識多方面的價值,實現知識向能力、情感、素質的轉化,彰顯知識的意義;(3)引導學生掌握知識、技能學習的方法與策略,學會學習,學會創造”。在這個目標的實現中,老師們要時刻關注學生的思維發展,引導學生。
細化到具體內涵,“過程”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概括的、外在的學術活動的過程,比如資料搜集、問題探究、自主學習等等;二是內在的、具體的學習思維的過程,比如搜集資料、探究問題、編輯史料的過程與方法等等。資料搜集、問題探究不是教學目標,而學會如何搜集資料,如何探究問題才是教學目標。其中第二層意思尤為重要。因為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思維方式及其能力、創造能力等等,老師是無法教給學生的,這些能力與思維的方法是潛伏在孩子本人的生理和心理層面的特質,需要老師創造一個環境、提供一個機會讓學生感悟、體驗、實踐。而思維技能的保持,“將會是他們中學、大學學習的有利條件”。“當歷史專業的學生或理科學生畢業后當上酒店經理、看護或企業家時,所學的歷史事件的日期、計算公式早已忘光了,永遠伴隨他們的就是思維能力,這才是真正的永不失色的教育的精華”。這就是“過程”目標所追求的,也是形式化的“活動”教學無法做到的。
三維目標中,“知識與技能”目標相對來說具有可操作性和確定性,比較好設計。而“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具有潛隱性、不確定性和隨機生成性,往往使老師們在具體教學設計中感到茫然。李老師在“二論”中,質疑有哪些行為動詞可以適用于“過程與方法”目標的設計,并提議我采用“造句”的方式,設計一些“過程”目標陳述的例子。其實,教學目標的陳述存在兩類基本方式,一是采用結果性目標的方式,即明確告訴人們學生的學習結果是什么,所采用的行為動詞要求明確,可測量、可評價。這種方式指向可以結果化的教學目標,主要應用于“知識與能力”領域。二是采用體驗性或表現性目標的方式,即描述學生自己的心理感受和體驗,安排學生表現自己的機會,所采用的行為動詞往往是體驗性的和過程性的,這種方式指向無需結果化的或難以結果化的教學目標,主要應用于“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領域。對于動態生成性的“過程”目標,國家課程標準提供了一系列的“體驗性目標的學習水平與行為動詞”,希望能夠幫助老師們設計出合理的、較理想的“過程”目標。限于篇幅,不再摘錄這些動詞。
值得注意的是,“過程”學習目標有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教師也很難預期一定的教學活動后學生的內在心理會發生什么變化。在設計的“過程”目標中,我們可以明確規定學生必須參加哪些活動,而不用精確規定每個學生必須從這些活動中習得什么。怎樣設計呢?我們還是來看看一些專家提供的例子,“能接受所提供的學習方法,并嘗試在學習活動中使用”“能辨別出需要學習的知識、需要解決的問題;能嘗試各種自己掌握的手段收集相關的信息”“能從多種角度假設問題的目標,從多種途徑思考問題,從而確定思考的方向或正確的答案”“能將遇到的問題、知識、規律依據某種標準進行分類和聯系”“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步驟,遵循這些規則來解決問題,并建立起相應的評估與反饋,從而完善規則”“能根據問題的需要制定出合適的解決方案及評估標準,實施過程中能及時反思、調整方案,最終形成新的規則”等。這些旨在關注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變化,教條的規定顯然與此相悖。
“過程與方法”目標是指對所學習、選擇的知識與技能的反思、批判和運用。要想在教學中將“過程”目標落在實處,我們就要把“過程與方法”目標的實現滲透在知識與能力的教學之中,重視教與學的方式的配合,以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學生的認知規律、教師的素養以及教學條件為依據,選擇課堂教學的方式。同時重視學生活動與實踐的設計,重視學生之間、師生之間的有效交流與互動,選準探究內容、創設探究情境、營造探究氛圍,使學生能夠親歷探究過程,啟迪他們的探究思維,實現歷史探究的價值。
歷史新課程強調學習的過程,有沒有忽視對歷史知識掌握的傾向呢?此次課程改革始終認為,結論與過程的關系是教學中一對十分重要的關系。“無論對哪一門學科而言,學科的探究過程和方法論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價值,學科的概念原理體系只有和相應探究過程及方法論結合起來,才能有助于學生形成一個既有肌體又有靈魂的活的學科認知結構”。國內一些學者受布魯納“知識是過程,不是結果”等言論的影響,認為學習過程的重要性大于學習結果,探究學習就是要求學生像科學家一樣進行研究,結論并不重要。這些觀點充斥于某些新課程培訓叢書之中,給老師帶來誤解。知識的獲取固然不是學習的唯一目標,但離開了知識的傳授,沒有基本知識的牢固掌握為基礎,探究就成了無源之水,能力培養目標也成了空中樓閣。同時學生掌握的知識的數量、質量、結構等狀況和水平,也決定了學生們能在什么水平上開展探究活動。掌握知識與發展智力相結合是一條規律性的教學要求,歷史教學必須以一定的歷史知識為基礎,既重知識又重結果。課程改革并沒有忽視知識掌握問題,早在2004年10月始,《全球教育展望》雜志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曾刊載系列文章論述這一問題。筆者不復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