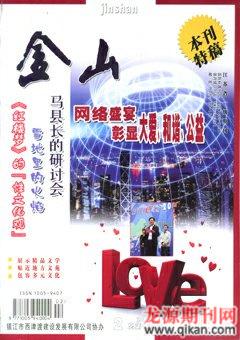古街之聲
張崢嶸
古街有古街的聲音,鄉(xiāng)村有鄉(xiāng)村的聲音,但鄉(xiāng)村即使有聲,也是靜的;古街即使無聲,也是動的。
一彎新月,十里荷花,十里蛙鳴,這是鄉(xiāng)村式的喧鬧,但意境卻是靜的;而古街就是入夜了,街聲漸息了,但仔細(xì)聽,仍能感覺到古街的呼吸、靜夜中暗伏的驛動。因為古街所處的城市是聲音的世界,是喧鬧的化身。
古街所發(fā)出的聲音是有著自身歷史的。處于鎮(zhèn)江西北端的西津渡街,古代之聲自有悠遠(yuǎn)的韻味與獨特的個性,用心去傾聽,總能領(lǐng)會到其妙處:“江風(fēng)白浪起,愁殺渡頭人”,這是唐朝的孟浩然聽到的西津渡口的聲音;“浩浩波聲險,蒼蒼天色愁”,這是戴叔倫聽到的西津渡江面的聲音;“潮落夜江斜月里,兩三星火是瓜洲”,這是晚唐詩人張祜在小山樓聽到的津渡夜晚的聲音;“夜半潮來風(fēng)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這是宋朝詩人蘇軾聽到的津渡江面夜晚的聲音。江之南,岸之上,樓之外,舟之中,吟的是風(fēng)高浪急的西津渡江面,誦的是月色迷離的西津渡口。月迷津渡,濤聲撩撥鄉(xiāng)愁。雖然時過境遷,但我們?nèi)匀荒軓倪@些古詩詞中,聽到古西津渡江面的濤聲,感受到江風(fēng)陣陣。
進(jìn)入近現(xiàn)代,歷史的車輪加快,鎮(zhèn)江日趨發(fā)達(dá),但也變得越來越喧囂、躁動。沉睡中的西津渡歷史古街,質(zhì)樸淳厚,相對安靜。習(xí)慣了高樓大廈的人們,會選擇節(jié)假日來到這里,他們從遠(yuǎn)處匆匆趕來,在飛閣流丹的民居里,在層巒聳翠的環(huán)境中,在莊嚴(yán)神秘的白塔下,放慢的腳步,讓心靈受到撫慰。
江南的風(fēng)和陽光照在古樸的老街上,踏著石板路,來到小山樓前,聽到從一家店鋪里傳來優(yōu)雅的古箏聲,時而低回、時而高亢的質(zhì)樸的奏鳴,蝕人心骨的滄桑,絲絲滲出又直入心魂。每一首樂曲,似乎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不論訴說的是什么,總給人以愿望和希冀。一種精神的向往,那么純真。蔚藍(lán)天空的浮云為之駐留。
沒有矯揉造作,沒有應(yīng)景的追求,有的只是對天地人和的純美訴求,無論在音樂里外,你皆能看到無瑕性靈的嫣然閃現(xiàn)。如果天籟讓人覺得神秘遙遠(yuǎn),那么這些普通百姓的演奏只會讓你感到親切。
這樣的藝術(shù)其實不是用來表演的,而是表演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灑滿月光的店鋪里,把廉價的老酒喝的微醉,歌喉和手腳也都半醉,然后古箏悠悠響起,行如高山流水,暢如天馬行空……
這樣的音樂是用心演奏的,也只能用心去傾聽。
音樂是智慧的語言,要凈了心才可感受。音樂那么多態(tài),是水樣的東西。我喜歡音樂,音樂里有太多我喜愛的東西,一串串愉悅跳躍,自在盤旋,游走在感性與知性的邊緣。仿佛躺在純潔無瑕的白云上面慢慢漂浮,四周一片安詳,所有的注意力都被樂曲吸引,在這躁動而凡俗的日子里給內(nèi)心平添寧靜!心靈放飛在這一片質(zhì)樸醇厚、充滿滄桑的歷史古街,觸摸著風(fēng)和陽光、青山與浮云。大自然的慈愛與恩典,在頃刻間灑滿荒蕪的心田。
忽然想起莊子的“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莊子將宇宙日月之光與心靈藝術(shù)之光交織在一起,在把自然音樂化的同時,也把音樂自然化,這是對人生和藝術(shù)靈性的徹悟。而民間藝術(shù)似乎天生就具有了這種秉性。
民間音樂最近好像紅了起來。使之紅起來的是有些所謂的“音樂人”。他們對民間音樂懷著獵奇的心情,并且按照自己的喜好進(jìn)行裁剪。其實民間音樂不需要這種施舍,它像一切原始的生命一樣早已存活了無數(shù)年,并且還將繼續(xù)存活下去。它并不需要流行化,不需要時尚作為點綴,不需要流行增添魅力,也無所謂是否進(jìn)入陽春白雪。
民間音樂是自得其樂的音樂,表達(dá)的同樣是人們內(nèi)心最深處的感情和想象,在任何情境下都會喚起生活的力量,給所有演奏者和傾聽者精神的支撐。
走在古色古香的老街上,聆聽著行人的腳步發(fā)出的細(xì)碎聲響,感受著小街古渡千百年來沉淀的古韻。但愿這種平和的古街之聲永遠(yuǎn)彌漫在每一個角落!但愿我能經(jīng)常享受到這滄桑而又直入心魂的純美訴求!無論是現(xiàn)在還是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