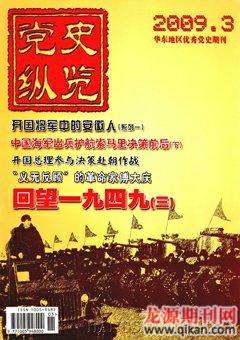胡耀邦與鄉土文學作家劉紹棠的不解之緣
楊建民

劉紹棠是我國著名的鄉土文學作家。他13歲時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作品,1952年高中一年級時,發表了小說《青枝綠葉》,引起廣泛關注,作品不僅被臧克家主編的《新華月報》文藝版轉載,得到著名作家、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圣陶的賞識,被編入1953年高中二年級語文教科書。劉紹棠也因此被人們譽為“神童”。之后,劉紹棠成了團中央的重點培養對象。從此,他便與當時主持團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聯系。胡耀邦甚至親自為劉紹棠設計長期創作發展規劃。這一規劃后來雖因許多客觀因素未能實現,但劉紹棠在人生多個重要關頭,都得到了胡耀邦的指導和幫助,兩人結下了一段“不解之緣”。
胡耀邦幫助制訂“五年計劃”
劉紹棠受到胡耀邦的關注和培養,是在他文學創作的初始階段。1951年,剛滿15歲的劉紹棠寫出了小說《紅花》。稿件寄到《中國青年報》后,受到該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著名作家柳青的高度贊賞。經與總編陳緒宗商定,這篇小說被特別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還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發,并加以編者按語大力推薦:“這篇稿子的作者,是一個16歲的青年團員,雖然是一篇習作,但寫得相當動人。希望作者繼續努力,寫出更好的作品來。”這篇小說的發表,使劉紹棠引起了文藝界和廣大讀者注意,并由此引起胡耀邦的注意。
《中國青年報》是團中央的機關報。在這一時期,劉紹棠的重點作品,多交該報發表。為此,《中國青年報》還特別聘請了當時已頗有創作成績的作家康濯對劉紹棠予以指點。劉紹棠早期代表作《青枝綠葉》,就是由康濯對初稿進行指導后完成的。此外,團中央還請沙汀、周立波、嚴文井等前輩作家為劉紹棠看稿,還舉行講習會,讓劉紹棠與更多作家及青年作者見面,使他在創作初期便走在一條良好而健康的發展道路上。
在胡耀邦的關注下,1952年,團中央安排劉紹棠到河北深縣農村體驗生活。8月到9月中旬,劉紹棠先后在段家佐村和賈各莊村住了一個月。賈各莊的房東賈大伯,愛惜一頭大青騾子,天下雨時,他會把衣裳脫下罩在騾子身上。這情景使劉紹棠印象深刻,回學校后,他便以此素材一口氣寫出了他的另一短篇小說代表作《大青騾子》。
后來,《紅花》、《青枝綠葉》、《大青騾子》、《擺渡》這幾篇在團中央直接關心下產生的作品,被編入了劉紹棠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這部以《青枝綠葉》命名的集子,于1953年6月,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當時劉紹棠才17歲,出版小說集的同年,劉紹棠還入了黨,真可謂少年得意。
在劉紹棠創作這幾篇小說的日子里,胡耀邦曾多次與他談話。談話內容包括創作、做人和為文……劉紹棠也視胡耀邦為可尊敬、可信賴的師長。在拿到《青枝綠葉》樣書后,劉紹棠將第一本樣書交給自己所在黨支部作為獻禮,第二本便呈贈給一直關心自己的胡耀邦。這本小說集,胡耀邦也很喜歡。他從頭到尾看過一遍,并對其中《擺渡》一篇頗為欣賞。他還十分誠懇地指出其不足:“為了體現黨的領導,便寫了個黨支部書記講一些大道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敗筆。”
劉紹棠入黨后,胡耀邦把他找來,交談了許久,并為他的創作發展設計了一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留存了下來,即:第一年到團區委工作,地點在東北地區;第二、三年到團縣委工作(因為這一步較重要,故須多一年),地點一是西北地區,一是西南地區;第四、五年到團省委工作,一年在中南地區,一年在華東地區;最后,再返回團中央從事專業創作。因劉紹棠是京郊人,對華北一帶生活比較熟悉,這個計劃便沒有安排華北地區。
胡耀邦的這個“五年計劃”,對一個長線作家來說,可以說是十分必要的。通過在全國不同區域任職,一方面可以對全國整個情況有較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開闊眼界和胸懷。有意思的是,這個“五年計劃”里,沒有給上大學留下時間。據劉紹棠后來回憶:“他(胡耀邦)不贊成我上大學……”這種安排,具體到劉紹棠,應當說是可行的。上大學對于一個已有相當根基、又正處在創作旺盛期的作家來說,并非十分合適。這一點從后來劉紹棠考入北京大學,不久又主動從北京大學退學的經歷來看,的確是值得人們體味的。
胡耀邦協調從北京大學退學
劉紹棠在創作道路上能夠取得巨大成就,和他能夠舍棄一些在別人看來應當珍視的機會有關。而他的這些舍棄,許多都得到胡耀邦的直接建議和幫助。
劉紹棠在讀高中階段,有過一次極難得的留學蘇聯的機會。20世紀50年代初期,國家為了加快發展,快出人才,向對華友好的蘇聯派出了許多留學生。當時全國大學生還很少,因而在挑選留學生時,也放寬到高中生中的優秀分子。
劉紹棠當時已經入了黨,政治可靠,又出版了一部小說集,因此,他當時所在的北京通州潞河中學便推薦他留蘇。
但是,當時國家為加快經濟發展,培養的人才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劉紹棠此時得到的名額,是到蘇聯列寧格勒學習化工專業。這讓他很傷腦筋。因為劉紹棠當時的學習成績整體雖然很好,可由于開始創作,自然較為偏于文科。初中、高中開設的化學課,他的成績并不理想。當時按優、良、中、差、劣五級計分,初中時他還能得到“良”,到了高中,卻只能得個“中”。況且此時他文學創作勢頭正盛,倘如一下子去蘇聯專門學化工,那可能會學習、創作兩頭不討好。因此,出國留學這樣的好事,別人求之不得,劉紹棠卻主動要求放棄。對此,學校和有關部門都不同意,劉紹棠急得沒辦法,便想起胡耀邦。他趕緊寫了一封信,托人帶去請胡耀邦幫助。不久,胡耀邦通過團中央繪通州學校及有關部門去函,明確表示準備將劉紹棠培養為專業作家,這才免了劉紹棠的“留學”之“怕”。
胡耀邦為劉紹棠設計的“五年計劃”,后來并沒有較好地實施下去。就在劉紹棠高中畢業的1954年,國家為了加快發展,最大限度地招收大學生。當年高中畢業生只有5萬多,國家的招生計劃卻是11萬。黨中央下達文件規定,所有應屆高中畢業生必須報考大學,任何方面不能截留。劉紹棠只能暫時放棄“五年計劃”,先行報考大學。
1954年,劉紹棠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而他的同學女友考入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這時的劉紹棠,雖然年紀不大,卻頗有名氣。大約是怕他把持不住自己,給以后的道路招惹麻煩,胡耀邦便找劉紹棠談話,讓他趕緊結婚。這雖然與當時學習蘇聯、人們早婚早育的背景有關,但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對劉紹棠無微不至的關心。
進入北京大學之后,劉紹棠按部就班地學習“古代漢語”、“中國文學史”、“文藝學”等課程。教授這些課的都是這方面的權威學者,如楚辭研究專家游國恩、語言學家魏建功、文藝理論家楊晦等。劉紹棠一方面學習,一方面也不忘創作。北京大學圖書館環境很好,十分安靜,劉紹棠便常常到這里寫作,圖書館成了他的創作室。后來被認為是劉紹棠中篇小說代表作之一的《運河的槳聲》,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這樣的一心二用,使劉紹棠的創作不能十分舒心盡意。加之中文系所開課程,多是對舊有知識的梳理和對文藝理論的探究,這些,對一個創作者而言,有時并不能有直接的助益,而且還須為此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有些課程漸漸成了劉紹棠的負擔,可又難于擺脫。于是,他想到了退學。
退學,在當年談何容易!本來招生時就有中央下發文件,而且他所在的又是中國一流的北京大學。劉紹棠深知此事有很大困難,只好再次向胡耀邦求助,希望能將自己調出來,先到團中央過渡一下,以后再按原先制定的“五年計劃”逐步實行。
劉紹棠的退學請求,在北京大學引起很大反響。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楊晦堅決不同意,兩次把劉紹棠叫到家里進行勸說,還發了脾氣。這事后來鬧到高教部。當時的高教部長是馬敘倫,副部長是周建人和劉子載。他們剛開始也都不同意,最后由于胡耀邦從中協調,花了很大力氣,才得到劉子載副部長的簽字,允許劉紹棠離開北京大學,轉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后改名講習所)學習3年。北京大學愛惜好學生的傳統使他們對劉紹棠做了特殊處理:在教務處開出的退學證明書上,寫上了保留他回北京大學復學的權利的字樣,據說這是沒有先例的。
胡耀邦批評:“你……就是驕傲”
從北京大學退學后,劉紹棠只到文學講習所呆了很短時間。不久,主持講習所的作家丁玲等人被定為“反黨集團”,“講習所”便停止了正規化辦學。1955年10月,中國農村掀起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高潮。團中央響應號召,組織干部奔赴全國各省,幫助工作。為了讓劉紹棠能有到農村體驗生活的機會,胡耀邦就安排他擔任中南分團湖南工作組組長。
在湖南工作時,劉紹棠仍抽空寫小說。中篇小說《夏天》的幾個章節,就是在這里寫出來的。另一部最后未能出版、但令劉紹棠念念不忘的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也是根據當時參加農業合作化過程得來的素材創作完成的。
1956年3月,經康濯和秦兆陽兩位作家介紹,劉紹棠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會員。由于仰慕蘇聯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劉紹棠希望像肖洛霍夫那樣專寫自己的家鄉,用自己的作品,描繪出家鄉京東北運河農村20世紀的風貌,留下家鄉歷史、景觀、民俗和社會學的多彩畫卷。為此,在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之后,劉紹棠馬上堅決要求從事專業創作。經胡耀邦及團中央批準,他從1956年4月起開始專事創作,不拿工資,全靠稿酬生活。
劉紹棠堅決要求從事專業創作,并不是沒有經過認真考慮的。當時的稿酬較高,劉紹棠的幾本書又頗為暢銷,因而已有了相對可觀的收入。當時他的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也已準備出版,稿酬算下來可以有35000元。這筆錢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按劉紹棠的打算,拿出其中的5000元,在自己出生之地,蓋一座四合院,過蕭洛霍夫式的田園生活。再用10年時間,拿出多卷本的長篇小說。在這10年里,即使不發表和出版作品,僅靠這筆錢的利息,也可以衣食無虞。
但是事情總不如料想得那樣順當。劉紹棠從事專業創作后,回鄉掛了一個鄉黨委副書記之職,以便體驗生活。可是這個時期,文藝界顯露出許多問題。當時劉紹棠創作勢頭正順風揚帆,不免有些年輕氣盛。1956年春天,在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劉紹棠帶頭發言,對當時文藝界存在的問題發表了一通意見。這在今天看來很平常,可當時大會的一位負責人將此事告到了團中央。團中央的一位書記要處分劉紹棠,可胡耀邦不同意。這事鬧得很大,胡耀邦便把劉紹棠找去談話。他在肯定了劉紹棠一些觀點還不錯的同時,又批評他不應當在大會上折騰;還說這是延安時期“輕騎隊”的作風;同時批評劉紹棠不該口出狂言,攻擊文藝界領導。
劉紹棠當時剛剛20歲,頗有些氣盛。他認為胡耀邦聽到的一些情況反映,與事實有出入,便與他當面爭執起來。胡耀邦見劉紹棠這么不接受批評,也發起火來,這次談話最后不歡而散。但在臨走時,胡耀邦仍嚴厲地告訴劉紹棠:“今后你少參加那些活動,一年要讀1000萬字的書,向我匯報。”
可是,劉紹棠沒有聽進胡耀邦的勸告,1957年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5周年時,又發表了一些過激的言論,受到了當時文藝界的一些領導的嚴厲批判。“反右”斗爭開始后,年僅21歲的劉紹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反黨典型”,被戴上了三類右派分子帽子。
劉紹棠被判為“右派”之后,他正旺盛的創作勢頭被阻扼;就連他已經寫成的50萬字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也因而終于灰飛煙滅。這的確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就在這樣的非常時候,胡耀邦又找來劉紹棠,對他的作為予以了教正;對他的未來,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
劉紹棠后來回憶,到了機關一個小會客室后,胡耀邦立即從沙發上站起來,和他緊緊握手,神情慈愛而又憂慮;接著突如其來地問道:“劉紹棠,有沒有自殺呀?”
劉紹棠一愣,很快并斷然一搖頭:“沒有!”
胡耀邦追問:“有沒有想過自殺呀!”
“沒有!”劉紹棠仍然搖頭。
到了晚年,劉紹棠才在一部書的題記里這樣寫道:“當時主持‘反右斗爭的一位領導人,在一次講話中說要將‘右派分子殺一批、關一大批。我自知難逃監獄、刑場這一關,曾經準備自殺,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下。1958年3月受到處理,胡耀邦問我可曾有過自殺的念頭,我沒有說實話。這是因為,已經傳達和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對于‘右派分子一個不殺,基本不抓。那個時候,共產黨員不管是何原因,自殺就是叛黨。我雖已被開除黨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為是共產黨員,也就以曾有自殺的念頭為羞恥。”
胡耀邦聽到劉紹棠的表白之后,打了個手勢,叫他坐到自己身邊,把茶幾上的香煙推給他。
接下來,胡耀邦臉沉下來:“劉紹棠,你知道你為什么犯錯誤嗎?”
劉紹棠低下頭,把人們批判他的一些話,拉出來作為回答:“我……一本書主義……墮入個人主義的萬惡之淵……大反社會主義……”
胡耀邦一揮手打斷他的話:“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驕傲!”
劉紹棠一聽,不禁愕然,“驕傲”?“大反社會主義”這樣嚴重的政治問題,在胡耀邦這里成了個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瞪著眼睛張大了嘴。
胡耀邦點了一支煙,態度平和了一些說:“你連我也看不起……不愛聽我的刺耳的話,喜歡聽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話。”
胡耀邦說的“連我也看不起”,是指劉紹棠1956年鬧全國青年創作會議的事。胡耀邦當時批評他,他不服氣并出言頂撞,鬧得不歡而散的那次。
但在口頭上,劉紹棠并不承認:“我沒有……沒有!”
胡耀邦神情很難過,長嘆了一口氣說:“去年春天大鳴大放,你如果跟我談一談,不會犯這個錯誤的。可是,你不請不來,請也不來。我的話不像某些人那么悅耳動聽啊!”
長久以來,胡耀邦一直關心劉紹棠的成長。1952年冬季,16歲的劉紹棠創作才華剛剛顯露,胡耀邦就親自找他談話。并在第一次見面時就約定,要劉紹棠每年找他談兩三次話。可劉紹棠年齡小,又忙著創作,加上對談話之類沒多大興趣,所以幾年中一次也沒主動找過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約他才去。這就是胡耀邦所說的“不請不來”。
“請也不來”,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個座談會上,談到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時,劉紹棠與當時文藝界的一位領導發生爭執。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劉紹棠談話。劉紹棠知道要挨“尅”,便找借口,編了個瞎話,就是不去。所以此時胡耀邦說他:請也不來。
這次胡耀邦與劉紹棠的談話大大超過了約定時間,致使工作人員幾次開門示意,胡耀邦只得結束這次談話。臨別時,胡耀邦爽朗地說:“劉紹棠,你還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給你3分鐘時間,趕快說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開除出黨,能不能……改為留黨察看兩年?”此時劉紹棠已被開除黨籍,說這話時已經泣不成聲。
胡耀邦站了起來,嚴正地說:“毛主席說了,對于黨內右派是揮淚斬馬謖,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給黨內右派的幾句話轉送給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為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你知道這幾句話的出處嗎?”
劉紹棠回答:“屈原的《離騷》。”
“會講嗎?”胡耀邦追問。劉紹棠沒有吭聲。
胡耀邦解釋說:“為什么過去的香花,現在變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別的原因啊,不好好進行思想改造的緣故喲!我的車趕緊原路而回吧,趁著誤入歧途還不遠。”
劉紹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趕緊點頭。走到會客室門口,胡耀邦緊緊握了一下劉紹棠的手,另一只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20年后還是一條好漢!”
最后這句話,劉紹棠記了20年。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國的冤案平反工作。劉紹棠給他寫信,他回信叫劉紹棠去談話。一見面便說: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驕傲。劉紹棠說起20年前的這句預言,胡耀邦仰起頭想了想,說:“我這個人愛說話,到處說話,說過就忘了。我跟你談過什么,早不記得了。不過,這句話肯定是我說的,只有我這個人那時才說這樣的話。”
友誼及情感的延續
劉紹棠被開除黨籍后,回家鄉勞動。在鄉親們的愛護下,有了更多、更豐富的人生體驗。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發表了他在60年代唯一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問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劉紹棠此時想找一份工作,便說想到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教寫作。胡耀邦馬上拿起電話,打給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請他予以幫助。經詢問后得知,當時的北京師范學院院長曾是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對胡耀邦是有求必應。劉紹棠便說定了到該學院教書。
可事不湊巧,劉紹棠的戶口遲遲轉不到北京,而國家的局勢卻發生了變化。為了渡過經濟困難時期,當時無論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團體……都在裁汰冗員,包括北京師范學院,也有很多人被裁下放支農。等到劉紹棠戶口轉到北京,不僅該學院院長調出,胡耀邦也到陜西省委當書記去了。幾種因素湊在一起,劉紹棠的戶口本上職業一欄,仍只能填上“無業”。好在當時管理并不嚴格,他還可以靠稿費維護生活。
當時,劉紹棠住在北京自己買的一所房子里,日子還算安寧。但1966年6月以后,北京及全國開始掀起“文化大革命”狂潮。劉紹棠此時不敢出門,他的家人告訴說,團中央樓臺示眾,胡耀邦被掛上大牌子,擰住胳臂,掐住脖子,抓住頭發,被恣意凌辱……連一個長期革命、忠誠黨的事業的領導,都被如此對待,劉紹棠一個“摘帽右派”,日子還能好過?這時,又是家鄉的親人接納了他。在家鄉,他避開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血雨腥風,逃脫了無休止的運動顛簸。在鄉親們的愛護下,還寫出了3部長篇小說。用劉紹棠后來的話:“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難——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
粉碎“四人幫”之后,劉紹棠在文學創作上恢復最快。在大部分作家才剛剛開始嘗試“傷痕文學”時,他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鄉土風情和鮮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學與傳統文化的脈絡,給讀者帶來了意外的驚喜。
1977年,胡耀邦重新恢復工作,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這顯然是個巨大的信號。急切的劉紹棠便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一方面匯報自己這20年來的生活和寫作情況,一方面對國家發生的變化感到歡欣鼓舞。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不到兩周時間,胡耀邦就給他回信了。信一開頭,就充分肯定了劉紹棠這些年來的表現:
“我完全不了解你這近二十年來的情況了。從來信看,你一直沒有向‘四人幫討乞求榮,一直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并且堅忍不拔,寫了幾部長篇小說,這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對于劉紹棠詢問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組織上將抱什么態度,胡耀邦先試著給予回答:
“我不清楚你寫得怎么樣,無非是三個情況:一是毒草,二是一般的東西,三是很好的香花。第一條我估計是不會的。但第二和第三都有可能。怎么鑒別是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呢?這不能靠組織扶持、介紹,而是靠廣大讀者去鑒定。”
“多少年來,不只是‘四人幫,‘四人幫以前的錯誤路線也是采取人為的(少數人)褒貶法,把毒草當香花,把香花當毒草,不都是破了產嗎?因此,你自己的東西,千萬不要請求什么名人吹捧、介紹,而是要請普通讀者、青年評定。如果評不上,就再加工,如果加工無望,索性重來。如果你決心要為后代留下一份或幾份革命的精神食糧,你就要決心奮斗下去,直到人們公認你是真正創作了這種有時代意義的精神食糧才算數。否則,都是靠不住的。”
1978年中秋節前夕,一輛黑色小轎車來到了劉紹棠生活的儒林村,這是胡耀邦派他的秘書來接劉紹棠前去做客。在西頤賓館附近的科技會堂,劉紹棠見到了等候多時的胡耀邦。劉紹棠只招呼一句:“耀邦同志,您好!”便忍不住流下了匯聚20多年未流出的滾滾熱淚。
這次久別重逢,兩人相互有許多的話說。胡耀邦首先告訴劉紹棠:中央在考慮為1957年反右中被錯劃為右派的同志平反,希望劉紹棠將自己的有關情況寫個材料報告上去。胡耀邦還回憶起劉紹棠第一本小說集《青枝綠葉》,連其中的幾個篇目都還記得。他們接續了20年前的那次談話,胡耀邦仍認為劉紹棠的問題不過是驕傲,并要求有關部門盡快解決他的問題。在胡耀邦的指示下,共青團中央于1979年1月,徹底改正了1957年將劉紹棠劃為右派的政治結論。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劉紹棠的小說創作進入了爆發期。全國多家報刊雜志不斷出現他的中篇乃至長篇小說,他要把耽誤了20年的歲月全補回來。由于他的創作實績,有關部門想調這位當時的“自由”作家,去從事文化行政工作。理由是,年齡適當(當時48歲);黨齡31年,在同輩人中算是很長的;大學學歷;這幾條頗符合當時“革命化,專業化,年輕化”標準。
可創作勢頭正旺的劉紹棠,更愿意在藝術領域有所作為,所以再三向有關部門婉謝。但在進行民意測驗時,他的票數又居于前列,因此組織上打算把他安排到文藝團體擔任領導工作。
創作和工作出現矛盾,劉紹棠又一次想到胡耀邦。他雖然知道時任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工作很忙,但事急顧不了許多,劉紹棠依然發出信函求助。
在給胡耀邦的信中,劉紹棠進行了數千字的自我解剖:認為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熱烈狂放;還不大會搞平衡,協調折中;缺乏組織才干和行政管理能力;還運用文學的夸張手法,如果當官,必然會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甚至誤國害己,絕沒有好下場。
為了完全打消組織部門可能的安排,劉紹棠還在信中向胡耀邦保證,要從1984年(48歲)到1996年(60歲),用12年的時間,一口氣連續寫出12部長篇小說。從這方面看,從政不如從文。胡耀邦是一個很通文化、知道如何讓一個人發揮才干的領導。他應允了劉紹棠的請求。
自此以后,劉紹棠便以全部精力,井噴一般地進行創作。盡管在當年的11月,他突發重病,險些猝死。但在病后的兩年多時間,他在遵照醫囑、盡量減少社會活動的情況下,仍然寫成了《豆棚瓜架雨如絲》、《這個年月》、《十步香草》、《柳敬亭說書》等4部長篇小說。1988年8月,劉紹棠因過于勞累,患中風,導致偏癱。但他以病殘之軀,仍奮力創作。在1995年,即距向胡耀邦保證的1996年提前一年,他已經完成了12部長篇小說的創作。
劉紹棠與胡耀邦之間,真正有著不解之緣。在劉紹棠成長的關鍵時段,總能獲得胡耀邦的支持和援手。從1952年,劉紹棠16歲時與胡耀邦第一次談話起,一直到胡耀邦的逝世,用胡耀邦夫人李昭對劉紹棠一個子女的話說“耀邦與紹棠之間的感情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