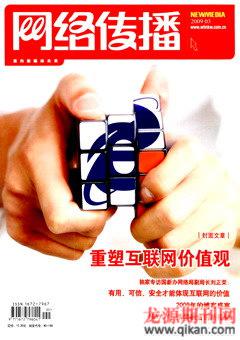從哲學視角審視網絡價值觀
田建平
價值觀,簡言之,即對事物價值的確立,亦即對事物價值的基本認識與語言表達。互聯網價值觀,即對網絡價值觀的確立,亦即對網絡價值的基本認識、基本理論與語言表達。
從網絡誕生那日起,人類就開始了對網絡價值的思考與探討。在網絡價值觀上,存在著兩種尖銳對立的觀點。一種是所謂“技術論”者,對網絡充滿了樂觀的情懷,認為全球網絡的建立是“人類學會取火以來最偉大的技術變革”,向世人許諾了一個虛構的烏托邦,認為網絡將削弱獨裁政府的統治,創造新的財富,提高少數派的地位并帶動社會變革。一種是所謂“災禍論”者,對網絡充滿了憂懼與悲觀的情懷。他們聲稱:網絡是一條非法的骯臟之所,其中充斥著罪犯和變態者。如果你的孩子登錄上去,他將受到色情作品的腐蝕和戀童癖的引誘。如果你下載某個軟件,病毒會吃掉你的硬盤。
顯然,無論是技術論者(樂觀派)還是災禍論者(悲觀派),都體現了人類對一種偉大的技術發明的復雜心理、理性訴求及文化上的終極關懷。但是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看,二者的觀點不免嚴重失之偏頗。技術論者興奮過度,把網絡想象成了上帝頭頂的“光環”,無視其負面效應及有害的一面;災禍論者悲傷過度,把網絡想象成了一只潘多拉匣子,大有末世將臨之感,無視網絡的正面效應及有益的一面。
網絡價值觀的8個哲學視角
哲學與文化需要的是冷靜與明智。只有當我們以客觀的心智去對待網絡這一“技術客體”時,也才有可能取得關于這一“技術客體”的本質認識。
初始闞值。計算機技術及其網絡的發明,本來是出于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貪婪攫取性”,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掘并利用勞動者的“潛能”,迫使勞動者在單位時間內完成最大量、最大值的工作之目的。假設離開了“初始”目的,離開了人們的使用,網絡不過是一堆“垃圾”而已。因此,人是第一位的,是根本的,是完全主動的。
工具與工具性。網絡是為了工作與生活,也許,較之人類前此的一切科技發明及工具發明來,現在網絡具有顯著的集中的普遍的強力的工具性。這一客觀的工具性更加強化了并且放大了人類的工具理性。同時。網絡也“培育”出了人類近乎“迷信”與“崇拜”一樣的“工具理性”。
技術值。網絡既是一種技術,更是一種技術化——技術之上的“技術”——技術之“形而上”的客體化事物。這種技術媒介之所以較之“單純”的媒介工具有著顯著的不同,就在于它提供了媒介“內存”的極大的豐富性、多樣性與似乎是無窮的可能性、中間性。因此,掌握了網絡的人才必然有可能在網絡世界實現其“黑暗”的各種可能。
語言。網絡語言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還是中和的以及間性的。事實上,較之古典時代意義上的“語言文字”,網絡語言尤其具有更大的彈性空間、不確定性、符號化、不規則性、非線性及延殖性——非程序性。網絡語言的這種特性稱之為它的“變異性”。但不論網絡語言如何“變異”,也逃不出人類既有語言文字這只如來佛的手掌。
異化。異化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自然本性的喪失或異變。在網絡環境中工作與生活將使人們遠離崇高的大自然,遠離客觀的原生態環境,遠離古典時代詩性的文化,造成普遍的生存“阻隔”,從而自覺抑或不自覺地“囚禁”于“人——機對話”的單一而又“狹窄”的“羊腸小道”上。現實中,不少青少年沉迷于網吧,徹夜不歸,其時已經“異化”為“網絡人”而非復“自己”。
潘多拉匣子。網絡的即時、速率、隱匿等特性使它成為了“發泄”基于人類“原欲”與“原罪”的“智能化”超級武器。例如,一位匿名者在網上污辱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一位副教授,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顯然,網絡這只“潘多拉匣子”傳播的并不都是樂觀派們揚言的“福音”,而是還有乾坤顛倒的、令人作嘔的斑斑“罪惡”。然而,佛經有云: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邪。以正抑邪,理應成為網絡媒介傳播中的永恒主題。
網絡自由。網絡自由正是基于網絡客體之“時空”性上的人的自由的展現。網絡為人類自由提供了似乎是無窮的“可能”。人類關于自由的潛意識、夢幻、欲望、精神、靈魂、文化、言論,凡此種種,都在網絡自由的時空中實現了其現在的“表達”。但是這種美好的“網絡自由”又引發了人們深刻的懼怕與擔憂。歸根結底,“網絡自由”實質上還是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受制于其時一般的社會物質狀況與文化狀況,因而只是一種相對有限的自由,而不可能成為絕對無限的自由。
虛擬現實。虛擬世界是真實與夢幻的混合體,是一個人自身“裂變”出來的世界,在“虛擬”的時空與語境中,人們的生存方式將變得簡單而單一,地球也將變得“狹窄”,而每當人們走出“虛擬現實”的“美滿姻緣”時,則往往會感到周圍客觀世界的陌生,甚至不知何去何從。作為傳播主體,不論是在客觀現實中,還是在“虛擬現實”中,人都不應“忘我”。
網絡文化。只有將網絡置于科學技術的語境及人類歷史與現實社會的語境中來考察,網絡文化才具有它的內涵及價值。網絡文化在其純技術層面、工具理性層面以及物質客體層面是既定的,它的豐富而獨特的文化內蘊則主要在于其“人化”(或主體性)上。網絡創造了文化,它本身也成為了文化。網絡文化是一種十分復雜的文化。
關于網絡之正面作用的論述和贊美之詞已經非常之多。例如德克霍夫使用了“共和國”、“環球村”、“全球意識”、“透明性”、“即時性”、“改變現代身份”、“技術假體”、“公共空間和公共領域”、“集體智能”等詞語來加以論述。
不論網絡媒介發展到何種地步,也無論是超越論者還是實證論者的論述,網絡媒介終究只是一種工具,潛伏于其背后的決定因素不外乎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以及民族國家的哲學習慣及文化治力。
在當今甚囂塵上的“全球化”(其實是西方化)浪潮中,網絡媒介扮演了“媒介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媒介“主角”。
網絡價值觀的科學重塑
鑒于網絡的雙重屬性(有利、有害)以及網絡世界存在的嚴重現實問題,必須樹立科學的網絡價值觀。
普及網絡科學知識,樹立科學的網絡價值觀。我們應充分利用互聯網,消除進步與發展中一切不良的、有害的現象,而不是利用互聯網去從事違法亂紀、傷風敗俗、危害他人及公共利益的行為。
以人為本,提高公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互聯網的使用者和技術更新者是人,網上信息的“操縱者”也是人。人的因素永遠是第一位的,是根本的,因此提高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是保障正確對待并使用網絡的根本之道。
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升公民道德水平。治理網絡低俗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要以胡錦濤總書記最近關于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的五項要求為指導,全力以赴地做好這項工作。
加強對網絡的監管力度,以法治網。大力加強對網絡的監管力度,以法治網。對于網上作奸犯科、違背公德的“害群之馬”應毫不手軟地繩之以法,嚴懲不貸,以儆效尤。
優化社會環境,創造健康的網絡外部空間。學習與借鑒中西方一切成功的治理經驗,引導人的正常發展,優化社會環境,創造促進人自身全面發展的良性公共空間才不失為解決網絡低俗化問題的萬全之策。
倡導網絡文明,提升公民的媒介素養。倡導網絡文明與提升公民的媒介素養二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網絡文明的進步與公民媒介素養的提高必將使網絡成為人類詩意的田園,促進人類社會向更高層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