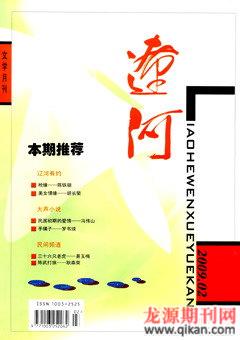站立成一棵大樹
暗 沙
一個飯盒
八十年代初,我就讀于鄉上一所中學,每日往返二十多里路,厚厚的黃上總是迫不及待地掩埋我們的足跡,似乎想恢復本來的沉重,可調皮的孩子們總也不能一步一步穩健前行,他們忽而向前沖去,忽而又返回到原地,打打鬧鬧中,破壞了一種秩序,使得習慣了安靜思考的哲學老人也不得不離開思想的領域,去欣賞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記載下這一段難忘的旅程。
那時,自行車在學生中算是很罕見的物件了,何況,我們都是貧窮人家的孩子,只能背負著貧窮的思想行走于屬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每天,村莊還在萬籟俱寂中,我們就踩著月影上路了,身后是笨重難看的書包,以及一個燒餅或者一個鋁制飯盒。提到飯盒,我總會記得一件事。那天,父親給我從城里買回一個保溫飯盒。這在農村是極少見的。我像以往一樣把這個飯盒擺在課桌上,課間,同學們圍攏過來,參觀這個新鮮事物,可不知道哪位男生,故意擁擠同學,我的飯盒掉在地上,摔碎了,里邊的飯菜倒了出來,還冒著熱氣,這可是入冬以來惟一的一頓冒著熱氣的飯菜。我哭了,這不光意味著中午得餓肚子,更重要的是摔碎了父親很久以來才積攢起來的,用以表達對女兒疼愛之情的禮物。我蹲下身子,一邊哭一邊整理地上的一片狼藉,可這時,耳畔卻傳來一陣竊笑,這笑聲終于把我徹底激怒了,丟下手里的東西,沖上去抓著那名高大的男生伸出了拳頭……
這也是我入學以來第一次打架,我自然不是那名男生的對手,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回家的路上,我書包后還掛著那個綠色的保溫飯盒,外表看著依然完整漂亮,但里邊已經是支離破碎了,就如同我此刻痛苦的心靈。我的眼淚還在不時地流下來,偶爾的一滴,也會飄落進黃土路,可它太微小了,馬上就會被揚起的塵埃覆蓋,根本尋找不到一絲可渲染的內容。我的腳步也是緩慢的,沉重的,這倒和夕陽的基色很相襯,只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天上的夕陽之大,地上的我之渺小,相互比照下,更顯示出我的孤獨來。
當快到村口時候,天已經完全地黑了。我感到一絲恐懼,不由向四周望去,萬物隱隱綽綽,因為失真,越發顯得猙獰。我又要哭了,這時,卻聽到遠處媽媽呼喚的聲音:“霞霞,霞霞……”一聲緊似一聲,我的心一下子輕松了,眼前豁然開朗起來,好像聲音之處就是太陽,我跌跌撞撞地沖了過去……
飯盒事件就這么成為我對童年記憶里的少數事件之一,那墨綠色的外殼緊緊箍住了我心靈的一角,而母親的呼喚聲就是那個角落里的一粒種子,在經過無數次的風雨,經過無數次的四季輪回后,最終茁壯成長為一棵大樹。
可這個成長的過程是多么的不易啊,每每憶起,還會淚雨滂沱,朦朧中,我總會看到一個小姑娘走在黑黢黢的夜色下,走在寂寞無人的山路上,走在蒼涼的土地上,走在風雨中……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段旅程啊,我不知道,只感覺四季的更替是那么絕情,那么殘忍,根本不容我的視線去適應。我總是行走在厚厚的黃土路上,抬頭是塵埃,低頭是黃土,而我只是黃土中的一名拓荒者,背負了一代人的理想和希望,因為有使命的存在,我只有學會成熟!
一條簡單的路
如果說童年行走的黃土路充滿了艱辛,那成長的旅程就是苦難的積累,最終誘發的結果,使得思想的外殼爬滿了青藤,始終牽著我的靈魂向上攀登、攀登……
我是這樣開始每一天的,六點起床,做早餐。七點送孩子上學,七點半上班,八點半準時到單位……一天的日程似乎沒有閑暇的時候,可無論時間再怎么擁擠,都不能制約思想火苗的燃燒。
每日的七點半到八點半是我思索的時空,通勤車成為我思索的搖籃。我的搖籃總是行駛于這樣一條簡單的路上:路的兩旁只有青山和土地。青山是真正的青,突兀的巖石也被周圍的植被染色,好似十八歲的小伙子剛剛長出了一層淡淡的胡須,使得原本潔白、光滑的肌膚變得青澀起來;土地是真正的桑田,貧瘠的沙土上總不能生長出茂密、碧綠的莊稼來,不是稠稀不均。就是綠中泛黃,給人營養不良的感覺。當然,對于這些景色,我早已熟稔于胸。因此,我不再探出頭去,只是在這個大搖籃里微閉雙眼,任思想的野馬馳騁于天地之間,不給予一絲的羈絆。在這個聯想的過程中,我想到簡單的旅途中,丟失了行李或遭遇了搶劫:想到了擁擠的街頭,我的雙腳失去了空間;想到了僻靜的山路上,依然有楓葉鋪出一條火紅的道路;想到平靜的湖水中被投入了石子;想到了蜿蜒起伏的山巒;想到了海域那邊的人家……脫韁的野馬赤裸裸地奔跑,只想尋求個自由和率真。
也因為這些無序的思索,使這條簡單的道路變得不簡單起來。路上的人物個個都被賦予了復雜的顏色,也因此絢麗多姿起來。
我看到一個個穿黃色馬甲的修路工,一年到頭,路面上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似乎在他們所能理解的概念里沒有了季節的區分,他們總是貓腰低頭,修整著那些不太平整的道路;我也看到莊稼地里的農民,在炎陽下播種,在秋風中收割,遮陽的草帽讓路人完全看不出他們的年齡,甚至性別;我還看到……看到什么了?還有哪類人呢?我睜大眼睛,四下逡巡,可視線里似乎沒有別的人了,難道這條路上只有這兩類人嗎?不,還有開飯館的、娛樂廳的、修理廠、電廠等等,和養路工、農民比起來,他們似乎算是“大人物”,可怎么就沒入我的視野呢?我沒有為這個疑問找尋答案,生怕過于求真的思維反而使我的主人公失真,便對這些“大人物”只是淡然一笑,就轉首繼續去了望自己看得見的這兩類人。不,還有一類,那就是如我般匆匆趕到郊區的上班一族,只不過我是閉著眼睛走人工作環境,而他們卻是睜著眼睛在干活,并極盡所能把丑陋雕琢成美麗。
相對于我的這兩類主人公,我的確是怯懦的,不敢睜大眼睛去生活,惟恐簡單生活背后不簡單的鋒芒灼傷了我的視線,灼傷了我的靈魂。我只能在這條簡單的路上,做不簡單的思索,然后把思索的結果加以整理,形成一個完整的東西,即便這個東西不能作為藝術品,不能被人們所欣賞。我仍然孜孜不倦。這種不知疲倦的碼字生活說藝術是在創作,說白了就是打著藝術的幌子在替自己吶喊,因為沒有膽量和勇氣身體力行地成為一名雕刻家,只好借助假象中的靈魂來完成一次次的雕刻。對于這樣的作品,究竟有幾個人去品讀,那似乎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而我卻知道,養路工、農民所鐫刻出的實物卻是人人都能讀懂的。
簡單的道路,被我一次次用思想的釘子破壞,卻又被我的主人公們一次次修補,這個破壞和修補的過程是怎樣的邏輯呢?我不知道,我只在這條簡單的路上,把思索的焦點集中到土地上,任季節的顏色把寂寥點燃,任思索的火花激揚出手下的文字,使生活的按部就班有了畫外音。我跟著這些音符去譜曲,把道路上零散如柳絮般飄飛的思想重新排列,便有了一首首完整的曲子。于是,“破壞和修補”終成為一個統一體。
我感謝這條簡單的道路,感謝這反反復復一小時的旅程,讓我的生命學會以鳳凰涅槃的姿態行走塵世間,永不消沉和懈怠!
站在陽光下
我想站在陽光下生活,而不是以坐、蹲或臥的姿態!我是對著一棵樹宣誓的,樹的背景是一片青灰色的天空,蒼茫而寂寥。
陜北的冬季也一樣是蒼茫而寂寥的,陽光發出蒼白的光芒,很直白地照在某個墻角,于是,那個地方就成了老農們的休閑場所,他們幾乎都是一個姿態,雙手插進袖管,蹲著、坐著,好像在等待一個宿命的結局。枯樹上有個鳥巢,這是惟一遮擋人視線的實物,心靈因此會有些許的悸動,證明自己還活著。穿過鳥巢望向太陽,陽光突然間變得特別刺眼,慘白慘白的,缺少溫暖。
山頂的這棵樹不高不矮、瘦骨伶仃,說不清是楊樹還是榆樹,但絕不是柏樹或柳樹,柏樹是萬古長青,柳樹是婀娜搖曳,他們的顏色和姿態很自然地否定了他們存在的位置。這棵樹木的枝丫向四方自由地伸展開來,但絲毫沒有影響周圍的空曠,反而周邊的空曠更顯示了樹木的孤寂。
為什么只有一棵樹木,而不是很多棵呢?我不禁疑惑起來。
植樹人自然不可能只種一棵樹,當他們種下許多株樹后,便把希望也播種進去,希望有朝一日,這里的山真正成為實質意義上的青山。可盼啊盼,樹苗一棵棵死去,他們希望的火苗也在一點點熄滅,直到有一天,他們發現山頂還存活了一棵樹的時候,終于懂得了什么叫“死灰復燃”,希望之火又開始熊熊燃燒,就因為這棵惟一的樹,這棵可以證明一個思想的樹。
我凝視著這棵樹,感覺有個很尖銳的東西刺痛了心靈,脅迫某種情緒醒來。我鄙夷地看著墻角懶散的肉體,看著只懂得享受溫暖,而不自己去點火的人們,終于放棄了試圖吶喊的聲音,把目光轉向了山巒。山巒起起伏伏,蜿蜒曲折,一直向遠方延伸。我突然想,如果把這些起伏勾勒出一條線的時候,是個什么軌跡呢?人生的旅途也總是坑坑洼洼,高一腳低一腳,或上或下,也把這些起伏勾勒出來,那會不會和山巒的起伏線重疊呢?
太陽似乎把自己完全地放逐了,正穩當地立于山頂,用溫和的目光打量眼前的樹,于是,那棵樹披了一層輕紗,神情雖淡淡漠漠的,卻少了幾分蕭瑟,多了幾分豁達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