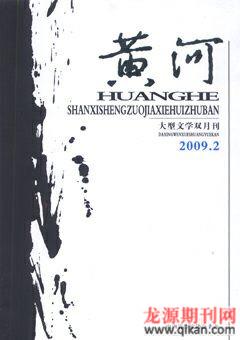本雅明《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的藝術(shù)作品》解讀
付一春
瓦爾特·本雅明出生于柏林一個(gè)富有的猶太商人家庭,高中畢業(yè)后進(jìn)入弗萊堡大學(xué)研習(xí)哲學(xué)。后又在慕尼黑、波恩、伯爾尼學(xué)習(xí),并以論文《德國(guó)浪漫主義的藝術(shù)批評(píng)觀》獲得博士學(xué)位。本雅明與當(dāng)時(shí)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布洛赫、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交往甚深并深受其影響。同時(shí),在前蘇聯(lián)導(dǎo)演及情人拉西斯的影響下,本雅明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及盧卡契的《歷史與階級(jí)意識(shí)》,并公開表示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名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積極為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社會(huì)研究雜志》撰稿,成為該學(xué)派事實(shí)上的重要成員。1933年迫于法西斯的迫害,逃亡到巴黎,1940年,本雅明不堪迫害在西班牙一個(gè)邊境小鎮(zhèn)自殺。
本雅明雖然生命短暫,但在哲學(xué)、文學(xué)、語言、藝術(shù)、歷史等領(lǐng)域都有不凡建樹,留下了一系列知名著作。《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的藝術(shù)作品》就是本雅明的代表作之一。以下就書中的一些關(guān)鍵詞語進(jìn)行解析。
一光韻
在《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的藝術(shù)作品》中,本雅明將“光韻”定義為:“(從時(shí)空角度所作的描述)在一定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近之物的獨(dú)一無二的顯現(xiàn)。”在本雅明看來,“光韻”具有兩個(gè)特點(diǎn):第一就是原真性和獨(dú)一無二性,第二就是膜拜價(jià)值和距離感。
首先,“原作的即時(shí)即地性組成了它的原真性。”也就是說,原真性就是藝術(shù)作品的獨(dú)一無二性。同時(shí),正如本雅明在書中所說,“即使在最完美的藝術(shù)復(fù)制品中也會(huì)缺少一種成分:藝術(shù)品的,即它在問世地點(diǎn)的獨(dú)一無二性”。藝術(shù)品由于具有的唯一的獨(dú)一無二的的特性,所以才形成了“膜拜價(jià)值”。本雅明認(rèn)為年代久遠(yuǎn)的藝術(shù)品之所以彌足珍貴,不僅在于其本身的藝術(shù)價(jià)值和其創(chuàng)作者的名望,最重要的還在于其歷史性,也就是指它距離當(dāng)代的時(shí)間差距。如古代的一件銅器,它的價(jià)值不僅在于鑄造者的聲望,材質(zhì)的優(yōu)劣,更重要的是它從古代延續(xù)到當(dāng)代的歷史過程。而任何一個(gè)仿制品由于缺乏藝術(shù)真品所獨(dú)具的“即時(shí)即地性”,因此并不具有原真性,更不具有膜拜價(jià)值。
正是這種歷史性的存在,具有“膜拜價(jià)值”的藝術(shù)品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不可接近”的烙印,而恰恰由于這種“不可接近”性使人們對(duì)其產(chǎn)生了神秘感和崇敬的心情。本雅明認(rèn)為在現(xiàn)代社會(huì),“光韻”的消失主要是因?yàn)椴豢山咏缘钠茐摹@纾环嫛⒁蛔嚯x很遠(yuǎn)的山,當(dāng)人們?cè)谟^望它時(shí),其距離產(chǎn)生的“不可接近”性會(huì)使人們?cè)谛睦砩袭a(chǎn)生一種崇敬感,同時(shí)這種崇敬心理也會(huì)促使人們產(chǎn)生突破距離,接近它、真實(shí)感受它的欲望。藝術(shù)作品的復(fù)制品就是這種心理作用下的市場(chǎng)產(chǎn)物。它的產(chǎn)生縮短了人和藝術(shù)品的距離。觀賞《蒙娜麗莎》不再局限在法國(guó)盧浮宮里,當(dāng)復(fù)制品出現(xiàn)之后,每一個(gè)人都可以擁有《蒙娜麗莎》,每一個(gè)家庭都可以懸掛《蒙娜麗莎》。但是只有真品才具有光韻,具有膜拜價(jià)值。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下的《蒙娜麗莎》仿制品,固然有著一樣的笑容,但是他所擁有的只是藝術(shù)品的展示價(jià)值。
二機(jī)械復(fù)制
本雅明認(rèn)為復(fù)制與技術(shù)復(fù)制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如木刻、蝕刻這類我們通常稱之為手工復(fù)制的復(fù)制技術(shù)因其在傳播領(lǐng)域的有限性,并不足以對(duì)藝術(shù)品的“光韻”構(gòu)成威脅。只有當(dāng)技術(shù)復(fù)制所帶來的數(shù)量的劇增、批量生產(chǎn)的出現(xiàn)才對(duì)藝術(shù)品的“光韻”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并最終導(dǎo)致其消逝。攝影、照相就是技術(shù)復(fù)制的代表。技術(shù)復(fù)制有兩個(gè)特點(diǎn)是手工復(fù)制所無法企及的:
一是技術(shù)復(fù)制更為細(xì)致。攝影技術(shù)可以捕捉到很多肉眼所無法關(guān)注到的細(xì)節(jié)。同時(shí),攝影可以從不同角度進(jìn)行拍攝,最終帶來的是更為全面、震撼的效果。例如早期人們用于記錄勞動(dòng)、祭祀場(chǎng)景使用的雕刻、繪畫,這些早期藝術(shù)作品的雛形很難細(xì)致地描繪出當(dāng)時(shí)的勞動(dòng)情形。在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其生產(chǎn)力遠(yuǎn)低于現(xiàn)在的平均生產(chǎn)水平,可以說只與原始人類時(shí)期生產(chǎn)力形似。現(xiàn)代的攝影技術(shù)細(xì)致地記錄了他們的生產(chǎn)生活場(chǎng)景,人們可以通過這些翔實(shí)的記錄了解原生態(tài)的生活環(huán)境、勞動(dòng)水平,同時(shí)還有利于對(duì)原始部落文化、風(fēng)俗進(jìn)行研究。
二是“技術(shù)復(fù)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帶到原作本身無法達(dá)到的境界”。藝術(shù)復(fù)制品的出現(xiàn)使得觀眾可以在任意的時(shí)間、地點(diǎn)、環(huán)境欣賞到藝術(shù)作品。藝術(shù)不再是只供少數(shù)人欣賞的陽春白雪,而成為老少皆宜的大眾文化。可以說技術(shù)復(fù)制使得藝術(shù)更大眾化、普及化。當(dāng)然,伴隨著藝術(shù)品普及化的同時(shí),藝術(shù)品的“光韻”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破壞。
三電影與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差別
為了更好地?cái)⑹鰝鹘y(tǒng)藝術(shù)與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區(qū)別,本雅明以電影與戲劇、繪畫為例進(jìn)行了比較。
電影演員和戲劇演員不同。戲劇演員面對(duì)觀眾表演,在表演中演員與觀眾形成一種互動(dòng),演員可以根據(jù)觀眾的反映對(duì)自己的表演做出適時(shí)的調(diào)整。但是電影不同,電影演員是面對(duì)著機(jī)械進(jìn)行表演,他與觀眾并不存在直接的交流,觀眾在觀看電影時(shí)缺乏一種與演員進(jìn)行溝通的氛圍。但是即使如此,戲劇仍然受到了電影的極大沖擊。
為了達(dá)到作品的效果,電影在制作后期通過采用蒙太奇技術(shù)手法,將冗長(zhǎng)的、不能烘托主題的片段刪除,剩余的片段聯(lián)系在一起,達(dá)到震撼的效果。同時(shí),這也使得電影的主題更簡(jiǎn)潔,更生動(dòng)地展示在觀眾面前。電影固然沒有戲劇所具有的“獨(dú)一無二”、“本真性”的特點(diǎn),但是電影仍然具有“唯一性”和“藝術(shù)真實(shí)性”。電影經(jīng)過選材、編排、取景、拍攝、后期合成制作等程序完成,然后通過機(jī)械復(fù)制手段復(fù)制出無數(shù)的作品。
在闡述電影與繪畫的區(qū)別時(shí),本雅明以巫醫(yī)與外科醫(yī)生為例說明畫家與攝影師的區(qū)別在于:畫家與對(duì)象保持著天然距離——正如巫醫(yī)一樣,雖然雙手的觸摸可以減小距離,但是作為巫醫(yī)的特性又夸大了這種距離——而恰恰又是這種距離使得畫家可以獨(dú)立于對(duì)象之外,創(chuàng)造出完整的藝術(shù)形象。而電影攝影師則“深深沉入到給定物的組織之中”,如外科醫(yī)生一般,雙手深入病人內(nèi)部,縮小了距離,同時(shí),由于謹(jǐn)慎性又使得這種距離有所拉近。如果說繪畫是一個(gè)整體的形象,那么電影攝影師鏡頭下的形象“則是一個(gè)分解成許多部分的形象”。
除此之外,本雅明在書中的最后提到了戰(zhàn)爭(zhēng)美學(xué),這一點(diǎn)反映了其政治功利性。讓我們聯(lián)系《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的藝術(shù)品》的寫作背景來看一下,本書著于法西斯橫行的年代。狂熱的法西斯分子鼓吹“戰(zhàn)爭(zhēng)是美的”、“政治審美化”的觀點(diǎn)和把“大眾獲得表達(dá)視為其福祉”的論調(diào)。針對(duì)法西斯的反人類觀,本雅明提出用“藝術(shù)政治化”來反抗法西斯。這里,“藝術(shù)政治化”就是要求革命者們用藝術(shù)作為手段,有力地與法西斯進(jìn)行斗爭(zhē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