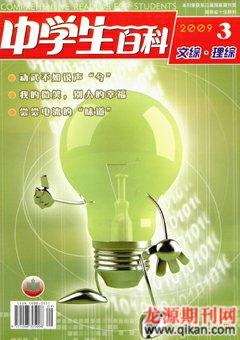道德原則是絕對的
石 勇
我們好像都喜歡評判某種事情或某個人的行為:“這是對的”“那是錯的”。比如,當某個人在大街上看到一個大人在打一個小孩子時,除非他是一個道德上的白癡,他的第一感覺肯定是“這是不對的”。個別道德感強的人甚至會認為,“一個大人絕對不可以暴力虐待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無論是出于什么理由”。
“這是對的”、“那是錯的”這樣的語句,常常表示一個道德判斷。比如,不管暴力虐待一個小孩子多么有利于社會,這樣做都是在道德上不能允許的,因為,即使這個小孩子有錯,也只能對他進行批評教育,暴力虐待在道德上是應該排除的。
顯而易見,當我們遇到那些可以讓我們作出道德判斷的事情或行為而說它是對或錯時,通常是這樣做的,我們認同于一種道德原則,然后,當我們看到有某種事情或行為在我們的理解下符合或違反這種道德原則的時候,便說它是對的或錯的。舉個簡單的例子,在我們的觀念中,我們認同“人不可以忘恩負義”,當一個人的行為在我們看來屬于忘恩負義時,我們便在道德上唾棄他或譴責他。
既然“對”、“錯”的道德標準是獨立于事情或行為,并用來判斷、規范事情或行為的,我們自然不會認為,當一個人在相同的情境下做了某件事情時,他是對的,而另一個人在相同的情境下做了同樣的事情,他是錯的;或者,當一個人在某個情境中應該做某件事情時,另一個人在相同或類似的情境中卻不應該這樣做。相反,我們認為,類似于“人不可以忘恩負義”這樣的道德原則是如此的不可違反,以致任何人在相同的情境下都應該這樣做。同樣,“人不可以見死不救”的道德力量,對于我們內心的召喚是如此強大,以致任何一個人,在他有能力的前提下,看到任何一個人落水都應施以援手。見死不救是應該承受道德譴責的,有時候甚至還要承擔法律責任。
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思維方式中,道德判斷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普遍施用于所有處于相同或類似情境的事情或行為。同時,道德標準或道德原則是客觀存在的,不是哪一個人主觀上的產物,也不是哪一個社會,哪一種文化刻意這樣認為或特有的。一種“你應該這樣做”或“你不應該這樣做”的“道德命令”是普遍有效的,不因你是中國人,他是美國人而有所改變。
但我們很快就遇到了一個麻煩。有人或許會反駁我們:既然你認為道德原則是普遍的客觀的,道德原則獨立于特定的文化或社會傳統,為什么有的社會(比如伊斯蘭教國家)認為用石頭打死通奸的婦女不僅在道德上沒有錯,反而是他們的道德原則,而有的社會(比如西方國家、中國)卻認為這在道德上是不可以容忍的,這是犯罪行為?如果認為道德原則是普遍的,那又如何解釋在文化的差異下,有這兩種相互沖突的道德原則?而如果道德原則是客觀的,又有什么理由證明一種道德原則就是對的,而另一種就是錯的呢?
類似這種反駁所觀察到的現象,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了。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他的《歷史學》中曾講了一個故事:古波斯國曾有一個國王叫大流士,他很喜歡到處旅行。在旅行中,他看到各地人們的傳統、習慣、文化等都不一樣,非常好奇。比如,他驚奇地發現,卡拉蒂安人(印第安的一個部落)習慣吃他們死去的父親的遺體,而且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希臘人認為對死者進行火葬才是正確的。于是,在某一天,他叫了一些宮廷里面的希臘人,問他們是否會吃他們父親的遺體。希臘人非常震驚,連說這種事情他們無論如何都干不出來。然后,大流士再把一些卡拉蒂安人叫進來,問如果叫他們火化自己父親的遺體,他們會怎樣。卡拉蒂安人也大驚失色,說這種事情太可怕了,以后最好不要提起。
看起來,卡拉蒂安人和希臘人的道德原則相差如此之大,以致在一方看來很正常的東西,在另一方看來非常可惡。多少年來,社會科學家們一再提醒人們,每個社會的文化、道德規范都不一樣,所以,似乎是不存在一個客觀的道德標準的。于是,有的人就認為,在這個世界上,由于每個社會、每種文化存在著差異,人們有不同的道德觀點和道德原則,因此道德是相對的。不存在一個普遍而客觀的道德標準,相反,是你有你的道德標準,而我有我的道德標準,我們誰也不能說,你就是對的而我就是錯的。
這種觀點在這方面肯定是有正面意義的,但是,這種觀點也是危險的,如果沒有一個普遍而客觀的道德標準,我們如何譴責一個人傷害他人?這樣,我們恐怕也不能說,法西斯德國屠殺猶太人、日寇的南京大屠殺是錯的了,因為盡管在我們看來這是最野蠻的獸行,但在他們看來卻沒什么不對。
更重要的是,這種認為道德具有相對性的觀點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希臘人認為吃父親的遺體不可思議,而卡拉蒂安人認為火化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有一點他們無疑是相同的,即都要對死者表示尊重。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是共有“尊重死者”這個道德原則的,只是表示這種尊重的方式不一樣。他們之間并非道德標準的不同,而是用以表示這種道德判斷的方式不同。就像“同意”,中國人是用點頭,但阿爾巴尼亞、印度等國家卻用搖頭表示。
道德原則是一種“絕對命令”。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是沒有含糊的。但是,如何去做應該做的,以及如何不去做應該不去做的,卻不一樣。這就要求人們一方面要多理解和寬容對方,另一方面也要堅持道德原則。編輯/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