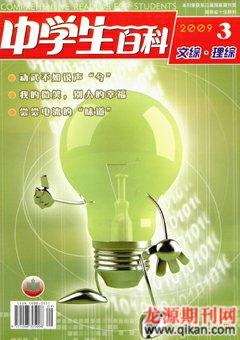人造連理枝
湘水落墨
白居易在《長恨歌》里留下名句:“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這其中的連理枝,指的是自然界中樹木的一種合生現象,即兩棵樹的樹干在相互發生摩擦而損傷,自然愈合后聯結生長在一起。連理枝在愛情上的貢獻盡人皆知,那就是給予了我們許多美好想象與向往。而在科學領域,連理枝的“巨大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尤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啟發人類發明了嫁接技術。
在雜交育種、轉基因育種等現代育種技術出現之前,嫁接一直是最神奇的育種方式。我國是全世界公認的最早發明嫁接技術的國家。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秦時代。現在,在追溯嫁接術的起源時,科學家一般都認為,同白居易寫下“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千古名句一樣,嫁接術也是人們對自然界的連理枝的“有感而發”。而嫁接術的出現,也讓連理枝進入“人造時代”。
人類最早對嫁接技術的使用,并不像現在這樣,有著抗病、增產等諸多方面的高要求,他們可能僅僅是為了吃上更為可口的水果。實際上,嫁接技術真正“取悅于民”,正是從果樹開始的。通過反復摸索,人們利用嫁接改進后的果樹,往往能夠結出味道更好的果實,這讓培植者嘗到了甜頭,也讓嫁接成為一門“農學技術”。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一書中就專門講到了嫁接梨樹的具體方法。
嫁接術在果樹身上的優異表現,也催生了一些有趣的夢想,培植“百果樹”即為其一。種一棵果樹,然后把其他品種或者種類的果樹嫁接上去,想吃什么摘什么,那該多好。名副其實的“百果樹”在一本小孩子讀的童話書里出現過,是一只小猴子種的。在現實中,“百果樹”的夢想仍然在路上。
浙江杭州一個七旬老漢便是尋夢者之一,他有一棵果樹能結6個品種的果實。日本福岡一個叫福島學的老農則技高一籌,他花了15年時間,讓一棵30歲的檸檬樹結出了11種不同的柑橘類水果。當然,作為執著的尋夢者,老農福島學一點也不滿足于現在的成就,他還想繼續往上嫁接新品種,培育一棵真正的“百果樹”。雖然,他離這個夢想似乎還有點兒遠。
果樹不是人類在嫁接技術上實現“以一敵百”的最好載體,而類似的夢想蔓延到菊花上就顯得現實得多。拿菊花來玩轉嫁接技術,幾乎可以說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最常見的是“塔菊”,即用植株高大、莖稈粗壯、生長迅速的黃蒿作砧木,在其側枝枝頭上采用切接或劈接法嫁接上大菊系菊花的枝梢,從而培育塔狀菊花。“塔菊”是經典的“菊花拼盆”,與“插花”的最大區別在于,它是植物活體,不是多個,而是一個。
也許有人會說,“塔菊”神奇還不是因為有黃蒿幫襯。其實,就算直接選擇菊花作為嫁接母體,奇跡也同樣可以被創造。在2007年的中國菊花展覽會上,有一株大立菊紅透了半邊天。在一株菊花母株上,開滿了各式各樣的菊花,姹紫嫣紅、爭奇斗艷。最后數出來的結果是,這株嫁接大立菊開出了547朵花,而這些花分屬513個品種菊花。于是,這株被稱為“史上最牛菊花”的大立菊,毫無懸念地“開進”了吉尼斯世界紀錄。
嫁接術在花卉上的應用,給我們創造了令人驚嘆的視覺大餐。而當嫁接技術走向田間地里,則給我們創造了更大實惠。現在一般認為,最早把嫁接應用到蔬菜生產中的國家是日本。實際上,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學會培育“大葫蘆”了。葫蘆在我國的種植歷史非常悠久, 700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很多遙遠的傳說中的男神仙腰間老喜歡掛個酒葫蘆,這其實是有“生活原型”的。
在以前,葫蘆除了被人們當做蔬菜用來吃,還用它用制造日用器皿,用來裝酒、舀水、盛東西。不論是吃還是用,大一點總不是什么壞事,于是古人開始想種出“大葫蘆”。通過不斷摸索,他們如愿以償地找到了方法。把10顆或者更多的葫蘆種子種在一塊,等它們長成苗后,用東西把根莖捆綁在一起,再用泥封住。等它們“合為一體”后,再通過整枝,長成最強壯的枝條。這樣,結出來的葫蘆與普通的葫蘆相比,就要大很多。這也是嫁接的一種,我們現在稱之為靠接。
拿葫蘆做文章的嫁接術現在應用得十分廣泛,跟我們關系最為密切的就是嫁接西瓜了。自1939年開始,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人所吃的西瓜十有八九都是葫蘆西瓜。如今,我們已經很難吃到“原汁原味”的西瓜了,絕大多數西瓜都是嫁接的產物。最常用的母體,除了葫蘆,還有南瓜。以南瓜做母體的西瓜長得快、結得多,據說瓜苗可以長到四五十米,不過口味比“葫蘆西瓜”差很遠。
編輯/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