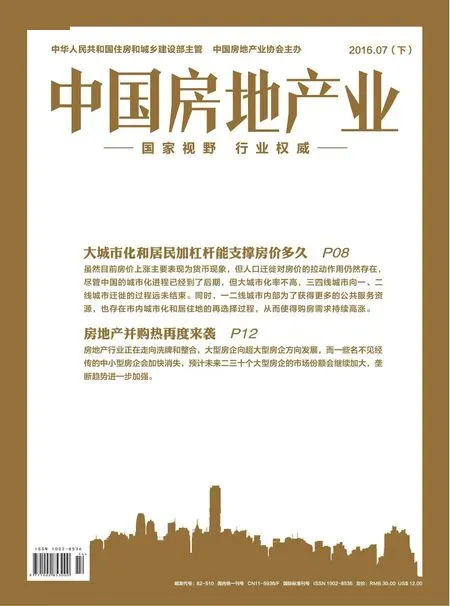淺析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
文/馬科 廈門海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福建廈門 361000
淺析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
文/馬科 廈門海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福建廈門 361000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使得我國房地產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再加上國家對于房地產業不斷加大監管力度,從而使房地產業已經逐漸遠離暴利時代,這就使得房地產企業必須真正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市場立足,而成本控制則是新形勢下房地產企業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手段之一。因此,本文對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進行了深入研究,目的在于更好的為房地產企業提供有益的理論和實踐參考。
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階段;成本控制
引言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使得我國房地產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再加上國家對于房地產業不斷加大監管和調控力度;并且,隨著2016年房地產去庫存新政的穩步實施,全國土地及房地產市場又呈現出一片火熱的景象,尤其是一、二線城市更是地王頻出。從而使房地產業已經逐漸遠離暴利時代,這就使得房地產企業必須真正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市場立足,而成本控制則是新形勢下房地產企業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手段之一。在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建設過程中,需要經歷項目決策、項目設計、項目實施、項目竣工交付和回訪保修等五個階段,而設計階段作為一個十分關鍵的決定性階段,在項目決策和項目施工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因此房地產企業能否對項目設計成本進行有效控制,已經成為關乎房地產項目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點。因此,本文對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進行了深入研究,目的在于更好的為房地產企業提供有益的理論和實踐參考。
一、房地產開發項目成本控制的概念
成本控制作為企業實現成本計劃的關鍵手段,主要包括對成本的
事前、事中以及事后控制。成本控制是以原先確定的目標成本為主要依據,對企業生產和銷售而產生的各種費用進行嚴格的監督和管理,從而達到降低企業成本、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根據成本控制的概念,我們可以將房地產成本控制定義為:主要針對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在保證滿足項目合同要求的前提條件下,對房地產開發項目整個實施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費用,通過科學合理的協調和控制來實現預期的成本控制目標,并且動態跟蹤以及時糾正偏差,從而盡可能的降低房地產開發成本費用的一種項目管理活動。應該說,房地產開發項目成本控制是一個復雜且長期的動態管理過程,涉及到的單位、部門、工作人員以及工作內容眾多,需要項目參建各方全員共同參與并綜合團隊智慧,才有可能真正達到實現房地產開發項目成本控制的目的。
二、設計階段對于房地產項目成本控制的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房地產企業加強成本風險控制
由于國家對于房地產業不斷加大調控力度,從而使房地產業已經逐漸遠離暴利時代,這就使得房地產企業面臨著土地成本不斷攀升、銀行貸款不斷收縮的不利局面,再加上房地產行業恰恰是一個高度依賴資金的行業,從而導致房地產行業的資金周轉日益困難。面對這一不利局面,房地產企業必須通過有效的項目成本控制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從而盡可能讓經濟效益最大化,進而不斷降低房地產企業自身的風險;而項目設計階段作為房地產開發項目成本控制的關鍵階段,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最大的控制效果,從而做到事半功倍。
(二)為房地產項目整體成本控制奠定基礎
在整個房地產項目實施過程中,各個不同階段都會產生相應的成本,關系緊密且內容復雜。根據相關數據統計表明:項目設計階級可以決定房地產項目后期75%左右的建造成本。可以說,設計階段在項目決策和項目施工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是項目整體成本控制的基礎和保障,房地產企業能否對項目設計成本進行有效控制,已經成為關乎房地產項目整體成本控制能否取得成功的重點環節。
(三)可以有效促進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競爭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使得我國房地產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這就使得房地產企業必須真正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市場立足,而成本控制則是新形勢下房地產企業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手段之一。因此,通過不斷加強項目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不僅有利于強化房地產企業的成本控制意識,而且可以改變當前企業的市場競爭觀念,從而更好的遏制行業的惡性競爭,進而有效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競爭,更能有效促進整個房地產業穩步、健康的發展。
三、房地產項目設計階段成本控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存在“重技術、輕經濟”的現象
目前,仍然有許多房地產企業在項目設計階段過于重視項目的技術問題,而對于項目設計的合理性和經濟性未引起足夠重視,從而導致房地產項目主要指標被過分提高,如鋼筋含量以及混凝土含量,從而使得建筑成本不斷提高。與此同時,由于現行的設計收費制度并沒有將項目設計的經濟性納入設計費用考核的范圍之內,從而導致設計人員對于設計過程中出現的浪費現象不需要承擔任何相關責任,這也使得部分設計單位及人員缺乏成本控制意識,加上設計保守,對安全系數考慮過大,從而使額外增加工程造價的設計現象時有發生。
(二)房地產項目限額設計沒有落到實處
目前,我國許多房地產企業已經開始逐漸推行限額設計,即根據項目設計任務書預先批準的投資估算開展初步設計,并且根據初步設計的總概算造價控制施工圖設計,然后再按施工圖的預算做出相應的決策。然而,由于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建設周期一般都較長,任何一個項目都會存在著不可預測的諸多風險因素,進而難免會發生工程設計變更的情況,從而導致工程成本難以得到有效控制。
(三)房地產項目設計招標制度不夠合理
我國已經逐漸將成本控制作為房地產項目設計招標制度的重要參考標準之一,然而由于設計方案評審不夠透明,意見和結果沒有完全公開,再加上仍然沒有一個詳細的可操作性的成本控制評價指標體系,從而使得設計招標的結果仍然嚴重依賴于評委的能力和道德水平,不僅難以保證設計方案的優化,而且也使設計概算成本指標失去應有的參考意義。
(四)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周期不夠合理
對于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而言,不僅需要確立一個合理的項目設計方案,而且還需要綜合考慮項目設計的經濟性和技術性之間的有機結合,這就需要對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階段的各個環節進行充分的論證和精準的比較,這樣才有可能獲得一個具備經濟合理性和技術先進性的項目設計方案,而這就需要具備足夠的設計時間作為基礎保障。然而,房地產企業出于資金時間成本及投資收益的考慮,加上各種主客觀因素,導致許多房地產開發企業將其視作為一種簡單的勞作型工作,一味的壓縮設計周期,只求速成而沒有給予充分的時間,從而導致設計質量和成本控制難以得到保障。
四、加強房地產項目設計階段成本控制的主要措施
(一)不斷完善設計招投標制度擇優選擇設計單位
應該重視并不斷完善房地產項目設計招投標制度,從中擇優選擇合適的設計單位以及設計方案,是做好房地產開發項目成本控制的第一步。為了不斷完善房地產項目設計招標制度,首先,房地產企業應對項目進行準確的定位,對其功能和投資提出明確的要求,并編制出完整規范的設計項目招標文件。其次,應建立健全設計招標評審指標體系,完善評價機制,以更好的保證設計招標工作的公平、公正。再次,在開始設計招標前應對意向投標單位的資質和信用等各方面開展相應的考察與資格審查工作。最后,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綜合分析各個投標單位的風格、工藝以及布局規劃、技術經濟性等綜合指標,從中選擇出有利于項目發展和銷售的最優設計方案;并應在中標之后應召集各個部門專業技術人員共同對中標方案進行優化,以期更好的提高設計方案的合理性和經濟性。
(二)提高項目設計單位及人員的經濟責任感
應該從思想上明確項目設計單位及工作人員不僅僅只需要負責設計方案的技術指標,同時也需要對設計方案的經濟指標負責。設計單位及工作人員應和成本控制人員密切合作,對設計的各個階段和環節開展成本對比分析,進行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評價,并且始終不渝的堅持經濟觀念,主動控制項目成本,從而實現優化設計的目標。與此同時,還應該適當引入項目設計優獎劣罰的激勵制度,并寫入設計合同條款;即如果設計單位及工作人員在項目投資限額內,在滿足合同的目標的前提之下對設計方案進行技術優化和經濟控制,從而達到節約成本的應該給予一定的獎勵,反之如果超出的則需要進行相應的處罰,從而強化項目設計單位及工作人員的經濟責任感。
(三)建立健全項目限額設計的管理體系
應該積極將限額設計落到實處,同時不斷建立健全項目限額設計的管理體系。首先,應將限額設計目標進行分解控制到各個專業,從而做到從初步設計到施工圖設計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嚴格準確的認證,進而依照最優原則選擇兼具經濟性和技術性的設計方案,真正確保設計預算控制在投資限額之內。其次,項目設計單位應不斷完善自我約束機制,將成本控制指標主動納入到項目設計成果的質量體系之中,并制定出科學的規范制度,從而更好的落實限額設計以達到控制項目成本的目的。最后,應在每一個建設環節的設計和選擇都應開展多種設計方案的對比和分析,從中選擇出技術先進且經濟合理的最佳設計方案。
(四)加強房地產項目設計交底與圖紙會審工作
房地產企業應該重視并加強項目設計交底與圖紙會審工作,盡可能將工程變更的發生控制在項目施工之前。應該邀請具備較高水平的專業審圖公司或工程技術、經濟專家,開展嚴格的圖紙會審工作,對施工圖紙技術上的合理性、成本上的經濟性以及施工上的可行性進行嚴格的審核,從各個專業角度對項目設計圖紙進行全面的會審,從而不斷提高設計質量,盡可能避免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而給項目施工帶來負面影響而造成經濟損失。同時,要求設計單位對其設計意圖、技術工藝難點、施工注意要點進行全面細致的交底,解除施工技術疑惑。
(五)嚴格控制房地產項目施工過程中的設計變更
在完成房地產項目設計圖紙會審工作之后,應該加強施工現場的配合工作,嚴格控制房地產項目施工的設計變更。雖然,在房地產項目施工過程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會導致突發情況較多,但仍然需要嚴格控制設計變更,建立健全起嚴格的設計變更審批審核制度,從而更好的保證投資限額不會被輕易突破。同時,應該要求設計人員全面細致的考慮每一個環節,并盡可能的進駐施工現場,根據施工現場情況不斷優化設計方案,進行設計工作的動態管理,從而盡最大限度的減少或降低設計變更的比例,使工程造價得以有效控制。
五、結語
成本控制是新形勢下房地產企業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手段之一。項目設計階段作為一個十分關鍵的決定性階段,在項目決策和項目施工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因此房地產企業能否在設計階段對項目成本進行有效控制,已經成為關乎房地產項目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點。應該說,房地產開發項目成本控制是一個復雜且長期的動態管理過程,涉及到的部門、工作人員以及工作內容眾多,需要全員共同參與并綜合團隊智慧,運用科學的方法不斷完善管理的措施和手段,才有可能最終實現房地產開發項目成本有效控制的目的。
[1]張斐.房地產項目開發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J].建筑設計管理,2009,(05):25-27.
[2]胡樹紅.淺析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J].建筑經濟,2011,(06):26-28.
[3]馬捷.房地產項目規劃設計階段成本控制[J].項目管理技術,2011,(06):26-28.
[4]張揚.設計階段成本控制提升房地產企業核心競爭力[J].經營管理者,2010,(06):84.
[5]王春波.房地產項目規劃設計過程中的成本控制問題[J].中國房地產,2012,(08):52-55.
[6]楊寶立.房地產項目設計階段的成本控制[J].建筑經濟,2011,(08):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