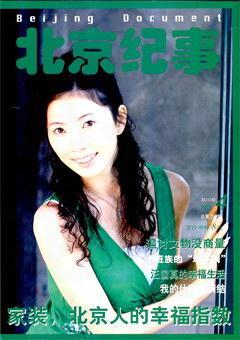唐龍疾書盡性情
康 康
一根禿頭筆、一張姜黃紙、一方“金不換”,起筆人生
聽不少人說過下鄉的事,免不了提日子苦,年紀輕,少有人像唐龍,痛快一句:“響應毛主席號召!”他充滿自豪感地將1969年8月31日銘記。那一年,他17歲,那一天,他到黑龍江省虎林縣珍寶島下鄉,成為建設兵團四師三十五團一連的一員。
在兵團10年,封封家書都是父親的毛筆字。最早讓唐龍拿起毛筆的就是他。
唐龍是根正苗紅的北京旗人,還是滿族八大姓氏之一“他塔喇”氏。自小住在西華門筒子河邊,后遷到西四小拐棒胡同。小時候的唐龍就聰明好動、四處結友。街坊四鄰都認得這個跑竄在幾條胡同踢足球的淘氣小子。他學說快板、吹笛子。晌午,站在胡同里不管誰家窗下,拿起笛子一通狂吹。能想象愣頭小子的專心致志,也能想象屋里人的無奈焦躁。
小唐龍在家也不閑著。他有整套的《水滸》《三國》連環面,這是用多少個幾分冰棍錢攢下來買的書。他把好好的橫格作業本扯了單片拿去臨摹書中人物,之后被父親發現挨打是常事,但這絲毫沒動搖他對畫畫的興趣。一天,父親看他又在畫,留下一句:“你沒事也寫寫字吧!”就這樣,唐龍用家里的小禿頭毛筆,裹副食的姜黃色包裝紙,加上當年一毛二分錢一個的奢侈品——“金不換”墨碇,寫起了毛筆字。
三拜師傅,喊一聲“老爹”。人在情誼在
唐龍是很戀舊的,經常提起曾在故宮當茶房但從未謀面的爺爺,他對爺爺穿著舊式朝服的印象都來自奶奶的描述,“連照片也沒留下。”是唐龍的惋惜。有人說,懂得戀舊的人才更懂得重情誼。用在唐龍身上是沒錯的。
1979年,唐龍完全可以回京就業,但他為了第一段感情留在了哈爾濱。
一直沒丟下書法的他,參加了黑龍江書法學院的學習課程。在這里,他認識了哈爾濱市書法家協會顧問、著名書法家王田老先生。“個不高,圓圓的臉,山東小老頭,說話耿直。”唐龍樂滋滋地形容第一次見老師的印象。
王老先生有一對子女,女兒常年體弱,兒子不在身邊。唐龍每周都去一趟老師家,屋里屋外的活兒他幫忙照應著,一入冬,冬儲大白菜全靠他了。就這樣,真心換來了王老先生的認可。
一天,唐龍認真地對老師說:“老師,您要是承認我,我就給您和師娘磕三個頭,成為您的正式弟子,從此師徒如父子。您坐好。”唐龍最敬佩水滸人物的義氣豪情,尊師重道是他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而此時,王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正式拜師后,唐龍從此改稱王田“老爹”。
結束了在哈爾濱十多年的生活,唐龍回到北京。2D03年,“老爹”到北京辦書法展,一行人吃住,唐龍全招待了。兒子盡孝道,他認為應該的。雖然現在“老爹”去世,但唐龍還一直和他的兒子保持來往,當年的三個頭,種下的是一生情誼。
書法、微雕數十載,成就仗義豪情
17歲的唐龍帶著他的快板、笛子和毛筆,開始了單調的下鄉生活。正經練字也從這會兒開始,但他說,談不上書法藝術,直到拜在王田老師門下。
跟隨王田的5年,唐龍從書法基本功學起。“你寫的這是什么字!”王田對唐龍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每當老師拍桌子大聲呵斥,唐龍都規規矩矩地聆聽教訓。漸漸地,他多練多看,汲取百家之長,融隸書、魏碑、漢簡等多種字體于一身。
也是從那時起,唐龍才認識到,書法,對自己性情的塑造和感情的抒發都有莫大的幫助。他一直謹記“做人要真誠厚道”的父教,“以德為鄰”是他的座右銘。
所謂十年磨一劍,唐龍在書法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幾年,形成了獨特的唐龍風格。
他的“蛇”字如同臥在宣紙上的一條草花蛇,形神兼備;“佛”字、“劍”字融合了生活化的理解,青煙繚繞、虔誠跪拜的景物人物形象躍然紙上,隨風舞劍的颯爽英姿讓一個“劍”字展現得淋漓盡致……他落筆看風雨,下刀如有神,字體拙中見巧,功力深厚。
除了書法,唐龍從1991年開始研究微雕。喜好鉆研的他用合金塊磨制獨一無二的雕刻工具,一塊塊原生的象牙,牛角凍、雞血石、白芙蓉、巴林石經過他280目、600目、1500目、2000目砂紙的層層打磨成為上好的微雕石料。微雕藝術“藝在微”,愈是細微,功夫愈精,價值也愈高;微雕也十分講究畫面和章法的藝術,這就是“意在精”。
唐龍憑借身、心、指尖的靈動統一,完全拋開顯微鏡,自如地在一元硬幣大小的石料上微雕絕句律詩。他仰慕毛澤東的胸襟,蘇軾的豪情,李白的壯闊,曹操的抱負,多少首激蕩人心的詩句被他精心雕刻。
微雕藝術家必須要有特別精熟的書法和國畫功底,雕刻的時候才可進行“意刻”。唐龍深得書法精髓,將書法藝術融入微雕創作之中,其筆畫雖細不可見,但卻深合書法中“筆端意聯,疏可走子,密不扦針”的境界。
如今的唐龍依舊仗義豪情,他的書法和微雕作品送給圈里圈外的許多朋友。演藝圈的唐杰忠,陳佩斯,王忠信……都曾是他的座上賓。唐龍還為北京市政協主席楊安江,宇航員費俊龍、聶海勝寫過藏頭詩。“安靜方延壽,江海展胸襟。”這是他送給楊安江的。力透紙背的字體融進了他的情誼,成為人們拜求的佳品。
編輯馮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