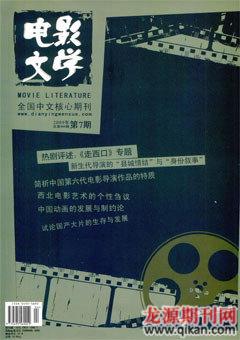《功夫熊貓》:東方文化的一種輕松圖解
黃曉軍
[摘要]本文由《功夫熊貓》引發的文化身份認同焦慮,探討了《功夫熊貓》的各種詮釋框架諸如:文化帝國主義、經濟掠奪、政治隱喻以及商業制作和思想啟迪。各種詮釋框架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造成了單一的視野,顯示出或抵觸或自我貶抑的文化身份認同焦慮。本文認為《功夫熊貓》體現出西方人超越單一視野,對東方文化內核的深刻了知,并輕松圖解。
[關鍵詞]《功夫熊貓》;詮釋框架,東方文化
夢工廠出品的《功夫熊貓》甫出,引來國人比較強烈的反應。尤其是成都5條院線發出了“關于影片《功夫熊貓》延期放映的公告”,決定在四川地區暫緩上映該影片(2008年6月21日《新聞晨報》《揚子晚報》)。此前又有首個發出公開抵制號召的行為藝術者趙半狄上書廣電總局,反對該影片的放映。在自稱為“熊貓人”的趙半狄的博客可以看到他抵制該片上映的相關博文。從很多博文題目不難看出博主用詞和感嘆號體現出的感情色彩,甚至夾雜對他人的辱罵。博主對該片的情緒,表現得比較極端。
當然,在國人的反應中,不乏理性的反思,比如:“‘洋熊貓引政協委員熱議,為什么不是我們拍的?”“《功夫熊貓》思考:為什么美國人能拍中國人不能?”在國人作出抵制和反思之前,《功夫熊貓》自然蘊涵著讓國人作出如此強烈反應的因素。一則,熊貓和功夫都是影片中的中國元素,二者的組合具有惡搞的嫌疑。二則,繼《花木蘭》之后,外國電影制片商又運用中國元素打造了大片向中國輸出。借中國的材料制作,又向中國輸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功夫熊貓》引發了文化身份認同的焦慮和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當一些對我們很有價值的東西處于危險時,焦慮就開始了。焦慮的功能在于,它能使我們面對自己,最終認識到并且挽救對我們最有價值的東西。同時,焦慮也使我們陷入自我價值中心的絕對化,失去對其他文化價值的感通。
《功夫熊貓》引發的文化身份認同的焦慮在于:中國文化符號(熊貓、功夫、針灸)被外國影片的運用使部分國人感到中國有價值的東西被他人歪曲和奪走的威脅,在國外強勢的電影文化的壓力下,我們正在偏離我們自己的文化特性,改變我們的文化形象,放棄我們的文化權利,以至于我們的文化群體的共存與發展處于危險之中,而此時,抵制放映等狹隘的民族主義情感可能產生共鳴。另一方面,追問“我們為什么拍不出”又表現出文化的自我貶損,產生文化挫敗感。抵制和反思都使我們陷入文化身份認同的焦慮。
文化身份焦慮的根本原因是對主體性和文化主體的過分看重,文化主體有助于呈現自我文化的價值,但總是表現為單一的文化視野,井隱含著排斥其他文化價值的看不見的暴力。面對同樣的一部《功夫熊貓》,國人的了解和外國人(包括此片的制造商)有不同的理解再正常不過,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各執一詞顯然無法達成交流,只有具備“互為主體性”的諒解,才有可能開展對話,才有可能發現所謂毹險和文化侵入,有可能只是一種臆想,是因為單一的視野局限將理解狹隘化。這種互為主體性的立場實際上是在文化的主體間性來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如果站在一方的角度來理解,如何達成這種主體間性的交流呢?這就是看到自己的立場,身在何處?比如說,我們在批評他人“壞”的時候,你是否看到了你的“好”的參照標準?如果看到這個“好”的標準,你能冷靜地思考,這個“好”就是絕對正確的嗎?如果你認識到“好”的這個標準并不具有真理性,只是因為自己的個性、習慣、出身而產生的標準,那么他人也同樣如此,相互之間就只能陷入交流的無奈。因此,關于《功夫熊貓》我們有各種評論,我們在各自的理由里執著地爭吵甚至喪失理智,其實,在我們議論《功夫熊貓》如何是一種文化侵略、經濟掠奪等問題之前,應該回頭看看自身的立場和出發點,自己對這個片子的詮釋框架。
1文化帝國主義
從文化帝國主義的詮釋框架來看《功夫熊貓》,有論者認為此片具有在東方外衣下的西方內核(《功夫熊貓》:東方外衣下的西方內核,片子里呈現的東方文化元素只不過是個噱頭,而商業化的手段是吸引大眾的根本核心。還有論者認為《功夫熊貓》展現的是美國式平民英雄的成長史,熊貓在片中被賦予了一個這樣的角色:家境平凡卻心比天高的后街少年。文化帝國主義的詮釋框架脫離不了西方人以自己為主的影子,在商業的外衣下傳輸自己的文化價值觀。
2經濟掠奪
這種詮釋框架認為國外影片的輸入存在著市場的占領和掠奪。有關議論甚少,因為從情理看,娛樂商業大片本來就有商業利益的訴求,夢工廠和迪斯尼并非慈善機構,只要是符合國家引進國外大片的相關政策規定,并非不可。國家引進大片的相關政策規定自然包含著國家利益的維護和國際交流開放多種價值的考量。
3政治隱喻
網上流傳的一篇帖子《功夫熊貓的國際政治隱喻》,在不同的博客或者論壇轉載(很多博客沒注明出處),在這篇文章中,每個角色都隱喻著相應的國家。烏龜隱喻美國,熊貓隱喻中國,黑豹太狼是日本,火狐是英法,小虎、螳螂、仙鶴等都是中國周邊的小國。《功夫熊貓》的故事則隱喻著以上國家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從詮釋學的角度看,各種解讀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過分的解讀似乎并不可取。
4商業制作
這個框架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功夫熊貓》的思想內涵,將之作為商業制作成功的范例,總結出該片的制作為國產動畫提供了哪些借鑒。如“《功夫熊貓》的四堂動畫電影課”,在題材、角色、技術、觀眾和檔期方面將之與國產動畫片比較,指出該片值得學習的地方。還有“《功夫熊貓》犯國產動畫片十大禁忌”,從反面批評國產動畫條條框框過多,缺乏想象力。
5思想啟迪
這種詮釋框架沒有以上角度那樣多少有點沉重,而是輕松地把《功夫熊貓》當作一種寓言,從中尋找這個片子帶給工作學習生活的啟發。如“《功夫熊貓》教育孩子七件事”,“功夫熊貓暗藏職場升位秘笈”,這些解釋將該片看成是一個類似思想庫的文本,依照個人的需要,以六經注我的方式從該文本中各取所需。這種視角最超脫,也最輕松,但是這種詮釋往往采用的是實用性的,而不是審美性的標準。
對于一部影片的詮釋框架,遠不止以上這幾種。正是從這樣的框架出發,對于《功夫熊貓》才會有不同的詮釋,實際上,每個人在看待同樣一部片子或者一件事一個人的時候,都必然從某種詮釋框架出發,不存在某個框架而發表觀點的似乎沒有,在這里指出發表觀點之前的框架或者前提,只是要我們認識到觀點發出是在某個框架下,就必然存在著局限,從而緩解面臨外來文化娛樂產品進入時,文化主體性意識加深產生的單一視野。福柯曾在《知識考古學》等著作中提到,對一切預設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把所謂天經地義、從來如此、理應如此的事物的秩序陌生化,重新審視現行社會規范,查找集中的缺陷、漏洞和非人性的東西。以上提到的框
架就是預設的前提,我們在從這些前提出發時可能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前提是否狹隘或者存在問題,一旦我們發出觀點,事實上已然肯定了前提當然的正確。這些前提從某種意義上也屬于思維定式或者刻板印象,容易產生將一個新出來的片子理所當然地歸入到曾經出現過的某一類片子當中,從而忽視了異質性。
此前,迪斯尼的《花木蘭》體現了西方人的某種東方想象。迪斯尼的《花木蘭》編劇藍本是中國北朝古詩《木蘭詩》,詩歌的重點內容是首尾兩部分,花木蘭既是巾幗英雄,又是溫柔淑女,但在迪斯尼的《花木蘭》中,卻按照西方人的理解打造成一個開放活潑的西部牛仔,中國傳統的單方面無條件付出的孝道被置換成熱愛父親和應有的責任感這種普適性的理念。《花木蘭》重點突出了從軍的經歷,從軍中的英勇行為動機是為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值得尊敬的人,整個片子表現了一個女性尋找自我的傳奇,個人價值的尋求演繹出愛和責任的主題。按照愛德華-薩義德在《東方學》中的思想,他者不過是自身的投影。迪斯尼的《花木蘭》中的中國元素不過是外衣,其內核則是西方的。片中的花木蘭是西化的花木蘭。但是,在Ⅸ功夫熊貓》中,似乎可以看到西方人在把握東方文化時的某種進展。且不說,片中對中國元素的運用嫻熟:將香港功夫片中的練功打斗橋段提煉組合,將武俠小說中的經典場景一一再現,將中國觀眾心中皆有、將中國國產動畫片中皆無的東西表現出來,可謂對中國片中的功夫研究頗深。
新浪和騰訊網都做了觀眾網上調查。騰訊的數據表明,觀眾的看點是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但其中功夫元素最為突出。而新浪的數據則表明動畫功夫喜劇三合一才是受關注的主要原因,兩個調查共同點就在于夢工廠的確對功夫元素的研究和運用下了點功夫。同時,從劇情上講,西方人在把握東方文化上不再純粹站在自己的詮釋框架上,而體現出深入中國文化內部去探求其精髓的傾向,這種探求的結果就是用動畫輕松地圖解東方文化的內涵。生活在社會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幾乎每個人在內心對一個外在于自己的人或物形成依賴,在片中,很多人都依賴“龍之典”這類秘芨類的東西,火狐師傅、熊貓、黑豹都是這樣,似乎有了這個秘芨就會天下無敵。豈料這個秘芨如同熊貓鴨子老爹的面條秘方,其實什么也沒有。另一方面,火狐師傅面對功夫基礎奇差的熊貓徒弟,他把精神寄托在烏龜那里。但是烏龜卻要火狐自己承擔,自己卻逍遙游。面對黑豹出獄帶來的危險。火狐和熊貓都把希望寄托在龍之典那里。卻發現那似乎是個玩笑。這個時候,當再也沒有任何可依靠的人(如烏龜)或物(龍之典)的時候,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火狐師傅要尋找出教熊貓的新方法,結果找到了,在吃飯中訓練了熊貓。熊貓不能有任何他人的指望,只有自己勇敢承擔成為龍斗士,結果果真夢想成真,一代大俠就是這樣煉成的。有論者認為,從《功夫熊貓》可看出外國對中國文化接納程度的改變,其所論站在中國大地震的背景下將之作為勵志片來看待這種接納,是一種經驗感覺。外國對中國文化接納程度到底如何,尚不能下定論,但是就外國對中國文化了解程度而言,筆者認為相對以前的《花木蘭》,則是大大加深了。此片已經探觸到東方文化中的佛教哲學,尤其是中國道家莊子的思想以及中國禪宗的思想內核。莊子的道家思想和中國禪宗思想有相通之處。莊子的逍遙游,是離卻一切相待或者條件,才能達致真正的自由,有所待則有束縛,自由則不能發揮。換句話說,靠無所靠,即得逍遙游。玩味《功夫熊貓》中火狐師傅和熊貓精神依靠的轉變,就能體會到外在的東西既是依靠,又是局限。對禪宗而言,則是殺活的方法,只有“死”透,才能大活。想依靠他人解除自己的問題,對禪宗而言,都是妄想,殺卻一切妄想,即死透,然后回光返照,問題是自己起的,只有自己才能滅掉。個人的潛能激發,置于死地而后生,則無往而不勝,這也就是大乘佛教講的真空妙有思想。《功夫熊貓》在輕松的笑料中圖解了這樣一種哲學,熊貓在劇情中大起大落的戲劇性強化了這種哲學寓言。越是具有戲劇性,越是在現實中缺乏可能性,就越是具備寓言性。之所以說是輕松圖解,是因為一種思想本身相當精微復雜,無法細致地體現,而作為引進大片有著很多利益訴求,兼之動畫本身體現的某種抽象的機械性。但總的來說,這種對于東方文化的圖解是比較到位的。
從《花木蘭》到《功夫熊貓》,如果被常見的詮釋框架限定,就很難發現這當中的變化,西方看待東方,以西方為主表現東方(實際上表現的是自己)到能研究東方,表現東方文化(表現得比較到位),的確值得我們回味。當然不能說,《功夫熊貓》體現的東方文化,已經拋棄了西方人的偏見,完全站在了東方人的立場上,事實上,《功夫熊貓》或多或少體現了對這種“無”的思想的某種揶揄。鴨子父親繼承的家產不過是祖上打麻將贏來的,鴨子父親“無”的秘方不過是一個騙局,鴨子父親最大的期望是子承父業。這些細節讓國人看了親切而可笑,外國人對中國家庭的理解或許如此,然而這些細節的集中卻體現了西方人在認識東方過程中的“本質主義”,將東方特質歸結為某種固定不變的東西。指望西方人不按照西方思維來看待東方是不可能,只能說,這種認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還是從《功夫熊貓》那里看到他人對我們輕松的理解,而我們在文化身份認同焦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生起的時候,是否能冷靜下來,反觀發表任何情感激烈的評論或者意見的預設前提,然后進一步對西方文化作深刻的了知,或者還能進一步加以到位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