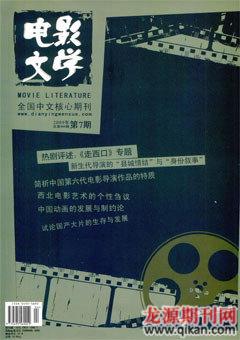一部生態預警小說
張冬梅
[摘要]《使女的故事》是當代“加拿大文學女皇”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所有小說中最流行的一部,1990年被改編成電影。在這部作品中,作家運用反面鳥托邦手法描繪了一個陷入重重危機的未來國家。本文旨在通過分析小說中再現的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三方面的危機,說明該小說實為一部生態預警小說,警示人們如果繼續征服、濫用自然,小說中想象的災難將成為現實。
[關鍵詞]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生態批評;生態預警小說
被譽為當代“加拿大文學女皇”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是一位有著深刻生態意識的女作家。她的很多詩歌、散文和小說都已成為當下生態批評學者關注的焦點。《使女的故事》(1985)是阿特伍德所有作品中最流行的一部,并為她贏得了第二次加拿大總督獎,1990年還被德國著名導演沃爾克·施隆多夫拍成電影,搬上了銀幕。自問世以來。小說的反面烏托邦文學手法一直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即小說是如何繼承并發展了赫胥黎和奧威爾的反面烏托邦文學傳統,然而其著眼點多為女性主義主題。本文通過分析小說中再現的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三方面的生態危機,試圖說明這部作品實為一部杰出的“生態預警小說”。
生態預警,又名“生態反烏托邦”,是生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著名生態批評家勞倫斯·布依爾在《環境的想象:棱羅、自然書寫和美國文化的構成》中稱生態預警性文學為“生態啟示錄文學”,并特別指出“預警性的啟示錄是當代生態文學的一個最有力的核心隱喻”。在布依爾看來,“生態環境面臨的最大威脅或許并不是如何遭到破壞,而是我們人類怎樣看待它,因為多數人仍然沒有接受生態危機已經相當嚴重的事實”。生態預警小說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創造生態災難的意象,想象恐怖的世界末日,對生態災難進行預警,“其根本目的是喚起人們對自然的關懷和對人類命運、前途的關注,激起他們的生態良知,使他們懂得保護自然生態與人類自身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小說以美國馬薩諸塞州為背景。在給該小說作注釋的一篇文章中,美國學者埃里克·多姆維爾提供了這樣的信息:20世紀末,美國發生了一系列生態災難,在加利福尼亞,沿圣安德列斯斷層不斷發生的地震引起了核電廠爆炸,其輻射物造成廣泛的破壞,其中有毒廢料和二氧芑使癌癥和不孕患者人數劇增。隨之,社會和政治上的動亂接踵而至,一批極端的基要主義分子通過暴力篡奪了政權,建立了專制的基列共和國。在這部小說中,阿特伍德以超凡的想象力,描繪了一個繼那次大的環境災難之后陷入重重危機的未來世界。
一、自然生態
在阿特伍德想象的基列國里,盡管扮演當權者代表人物的大主教們在竭力使。一切回歸自然”,荒野也已在這個高度“文明化”的國家徹底消失了。每個大主教家里的花園幾乎成了小說唯一呈現的。自然”。然而,這些花園顯然是人化自然,這里決不允許一棵雜草的出現,正如奧弗雷德所描述的,“這里看不到任何齒狀的蒲公英,草坪里的雜草被除得一干二凈”,一如基列國對人的嚴格、呆板的等級劃分,花園和街道都要絕對整齊。
在基列國,未被污染過的地方已經不存在了。核輻射、殺蟲劑、化學廢棄物等污染物充斥著各個角落,空氣中布滿化學物質,輻射線和放射物體,河水里充斥著有毒成分,各種有毒物質悄悄侵入人的體內,包括當權人物眼中唯一保持“自然”的女性身體,“在她們的脂肪細胞層里安營扎寨。天知道,恐怕從里到外都被污染了,骯臟得就像進了油的河灘,不管是濱鳥還是未出生的嬰孩,都必死無疑……”由此導致基列國的大多數人們喪失了生育能辦,從而也促發了嚴重的人口危機,非正常嬰兒的概率達到了四比一。
此外,各種有毒污染物以及人類的濫捕還導致許多動物都像鯨魚一樣遭到滅絕。其中,海洋漁業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如今,人們難得能吃到的魚都是從養魚場里捕撈的,吃起來盡是土腥味”,而整個沿海地區都處在“休漁”時期。小說中談及動物的文字暗示了動物遭受人類利用、虐待的狀態,奧弗雷德在其敘述中多次涉及這類內容。如,“人們為欄養豬發明了專門供它們玩耍的游戲球。那是一些彩色的大皮球,讓豬用蹄子踢來踢去。據豬肉經銷商反映,這一活動改善了豬的肌肉張力” “這段文字我是在《心理學入門》這本書上讀到的,另外還有關于籠中鼠的章節,它們為了找點事干,竟不惜電擊自己……”不難看出,動物在人類眼中僅僅是為人類謀福祉的工具,人和動物間不存在任何倫理。
二、社會生態
基列國表面看來處于一片死寂當中,偌大的國家卻“人跡罕見”“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其實不然,戰爭、暴力和犯罪,尤其是宗教沖突從未停止過。電視上經常報道戰況,同性戀者、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教友派信徒的尸體也經常可以見到。此外,阿特伍德還通過奧弗雷德的回憶再現了前基列國家的動蕩形勢:那時謀殺事件已成家常便飯,人人感到岌岌可危,女性更是長期生活在恐懼當中。
在通過武力奪取政權后,宗教基要主義分子建立了新的極權統治。他們遵照《圣經》中的父權原則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度。男人的權力在女人之上,另外男人和女人內部還有更仔細的劃分,如,男人分為:大主教、眼目、天使軍士兵、衛士等,女人則分為:夫人、馬大、經濟太太、嬤嬤、壞女人和使女等,且他們都有統一規定的服裝。
嚴重的人口危機使女性在基列國的處境最為悲慘,因為“在一個以生育能力為標準定義女性價值的男權社會中,如果女性喪失其生育能力,很可能會面對被放逐、被剝奪社會地位的危險”。基列國是一個極端的男權社會,剛剛上臺的當權人物所做的首要事情,就是將所有女性的銀行賬戶轉賬到她們的男性親屬名下,從而使其在經濟上依賴男性;婦女被趕回家中,負責照顧家人和花園,重新扮演起“家庭天使”的角色。那些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送到“感化中心”培訓,然后成為某個不育的大主教家庭的使女,專門為其生育子嗣。使女們被剝奪了所有的自由空間和權利,在當權者眼中,她們“只是長著兩條腿的子宮:圣潔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
而上了年紀的婦女、給了三次機會仍不能生育健康嬰兒的使女以及那些“壞女人”會被送到“隔離營”終結生命。在那里,她們終日都在清洗和焚燒戰場上下來的或貧民區里的尸體,或者“專門和有毒傾倒物和輻射泄漏物打交道。據說在那里不出三年鼻子就會脫落,皮膚會像橡皮手套一樣剝落下來”;那里的人“全是些被社會遺棄的人。當然她們全都不育。假如開始時不是這樣,到那里過上一段時間后必定如此。如果還不肯定,他們會在你身上動個小小的手術,那樣就能保證你不育”。在這個極端男權的社會中,女性完全淪為了失去話語的客體。
三、精神生態
環境的惡化、社會生態的失衡使基列國也陷入了精神困境。這個完全由基要主義分子控制的國家,允許信奉的只有《圣經》。他們從字面解讀《圣經》,相信里面所記
述的內容均來自上帝之口,是絕對正確的,并嚴厲禁止其他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們自認為這樣做是為了使“一切回歸自然”,所以他們得一切照《圣經》說的辦。
在《圣經·創世紀》中有使女比拉代替拉結為雅各生子的故事:拉結多年未能為丈夫雅各生出孩子,便說,。有我的使女比拉在這里,你可以與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子”(《圣經·創世紀》。第30章1-3節)。統治者仿效《圣經》中拉結和雅各的故事,強迫那些尚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成為“使女”,為不能生育的大主教家庭生育子嗣。那些本是用來傳播知識的學校也成了基列政權向使女傳播愚昧思想的“感化中心”。在那里每天都有嬤嬤為她們念《圣經》語錄,力圖讓其忘記自我,心甘情愿地成為生育機器。
統治者還用《圣經》中的名字命名人和物。如,男人按照各自在社會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被稱為“大主教”“眼目”“天使軍士兵”;不同階層的女人被細分為:“夫人”“馬大”“經濟太太。和。使女”等等。除了人,一些機構或商店的名字也源自《圣經》,如,對使女進行教化的感化中心被稱為“雅各與拉結中心”。面包店和肉店被稱為“眾生”、“田野中的百合”或。牛奶和蜂蜜”等。此外,使女見面時要用固定的寒暄語,一個說,“祈神保佑生養”,另一個得回答“愿主開恩賜予”。
在這個唯《圣經》是瞻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正常的愛也是嚴禁的。奧弗雷德曾感慨地說:“這里沒有我可以愛的人,所有我愛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身在異地。”愛的感覺,尤其是男女間的愛情是絕對不容許的。當大主教詢問奧弗雷德究竟他們這些統治者忽略了什么時,她的回答是“愛”,“哪一種愛?”大主教問,“戀愛”,她說。男女之間的性愛也被完全公式化了,因為它的存在只是為了生育。對此男人是厭惡的,大主教說:“(性)是輕易就能得到的東西。隨便什么人,只要用錢就能買到……男人們甚至開始對性失去興趣。對婚姻也興味索然”;而在女人的眼中,“男人是性機器……除此之外,別無他求。”
除了異性之愛,友誼或姐妹情誼也被禁止。他們鼓勵用女人統治女人,因為在當權者眼中,這樣做“是達到生育和其他目標的最好最劃算的辦法”,此外,基列國還令使女們彼此互相監督,“進城同樣必須兩人結伴同行,否則休想。據說是為了保護我們,……事實是,她監視我,我監視她”。
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運用反面烏托邦手法描繪了一個陷入重重生態危機的未來基列國,以此警示人們:如果人類繼續破壞自然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人類目前面臨的生態危機會繼續惡化下去,小說中想象的災難也將成為可怕的現實。然而,在預警的同時,作者并未讓讀者徹底絕望。在小說最后的“史料”部分,不難發現,人類這一物種在2195年幸存下來,所有參加基列研究專題研討會的人還被邀請參加“漫步自然”活動。正如生態批評家格萊塔·加爾德所說,“畢竟,只有在想象地球還有未來時,我們才可能去為它承擔責任”,阿特伍德在小說最后試圖告訴人們,只要人類增強環境保護意識,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挽救措施,人類依然有希望在地球上“詩意地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