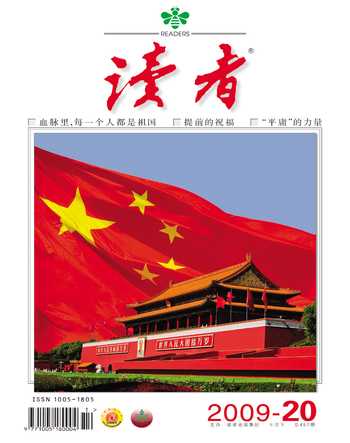加州的傳說
馬克·吐溫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到加州淘金,然而,我從來就沒有淘到足夠的金子讓自己富裕起來,不過,我卻發現了一處非常美麗的地方,叫“斯坦斯勞”。斯坦斯勞簡直就是人間仙境,這里群山蔥蘢,樹木茂盛,清風徐徐,松濤陣陣。
在我到達此地的很多年前,就已經有人來到了斯坦斯勞,他們也是來淘金。他們在山谷里建起了一座小鎮,這里有人行道、商店,還有學校。他們還修建了許多漂亮的小屋供自己居住。
起初,這些人在斯坦斯勞山區挖到了很多黃金,但他們的黃金運并沒有持續多久,幾年后,這里的黃金就被挖沒了。在我來到這里時,已是人去樓空了。
那是夏季的一天,當我走進這空曠的小鎮時,此時小鎮的人行道上長滿了荒草,那些漂亮的小屋也已經爬滿了野薔薇,昆蟲的鳴叫聲在空中飄蕩。然而,我很快就意識到,在這個小鎮里,我并非只身一人。
有一個人站在一座小屋前面微笑地看著我。小屋前面有一個漂亮精致的小花園,花園里開滿了各種鮮花。潔白的窗簾懸掛在窗戶上,在夏日的微風中輕擺。
這個人微笑著把門打開,讓我進去。我走進了小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和其他挖金的礦工住在粗陋的帳篷里,睡在堅硬的地上,吃著冰冷的豆類罐頭。而這里,在這座小屋里,我的靈魂似乎再次回到我的生命中。
我看到木地板上鋪著漂亮的地毯,房間四壁掛滿了畫,在一張小桌上還擺放著貝殼、書和盛滿鮮花的瓷器花瓶。肯定是一位女士使這間小屋變成了一個家。
我內心的快樂浮現在臉上,這個人讀懂了我的內心。“是的,”他微笑著說,“這一切都是她的功勞,這房間里的一切都是她打理的。”
墻上有一幅畫沒有掛好,他注意到了,走過去把這幅畫掛好。他來回看看,以確認這幅畫掛好了。然后,他輕輕地撫摸了一下這幅畫。
“她總是這樣,”他向我解釋說,“就像母親在給孩子洗完頭后輕輕地拍一下一樣。我總是看她這樣做,所以我也就學會了。”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我注意到,他想讓我在房間里找到些什么。我環視四周,當我的視線落在靠近壁爐的房間一角時,他雙手搓著,開心地笑了。
“就是這!”他大聲叫道,“你發現了!我知道你會發現的,這是她的照片。”我走到一個黑色的小相框前,那里有張女士的照片,這是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女士,她臉上呈現出的甜美和文靜,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這個人從我手里拿過照片,凝視著,“她剛過完19歲的生日,在生日那天,我們結婚了。你看到了她的照片,噢,你就等著看看她吧!”
“她現在在哪?”我問道。
“噢,她走了,”這個人嘆息地說,“她去看望她的父母了,她的父母離這兒四五十里地,她是兩個星期前走的。”
“她什么時候回來?”我問道。“噢,今天是星期三,”他慢慢地說,“她要在星期六晚上才能回來。”
我覺得非常遺憾,我對他說:“對不起,我等不到那一天。”
“等不到?不!你不能走,不然她會很遺憾的。你看,她喜歡有人來和我們在一起。”
“不,我真的要走。”我堅定地說。
他拿起她的照片放在我的眼前,說:“那好,你當著她的面告訴她,你本可以留下來等著見她,但你不肯。”
當我再次注視這張照片時,我不由得改變了主意,我決定留下來。
這個人告訴我他叫亨利。
當天晚上,亨利和我談了很多,但主要是關于她的。
星期四晚上,我們接待了一位來訪者,他是一位高個子、頭發花白的老礦工,他叫湯姆。“我只待幾分鐘,想問問她什么時候回來。”湯姆說,“有什么消息嗎?”
“噢,是的,”亨利說,“我收到了一封信,你想聽聽嗎?”他從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發黃的信,并向我們朗讀了起來。這封信充滿愛意,包括對亨利的愛、對他們親近的朋友的愛和對鄰居們的愛。當亨利朗讀完信后,他對他的朋友說:“你又哭了,湯姆,每當我讀她的來信時,你總是哭,這次我可要告訴她了。”
“不,你不能告訴她,亨利,”湯姆說,“我老了,任何一點悲傷都會使我流淚,我真希望她今晚就回來。”
第二天,星期五,另一位礦工喬來訪,他也請求聽她的來信。這封信同樣也使他流淚,“我們都非常想念她。”
星期六終于到了。我不停地看手表,亨利也注意到了這點,他問:“你是不是認為她會發生什么事?”
我微笑著說:“我相信她一切都很好。”
日落時分,我很高興地看到他的兩位朋友湯姆和喬從遠處走來。他們帶著吉他,還帶來了鮮花和一瓶威士忌。他們把鮮花插在花瓶里,開始彈唱一些節奏很快很有激情的歌曲。
亨利的朋友不停地給他倒威士忌,非得讓他喝。當我想拿一杯喝的時候,湯姆攔住了我,他小聲地對我說:“這杯放下,拿那一杯!”然后把這杯威士忌遞給了亨利。此時已經是午夜,天涼了下來。
亨利喝完這杯酒后,他的臉越來越白,“伙計們,”他說,“我覺得不舒服,我要睡覺去了。”
亨利剛說完這話就睡著了。
他的兩位朋友把他扶起來送進臥室,輕輕地把臥室門關好。他們似乎準備離開,我說:“先生們,請不要走,她不認識我,我只是一個陌生人。”
他們相互看了看,湯姆說:“他的妻子已經死了19年了。”
“死了?”我驚呼。
“死了。”湯姆說。
“她在結婚半年后回去看望父母,在回來的路上,也就是六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就快到家的時候,印第安人抓住了她。此后再也沒有人看到過她。亨利瘋了。他一直認為她還活著。每當六月來臨,他就認為她去看望父母了,于是他就等待著她回來。”
“每年在預計她回來的星期六晚上,我們來到這里和他在一起。我們把安眠藥放進他的酒杯,這樣他就能夠睡個通宵,于是又能平安度過一年了。”
喬拿起他的帽子和吉他,“19年來,每年的6月我們都這么做。”他說,“第一年,我們才27歲……現在,該是我們離開的時候了。”他打開漂亮小屋的門,兩個人消失在斯坦斯勞山谷的濃濃夜色之中。
(周文燕譯自譯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