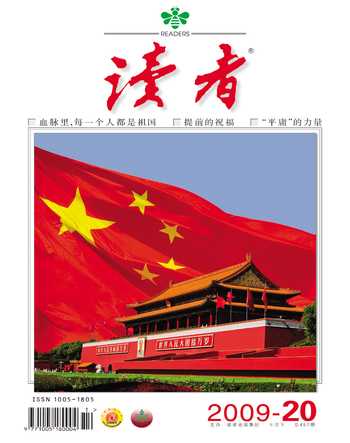“平庸”的力量
周燕芬
常常聽到偉人和名人們說,其實自己是個平凡的人,而胡風的夫人梅志卻更將自己放低至“平庸”,老年的梅志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我實為一個平庸的老嫗,僅比一般人多受了一點苦難,也就多知道一點為人之大不易。其實,我也僅僅是盡自己的一點能力,不傷害生靈,不嘩眾取寵,老老實實做人而已!今天還能坦然地見人,理直氣壯地說話,可能也是我的平庸吧!”
梅志,這位“美麗、堅韌、勇敢”的偉大女性,倘若不是自己親筆寫下這些話,誰能將她與“平庸”聯系在一起呢?因為研究胡風社團的關系,我曾三次走訪梅志老人,也閱讀了胡風、梅志和相關人員的不少著述。直至2004年,90歲高齡的梅志悄然離世,我才漸漸理解了梅志的所謂“平庸”,品味出其中真實醇厚的人生道理。
1933年,胡風因宣傳抗日和其他留學生一起被日方遣送回上海,由此開始了他在左聯的文藝活動。在老朋友韓起家里,胡風認識了本名屠玘華的梅志,那是一個理著短發、穿淡藍色旗袍的清純秀美的小姑娘,胡風一見鐘情,再難忘懷。壓抑中相處了一段時間,終于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跡:“我不能再隱瞞了,只有你才能給我一個歸宿,只有你才能將我從混亂的感情中挽救出來。”
梅志這一年只有19歲。面對胡風急切而忘情的求愛,梅志被嚇住了,她還沒有走進愛情的心理準備,她給胡風寫了一封短信,決定離開上海。胡風瘋了一樣找她,抓住她后又是一番語無倫次的表白。梅志感受到胡風的誠實,感受到自己在胡風心中的分量,回憶這段往事時,梅志說:“看到他那已開始謝頂的腦袋和滿臉的胡茬,真是一副受苦人的面容,心里不由得產生了憐憫和同情——他是一個好人,應該給他以幫助,不能丟開他不管。”
就這么簡單,因為胡風的誠實正派,也不忍心胡風深陷感情的痛苦之中,梅志心軟了。梅志的漂亮在左聯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詩人楊騷給她取了個諢名叫“冰激凌”,典出詩怪李金發。李金發曾說過,讀一篇好作品,就像心靈坐沙發,眼睛吃了冰激凌一般。可見當時的梅志是多么冰清玉潔。像梅志這樣年輕貌美的女學生,在30年代的上海灘應該是有不少出風頭的機會的,而梅志卻很簡單地把自己嫁給了胡風,一個熱情的、急躁的、耿直的、獻身文學的農家子弟。她從此與胡風苦樂共擔,相伴走過53年風雨坎途,不再設想人生還有沒有第二種可能。
梅志也曾以文學為志業,但在理論家胡風看來,梅志實在太幼稚了。于是毫無商量,在成為胡風妻子的同時,梅志也成了胡風文學課堂里的一名學生。胡風曾戲謔說:“我就是喜歡單純而又有點無知的女人。”不想孩子般的單純透明卻成就了梅志的童話創作,得到了小朋友的認可,也得到了苛責的批評家胡風的贊許。
婚后的梅志,讀書寫作成了業余愛好,主要工作是幫助胡風,為他抄稿子,以及帶孩子和操持家務。抗戰期間,梅志跟著胡風顛沛流離。誰也想不到,胡風創辦聲名遠揚的《七月》和《希望》、出版《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等大量文學著作,常常是他一個人唱獨角戲。刊物的編務,包括刊稿和聯系作者、跑印刷廠、設計封面、看清樣、發行以及財務結算等工作,除了自己,主要靠梅志來承擔。詩人綠原在投稿過程中也發現了這個秘密:“全國第一流的文藝刊物《七月》竟沒有一個編輯部,連退稿信都要主編動手來寫。”
戰亂歲月中,梅志支持著胡風的工作,又牽掛著離散的兒女。作為一個女人,她渴望和平日子的到來,期盼一家人能團圓,能平安穩定地生活在一起。這不是一個非分之想,但對于胡風梅志一家人來講卻是萬般艱難。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胡風及其同人被視為主流文藝戰線的對立面而持續受到壓制。到1955年落入政治運動的陷阱,聚少離多的一家人從此真正四分五裂了。
在我走訪梅志的時候,一旦談到1955年以后的遭遇,我探問的口吻就小心翼翼了,唯恐揭開往事讓老人再度傷心,那是一段多么不堪回首的慘痛經歷啊。令人吃驚的是梅志的神情始終淡定并微笑,像閑聊家常一樣柔聲細語,令我的緊張和擔心渙然冰釋。她說了讓我反復思量的兩句話:我相信他(胡風)。只要一家人都活著,就有希望。
因為相信胡風,梅志全力為他謄抄“三十萬言書”;又因為牽系著家人的安危,梅志提醒胡風寫這個不得了啊,但胡風不聽,認為言者無罪。想到手下抄寫的東西可能會成為治罪的證據,親人可能因此而遭殃,女人的心是怎樣被信念和預感中的險境撕扯著,真的無法想象。
1955年5月17日災難降臨之時,梅志也曾想到過死——在生的壓力過于沉重時,選擇死或許還更容易些。但梅志不能死,她不能丟下胡風讓他獨自承擔厄運,她也割舍不下年近80的老母和只有8歲的小兒子。于是,從他們夫妻被帶走關押那一天起,梅志開始了她人生新的征戰:守護自己的親人和自己的家。在獄中,她思念家中的老母和兒女,在她的頑強要求下,準許家人來探視,她可以見到孩子們了。老母病逝后,梅志力爭奔喪的權利,從而獲得釋放,與孩子們團聚。緊接著,梅志開始打探胡風的音訊,向公安部要求見胡風,從不予答復到有了答復,從不準探監到終于見面,梅志奔波在家和公安局和秦城監獄之間,雨雪風霜,不屈不撓。當十年未見的親人站在面前的時候,她只有一個信念,我們還都活著,我們一定要堅持活下去。
“文革”當中胡風才正式被判刑,梅志再一次離開兒女們,陪胡風前往成都,度過了13年漫長的伴囚生涯。孩子們漸漸長大,已經能夠離開父母了,但胡風十年獨身坐牢又面臨放逐四川,他既是囚犯,也是一個病人,他離不開梅志了。但即便是這樣,夫妻相依為命的日子也不長,胡風再一次從梅志身邊被押走,梅志成了無囚可伴的人。一直到胡風被改判無期徒刑后的1973年,夫妻再次相見,此時的胡風身體極度虛弱,精神也崩潰了,在他思想混亂心里恐懼的時候,梅志像哄孩子一樣抱他在懷里安慰他,胡風清醒過來的第一句話是:“真是你嗎?不是在夢中?太可怕了!”梅志說:“今后我一直陪伴著你,別害怕。”胡風這才安然入睡。胡風是怎么活過來的,動亂的年代、復雜的環境和政治批判的狂潮都擊不倒胡風,但當他的信念和精神支柱被摧垮時,胡風絕望了。支撐胡風活下來的,唯有妻子溫柔的關懷,唯有親人愛的牽掛。
1979年,胡風重獲自由,一家人才過上長久夢想的平靜安定的生活。1985年胡風病重,冤案還沒有徹底解決,看到臨終的胡風依然焦慮不安,梅志心碎了,她得讓親人走得安心啊。她不顧一切地許諾:“我會為你說清的。”為了這一承諾,梅志以年老之身,以難以想象的堅強意志寫出了60萬字的《胡風傳》,給后人留下解讀胡風、認識胡風的最完整和翔實的資料。然后,在兒孫繞膝的溫馨快樂中,安靜地度過了余生。
一個女人的一生,沒有立下什么宏愿大志,對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沒有超常的期許,一心為家人的平安幸福付出努力,這大概就是梅志所說的平庸。梅志說,在那些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日子里,關起門來的小家庭中還是能聽到歡聲笑語的,也就是靠著這些,一家人活下來了。這就是庸常人生的力量。
梅志曾寫過一篇題為《珍珠梅》的短文,說1954年的時候一家人去北海,只看到樹林中一叢叢的叫做“珍珠梅”的小白花,這花看著不起眼,花期卻長,但沒有香氣。胡風建議家人在花前照相,并說正因為珍珠梅花小,不起眼又沒香氣,所以沒人去采它,它才保持得長久。珍珠梅實在是太平常的一種花,但它樸素、堅韌,以開花的持久最終贏得人們的關注。以花照人,珍珠梅正符合梅志的身份和秉性,珍珠梅所昭示的,也還是“平庸”的力量吧。凡見過梅志的人,無不為梅志那永遠的微笑所感動,很純真、很溫暖,當你想到一位飽經滄桑歷受傷痛的老人還能笑得如此純真溫暖時,那就不只是感動而是震撼了。倘若要贊嘆女性的堅強和偉大,任何稱頌的詞匯用在梅志身上都不過分,但她總是帶點羞赧地搖頭,說自己沒有那么了不起,自己沒辦法不保護親人和家庭。去到監獄,胡風看到妻子好好的,才能堅持下去;回到家里,孩子們看到媽媽好好的,也才能正常生活,梅志是家的守護神。女人為家看似平庸,而如梅志這樣于絕境之中堅守自己的家,已然是一種偉大的“平庸”了。
詩人牛漢有兩句詩寫得好:“梅志是胡風的花朵,胡風結出了梅志的果實。”沒有花開,何來果實,花朵的成就,已在果實之中了。
最后一次見梅志,是2003年冬天在北京協和醫院的病床前,我把從家鄉帶去的兩個很大的紅石榴放在她的枕邊,希望能夠傳達我美好的祝福。虛弱的梅志再一次露出她純真溫暖的笑容,臉色在石榴的映照中有了一抹紅暈,輕輕說了一聲:“真好看。”至此一別即成永訣,梅志先生的美麗笑臉就定格在我的腦海中了。
(陸紅芳摘自《美文》200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