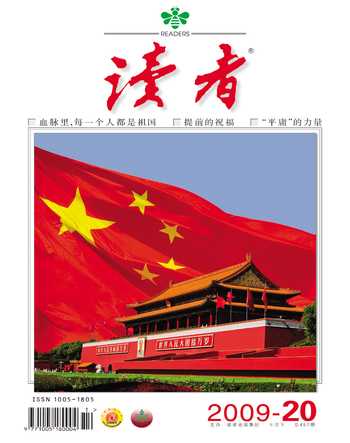淚讀歷史巧合
吳光輝



一
我的腦海里反反復復地閃現著民國時期兩個腆著大肚子的少婦形象。她們素不相識,甚至相互敵對,可她們的命運卻是驚人的相似。我一直弄不懂,她們為什么會從兩個不同的歷史角度走向幾近相同的結局。
60多年前的生離死別,使這兩位中國現代史上的美人肝腸寸斷。這時她們都懷有身孕,可她們又不得不把各自的丈夫送上前線。她們都萬萬沒有想到,她們各自心中的英雄會一去不回,橫尸沙場。這兩位美人,一位是林穎,另一位是王玉玲。林穎守寡時22歲,王玉玲更小,只有19歲。她們一位是新四軍第4師師長彭雪楓的愛人,另一位是國民黨軍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的太太。
我站在洪澤湖古老的石堤上,想象林穎與彭雪楓生離死別的那個傍晚的種種情景。那是1941年8月的一個傍晚,那天肯定有一輪火紅似血的落日熱情奔放地與千里大湖熱吻,肯定有一群白鷺在那條滿載著離情別意的漁船的桅桿四周盤旋。林穎與彭雪楓便站在洪澤湖邊的石堤上,兩人的臉上掛著淚花,四手緊握,相對無言。不遠處十幾條漁舟已經排成了一行,“嘩啦啦”地拉起了白色的漁帆,接著傳來部隊出發的嘹亮軍號。林穎的心猛然一緊,下意識地一把將彭雪楓拉到自己的胸前,緊緊地抱著不肯放手。她想永久地抓住自己的愛。
“我真的不想讓你離去。”林穎流著淚水,望著站在船頭的彭雪楓大聲地說。彭雪楓揚著手臂對她喊道:“等著我,等勝利了,我們全家團聚!”林穎挺著大肚子高聲喊道:“我等你回來!”
然而,林穎再也等不回自己的丈夫,這次分別成了林穎與彭雪楓的生死訣別。
在彭雪楓戰死3年之后,同樣也是在淮海大地上,19歲的王玉玲也與林穎一樣,挺著9個月的大肚子與丈夫話別。只是王玉玲不像林穎那樣在分別時產生不祥的預感,而是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這是自己與丈夫的訣別。
在王玉玲的心目中,當然也在許多國民黨將士的心目中,張靈甫幾乎是一位常勝將軍。1937年,張靈甫任國軍153旅305團團長,開赴上海參加淞滬保衛戰,他甩掉上衣抱著機槍跳出戰壕,帶領敢死隊沖鋒在前,殺得日寇丟盔棄甲;1938年武漢會戰,張靈甫主動請纓,率領敢死隊連夜奪回被日軍搶占的制高點,右腿被日寇的機槍打斷,身中7彈不下火線;1945年芷江保衛戰,張靈甫與日軍血戰三天三夜,大獲全勝。抗戰八年,張靈甫屢立戰功,職位也一路高升,成為國民黨赫赫有名的少壯派將領。
對于這樣一位丈夫,作為太太的王玉玲總是以為他會永遠這樣勝利下去,壓根兒就沒有想過最后會全軍覆沒。因此,這一天早晨告別時,站在美式吉普車前,她還帶一絲撒嬌的口氣對張靈甫說:“親愛的,吻我一下。”張靈甫看了看四周荷槍實彈的衛士,微笑著將愛妻輕輕地擁在懷里,在她的額頭上萬般柔情地吻了一下。
這一吻就是王玉玲和張靈甫的最后一吻,他們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現代版的《霸王別姬》。
二
我佇立于9月的洪澤湖邊,承受著夏末太陽的余威,聞到了洪澤湖彌漫著哀痛的水腥味兒。
9月對彭雪楓和林穎來說,是一個十分特別的月份。彭雪楓似乎早就覺察到了這個問題。他在給林穎的情書里曾經這樣寫道:“9月,對我有特別的意義。我的生日在9月;1926年的9月是我由青年團轉為入黨的日子;1930年的9月,我們從長沙入江西開始建立蘇維埃;而1941年的9月,我的終身大事得以決定了。難道這叫做巧合?”也就在他寫這封情書的整整3年之后的1944年,他戰死沙場,而他犧牲的時間恰恰就是他早就認為十分特別的9月。此外,彭雪楓生前寫給林穎的情書也恰好是90封,又是“9”這個特別的數字。
1944年9月11日,在收復河南夏邑八里莊的戰斗中,彭雪楓不幸被流彈擊中,當場身亡,年僅37歲。按常理,他根本就不應該犧牲。戰斗已經勝利結束了,作為最高指揮官,他當時正站在八里莊寨墻上指揮打掃戰場,可這時飛來一顆流彈不偏不倚地射中了他。
那顆子彈發射時的動機肯定不是對準彭雪楓,然而當子彈擦過莊前的那株老槐時,完全偶然地改變了原來的飛行方向,向著它必然的結果減速飛行;本來流彈的殺傷力應該大大減弱,然而它的余力偏偏恰好可以擊中目標;原先流彈的飛行方向完全是失控的,然而它偏偏命中了彭雪楓的心臟,一彈致命。
當彭雪楓突然之間仆倒在地時,一直站在他身邊的老戰友、參謀長張震幾乎沒有反應過來。他一把將彭雪楓抱在懷里時,彭雪楓什么話也沒來得及說就死了。我推想彭雪楓在被流彈擊中的一剎那,肯定想到了遠方的妻兒,昨天深夜他還抽空寫了一封家書。這是他給林穎寫的第90封情書,這封情書還沒來得及寄出去。在這最后一封信里有這么一段話:“時刻思念的穎:人們說我是個情感豐富的人,過去有點壓得下,近來有點異樣了,你的影子自早至晚怎么也排遣不開……紙短言長,夜深人靜,下次再寫吧。你的楓。”那顆致命的子彈將這封最后的情書穿透,鮮血將情書染成了紅色。
與彭雪楓一樣,作為北大高才生的張靈甫也喜歡給太太寫情書,也是在前一天深夜寫了他最后一封家書后戰死在孟良崮的。只是他的這封家書沒有像往日那樣抒發對妻子的深情,也沒有說“下次再寫吧”。這是一封遺書:“……老父來京,未克親侍,希善待之。幼子希善撫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他臨死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嬌妻乳兒,妻子只有19歲,而兒子才剛剛出生十幾天,自己還沒能見過一面呀!想到這些,張靈甫肯定潸然淚下。
張靈甫身中數彈身亡之后,在他的內衣口袋里發現了這封給妻子的最后家書。張靈甫的這封家書也被子彈擊中,也被他的鮮血浸透,和彭雪楓最后的家書一樣。
然而,張靈甫的這封帶血的家書并未交到王玉玲的手里,彭雪楓的那封帶血的家書也沒有交到林穎的手里。她們都沒有被告知丈夫戰死沙場的消息,她們仍在一天一天地盼望著她們的英雄能夠早日歸來,與妻兒團聚。
我推想林穎肯定日復一日地抱著剛剛出世的嬰兒,站在她送別丈夫的湖邊,凝視著大湖的盡頭,期盼著那水天相連的地方能夠出現丈夫的歸帆。她從早站到晚,從月圓站到月缺,又從深秋站到了嚴冬。她總是輕輕地拍著襁褓中熟睡的嬰兒,自言自語地說:“你爸爸讓我們等著他呀,怎么還不回來呢?”
三
我翻閱彭雪楓和張靈甫的有關資料,越是順著他們的命運發展線索往下讀,就越是驚異于他們以及他們夫人的人生結局是何等的相似,特別是他們戰死之后的遭際簡直就是如出一轍。彭雪楓犧牲之后4個月,組織才告訴林穎,而張靈甫戰死的消息恰恰也是4個月之后才讓王玉玲知道的。也就在彭雪楓和張靈甫分別戰死4個月之后,毛澤東、蔣介石分別為他們舉行了國葬。中共中央給彭雪楓的挽詞是:“為民族為群眾二十年奮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國;打日本打漢奸千百萬同胞自由平等澤被長淮。”蔣介石為張靈甫親撰了祭文:“以我絕對優勢之革命武力,竟為劣勢烏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損失,能不令人哀痛!”共產黨為彭雪楓在洪澤湖西岸的半城鎮建造了一座紀念塔,國民黨為張靈甫在洪澤湖東岸的淮陰城建造了一座巨墳。而這兩位將軍的身后之事那樣的“雷同”就更是令人吃驚了:他們的這兩座紀念物后來同樣被摧毀,同樣被掘墳刨尸,同樣被拋骨荒野。
1946年的11月,淮北根據地落入敵手,地主還鄉團血洗淮北,對彭雪楓這位抗日英雄的紀念塔居然也不放過。他們用機槍掃射紀念塔,拉倒新四軍銅像,扒開彭雪楓的墳墓,劈開彭雪楓的棺材,將彭雪楓的遺骨全部拋入洪澤湖里。當天夜里,一個啞巴腰間扎著一只小蒲包,冒著生命危險悄悄地潛進湖里,將彭雪楓的遺骨一塊一塊地摸上來,放進小蒲包里,然后一趟一趟地送至小河東的洪澤湖游擊隊。然而,就在他最后一次去打撈遺骨時,天已放亮,很快就被敵人發現了。敵人把他抓去嚴刑拷打,逼著他交出彭雪楓的遺骨,可他堅強不屈,至死不交。最后敵人用繩子捆起了他的手腳,將他扔進了洪澤湖,用機槍活活地射死。
我沒有聽說張靈甫的遺骨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去保護。我想恐怕只有這一點,才是張靈甫與彭雪楓之間的不同之處吧。
張靈甫死后遺體下落不明,普遍的說法是由華野特務團士兵埋葬在沂南縣一個叫野豬旺的地方,隨后蔣介石命令將他的遺體移葬南京,并在南京玄武湖畔修筑墳墓。相傳國民黨軍隊占領野豬旺后,便將棺木挖出直送南京,可途經淮陰時遺體開始腐爛,只得將棺木埋葬在淮陰城南公園的北側。據說當時這座墳墓建得十分高大氣派,約有兩層樓高。然而,在解放軍解放淮陰后的第二天,就挖開了他的墳墓,劈開了他的棺材,拉出了一堆尸骨。南京玄武湖邊的張靈甫空墓,也在解放軍占領南京的當天被炸毀了。“文革”中,后來放在淮陰實驗室里的張靈甫骨架被紅衛兵小將弄去游街,最后居然也被扔進了洪澤湖。
這千里大湖成為彭雪楓和張靈甫共同的歸宿。而他們的遺孀的人生歸宿也是何等的相似。王玉玲帶著母親、兒子赴臺以后的生活十分艱苦,每個月只能靠領取撫恤的幾十斤大米艱難度日。為了養家糊口,1953年王玉玲考取了美國紐約大學。她帶著母親、兒子一起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她在美國的生活依然十分拮據,只得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去大學聽課。經過4年的艱辛努力她如期畢業,到美國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一直到退休。這位豪門千金在這幾十年里,用她嬌柔的雙肩承擔起了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擔;這位美麗的遺孀從她19歲丈夫戰死直到風燭殘年,漫漫60多年獨守終身。1967年周恩來總理曾經邀請她回國參觀,并且對她說:“張靈甫是個好人。我在黃埔軍校當政治部主任時,他是我的學生,我沒能把他勸說過來,我有責任。”王玉玲聽了周恩來的話,淚水奪眶而下。而彭雪楓烈士的遺孀林穎,后來的人生道路也是十分坎坷。作為大家閨秀的林穎,1957年在紡織部工作時先是受到批判,后來被打成右派,接著又下放到保定化纖廠勞動改造。后來還是經過周恩來總理的多次協調,才摘掉了戴在她頭上的右派帽子。
我徘徊在洪澤湖的楊柳岸邊,凝視著泛著紅色的湖水,推想彭雪楓和張靈甫的尸骨早已化做湖底的淤泥,就和水漫泗州時葬身湖底的20萬百姓一樣;推想他們的亡靈肯定一起躲到這個世界的外面去了,他們在那里靜靜地等待,等待著狂風將60多年前的歷史碎片刮起,等待著能夠看見最終落滿大地的不是枯葉,而是愛。
(顧沖摘自《散文百家》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