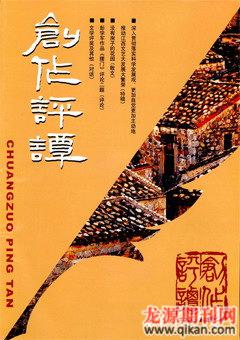一路這樣走來
彭學軍,上世紀六十年代生于湖南吉首,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編輯,中國作協會員。1990年開始發表小說。著有中短篇小說集《告別小妖》、《歌聲已離我遠去》、《長發飄零的日子》、《藍色滑板上的小妖精》,長篇小說《終不斷的琴聲》、《你是我的妹》、《腰門》,散文集《紙風鈴紫風鈴》等二十多部。曾獲宋慶齡兒童文學小說大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冰心兒童文學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等獎項。作品多次入選各種優秀兒童文學作品集。
最初的時候——是說這三十年的最初、也就是1978年,我還在湖南吉首的自治州少年體校。
我學的是田徑,專項是四百米和八百米。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年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在體育場鋪著黑煤渣的跑道上跑圈子,一圈一圈又一圈,氣喘如牛,汗水滴在地上摔八瓣。耳邊還不時響起教練兇巴巴的吼聲:快點,再快點!那架勢跟舊社會的地主差不多,只是手上少了一根鞭子。日曬雨淋再加上大運動量的訓練,豆蔻年華的少女出落得跟非洲難民一樣,又黑又瘦。
那時,家里喜事連連。我父母都是老師,文革的時候下放到鄉下去了,那一年,落實政策陸續調回了城里,母親在衛校,父親在自治州的民族中學,那是當地最好的一所中學,周邊的十個縣都把最好的學生送到那所學校來讀書,來讀書的學生只有一個目標:考大學——那時,已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了。
我開始考慮自己的前途。我已經厭倦了跑圈子,老這樣跑下去,什么時候才能停下來呢?那么,出來讀書,然后考大學,我行嗎?我十一歲就進體校,基本上沒讀什么書,底子太差了……但最終,我還是離開了體校。
以我的成績,民族中學就是拼了小命也進不了的,但因為是教工子女就很順利地成了那里的學生。以前是一天到晚地跑圈子,后來是一天到晚地做功課。從早自習到晚自習,星期天也要上半天課。那個時候老師補課從來不收費,很無私也很有激情,干勁十足,只要把學生教好了,成績提高了,他們就會由衷地高興。
也就在那時,我第一次接觸到了兒童文學。
還記得我們住在操場邊的一排平房里,隔壁是語文老師,和我家一樣,她家也是三個女兒,大女兒和我是同學。語文老師比較重視閱讀,給她的女兒們訂了《少年文藝》,每期新到的雜志我都會借來讀,每每讀到精彩的文章就興奮得要命,也羨慕得要命。那點可憐的閱讀成了我發奮讀書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
后來,我父母調動工作,舉家遷到了江西贛州。
贛州是一座古城,宋代時已初具規模,至今仍有一段三千多米的宋城墻橫臥在贛江側畔。剛去的時候,覺得它寧靜清潔、古風撲撲,又稍稍有點落寞。也許我該把它看成我的第二故鄉。
我在贛州上了大學,畢業后分在一所中學做老師。
我教高中的語文,和我同分到那個學校教語文的女老師還有三個。我們四個人常在一起玩。那時才畢業,都還沒有戀愛,四個人湊在一起就是瘋玩,或商量下次去哪瘋玩。
那時是八十年代中期,沒有卡拉OK,沒有酒吧和咖啡館,連像樣的大商場都沒有。我們湊在一起多半是看電影,然后手牽手地壓馬路,肆無忌憚地高聲說笑。有一回,玩得太晚了,回到學校鐵門已經關了。看門的老頭可能又喝多了酒,怎么也叫不醒,無奈,四個平時看上去還算溫文爾雅的女教師只好爬鐵門……爬鐵門時笨拙而又輕盈的身影成了我們作為一個女孩的最后的、標志性的畫面,定格在了記憶中。很快地,就有人請婚假、休產假了,然后是另一個……
我大概算不上一個好老師,教了幾年書后就沒了激情,而且學校越來越重視升學率,每次考試后,算總平均、及格率、優秀率……每個老師都精細得很,也不免斤斤計較,但我對這些都毫無興趣。
我得找點有意思的事做,于是把念大學時訂的雜志都翻出來:上海和江蘇的《少年文藝》、《兒童文學》、《東方少年》,也許是想延續讀中學時的那種閱讀感覺,我訂了一堆這類的雜志。我把這些雜志重溫了一遍后,心里燃起了一個希望:我要寫小說,就寫中學生,我有這樣的生活,而我的文字一直還不錯,讀中學時作文常被老師當作范文念……
那時已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還是文學備受推崇的時代,能發表作品、出書。是一件無上榮光的事。我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發表了第一篇小說。
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去了電視臺。
也許是職業和視野發生了變化,我開始注意這個城市的變化。城市越來越大了,它迅速地向郊區延伸,高樓也越來越多,人哦車哦一下子多了起來,大街上一天到晚都熱鬧非凡,人們的衣著也日益地光鮮、時尚。這個城市再也不會讓人感到落寞了。
但我終歸是一個喜歡清靜的人,我很享受去鄉下采訪的日子。特別是春暖花開或秋高氣爽的時候,走在鄉間小路,滿眼蔥綠,空氣中飄散著植物的青澀和瓜果的芬芳。
有一回,鄉里派了一輛農用車送我們,走到半路,車出故障了。那天正逢趕集,本來就不寬的馬路被擠得只剩下細細的一條。到了一段長長的陡坡,司機也不減速,直直地往前沖。我當時坐在駕駛室,看見司機滿臉是汗,神情緊張,嘴里嘟嘟噥噥地罵著,就知道,剎車失靈了。怎么辦,再這樣沖下去會出人命的!我壓抑著恐懼,強裝鎮定。指著前面路邊的一堆碎石說:“沖到那堆碎石上去。”司機聽了我的,讓車輪陷在了碎石里才剎住了車。還有一次進山采訪迷了路,頂著烈日在山里轉悠了一天,天快黑了才找到出山的路:去礦山,爬了大半天的臺階,腿軟得發抖,可到了目的地因為大霧天設備受潮根本開不了機……還有雨中的果園,冬天的林場。嘰嘰咕咕的養雞場……有些經歷其實是為著記憶存在的,為著有一個豐沛的人生。
我大概是個做事沒有長性的人,電視臺沒呆幾年,又去了出版社,那已經是上個世紀的最后一年了,我離開了那個已經相當繁華了的城市。
我的寫作也有了一些長進,書一本一本地出,還獲了一些獎,有了一點知名度。而這個和文字打交道的職業似乎也更符合我的心性,我有一種船靠碼頭車到站的歸宿感。我一邊看著別人的稿子,一邊寫著自己的稿子,我很滿意這樣的狀態。在一篇文章中我這樣表白道:“如果,必須要有一個職業并且在職業之外再做點自己愿意做的事,除了現有的狀態,我不知道對于我這樣一個散淡、平和,對人對事有著淡淡的疏離的人來說,還有什么更好的選擇。只是愿意,我可以盡可能多的只面對文字,這就極大地成全了我的個性。那些優美、靈動、睿智、幽默、飄逸、潔凈的文字,以及由此而結構、交織、描摹、顯影出來的美麗的故事、不朽的人物、雋永的思想和寫作者真切而生動的靈魂,是那樣的令人愉悅和贊嘆。如果讀到了它們之中的極品呢——當然是就自己的欣賞水平和閱讀視野來說——那就只能是深深的沉醉、艷羨和激賞了。然后,會不自覺地角色轉換,一個寫作者的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于是,暗暗地妒意橫生,咬牙切齒或萬分沮喪地想:這樣的東西,就是再給我兩個腦袋也寫不出來哦。忍不住再讀一遍,心里的‘不平就漸漸被它的卓越銷融了,寬慰地、感恩地想到:幸好我是個編輯,被我讀到了,如果我僅僅只是個讀者,泱泱書海,很可能就失之交臂了。”
編輯這個職業應該比其他的職業更能感覺時間的流逝吧?每年幾個訂貨會一過,到了要報年度選題的時候,就知道是年底了,又是一年要過去了。明年又該做些什么書呢?就像老農咂巴著煙斗尋思著:明年地里種些什么好呢?
我們不能說文字是永恒的,但至少,它是可以流傳下去的,這樣,文字就有了時間的意義。這些文字伴隨著我走到了2008年。走到了可以寫“我這三十年”的時候——其實只要在這個世上活過了三十年就可以勝任這個題目,但我還是覺得它有一種沉沉的歲月之感。它讓我想起曾采訪過的一位老人。
很多很多年以前,老人還是一個剛過門三天的新媳婦的時候,她的丈夫就離開了她。臨走時,她穿灰軍裝、戴八角帽的丈夫望著田里青青的禾苗說:“等著我,到了收稻子的時候我就回來了。”
從此以后,每當太陽下山的時候,她就站在高高的老門檻上朝遠處張望,在她日日的守望之中,禾苗黃了熟了割了,又青了……她的丈夫沒有如期歸來。人們都說他丈夫戰死了,不會回來了,勸她改嫁,可她不聽,她只聽丈夫的話——“等著我。”她為他的弟弟妹妹成了家,給他的父母送了終,后來,只剩下她一個人了,沒有人能活過她……她獨自一個人在老屋里守著,天天站在老門檻上望著,門檻硬是被她踩得缺了一塊,萎頓了下去,三十年,又一個三十年,從那萎頓下去的老門檻上溜走了。如今,她已活在第三個三十年的日子里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還在那里等著她的丈夫。
可是,不是人人都能像她一樣堅忍地活著,至少我做不到。不過我們這樣的時代也不會再有那樣的故事了。但不管怎么說,如果人的一生以三十年為一個單位來衡量,對有些人來說有點殘酷,對有些人來說又有點奢侈。而對一個孩子來說,大概是不可思議的漫長,就像一段沒有盡頭的路。不過等他走過去后又回望來路時,又會是另一種感覺——怎么就到頭了,沿途的風景我還沒看夠呢。幸而,腳下還有路……
我現在就是這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