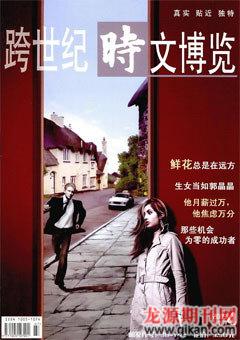我在阿布格萊布監(jiān)獄當(dāng)獄警
潘曉凌
阿布格萊布自然成為伊拉克反美武裝最集中的襲擊目標(biāo)。加之阿位于三個(gè)村落之間,時(shí)不時(shí)地,會有一個(gè)火箭筒或迫擊炮從某個(gè)村子打進(jìn)來。一次,一枚火箭筒命中一個(gè)正在修的囚犯樓,削掉一角,還把一個(gè)戰(zhàn)友的頭盔削去,在他的腦袋上劃了一道口子。
2003年臭名昭著的美軍虐囚事件發(fā)生后,阿布格萊布成了伊拉克最敏感的地方。我們這撥駐扎軍隊(duì),包括一個(gè)工程營、一個(gè)炮兵營、一個(gè)工兵營等,就是為了制約領(lǐng)導(dǎo)人的權(quán)力。此外,部隊(duì)每周起碼開一次座談會,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七項(xiàng)紀(jì)律八大注意”。那往往是我們的“瞌睡會”。
獄警分內(nèi)警與外警,內(nèi)負(fù)責(zé)監(jiān)管關(guān)押人員,外負(fù)責(zé)防御,每人一天工作13個(gè)小時(shí),凌晨兩點(diǎn)至下午兩點(diǎn)倒班,中間交接一小時(shí)。
在押人員從搶劫偷竊到宵禁期間出來找牛的,無所不包,關(guān)押人數(shù)最多時(shí)高達(dá)6000人。阿布格萊布根據(jù)嫌犯的危險(xiǎn)程度設(shè)置了五個(gè)營房。一營的管制最寬松,一個(gè)牢房可關(guān)30-50人,他們白天可以踢足球、打排球;五營則是一個(gè)個(gè)單間,通常用來關(guān)押恐怖分子,他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老老實(shí)實(shí)呆著。
營房全是帳篷,原是美國大兵的軍營,后來我們發(fā)現(xiàn)伊拉克的監(jiān)獄條件好,便將其改裝成軍營,將帳篷區(qū)改造成現(xiàn)在的阿布格萊布。
別以為從這座帳篷監(jiān)獄越獄是件容易的事。帳篷四周圍了7層鐵絲網(wǎng)——一層鐵絲網(wǎng)加一層鋼筋混凝土水泥墻,再一層鐵絲網(wǎng)加一層更高的水泥墻。此外還有瞭望塔,每名獄警隨身攜帶218發(fā)子彈,即便是6000人同時(shí)越獄,我們每人也能對付100個(gè)嫌犯。
我們沒遇到越獄的,雙方之間的“斗智斗勇”倒天天上演。每個(gè)月都有獄警被打,襲擊者在點(diǎn)名時(shí)躲在廁所里或別的什么陰、暗角落,猛地朝搜尋的獄警襲擊。阿布格萊布不乏這樣的亡命之徒,他們將付出極大的代價(jià)。我們會將這家伙從第四營到第一營逐次各關(guān)一個(gè)月,每到一個(gè)營,他所在的獄友統(tǒng)統(tǒng)不得打球、抽煙,大家便把怒氣全發(fā)到他身上。我們要做的,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我從來沒有受到襲擊,因?yàn)橐晾巳藢χ袊说挠∠蟛诲e(cuò),在他們看來,中國人到伊拉克只是來做生意,讓他們一起有錢賺,不像美國人,把他們平靜的生活攪得支離破碎。
阿布格萊布自然成為伊拉克反美武裝最集中的襲擊目標(biāo)。加之阿位于三個(gè)村落之間,時(shí)不時(shí)地,會有一個(gè)火箭筒或追擊炮從某個(gè)村子打進(jìn)來。一次,一枚火箭筒命中一個(gè)正在修的囚犯樓,削掉一角,還把一個(gè)戰(zhàn)友的頭盔削去,在他的腦袋上劃了一道口子。
晚上,我們經(jīng)常能看到一枚又一枚閃光彈在附近村落發(fā)出橙色和白色的光,我們呸道:“全是狗屎!”
我不想在這狗屎地方送命,盡管我參軍是因?yàn)槲覠釔圮娐蒙睢N也恍枰们啻簱Q國籍,參軍之前,我已是美國籍。我們營有一個(gè)菲律賓人就是綠卡兵——在美國,持綠卡者便有資格參軍,連續(xù)服役五年且赴戰(zhàn)場執(zhí)行任務(wù),便可入籍。
我們對綠卡兵戰(zhàn)友沒有任何歧視,在基層部隊(duì),每個(gè)人都靠本事吃飯,靠能力贏得尊重。在美國,哪有什么本國人、外國人,主流和非主流,它就是一鍋大雜燴。但在領(lǐng)導(dǎo)層,身份是最重要的,比如軍隊(duì)軍事軍情局就不招綠卡兵。因此,綠卡兵至今官不至下士。
從伊拉克回到美國后,那個(gè)菲律賓戰(zhàn)友如愿以償拿到了美國國籍,還請大家喝了一晚上酒。我也從現(xiàn)役調(diào)入后備役。美軍要求預(yù)備役軍人每個(gè)月定期做體能測試。跑步、仰臥起坐和俯臥撐,如果不合格,將會受到降級、扣工資等處分。保持良好體能是必須的,如果美國進(jìn)入戰(zhàn)時(shí)狀態(tài),上前線的是我們這些老兵,而不是剛?cè)胛榈男卤?/p>
其余的時(shí)間,你愛干嘛干嘛。美軍工資不高,一年四五萬,相當(dāng)于普通工薪階層收入。但福利很好,如高額免稅保險(xiǎn)、大學(xué)獎學(xué)金、醫(yī)療保險(xiǎn)。
我現(xiàn)在麻省州立大學(xué)念旅游管理,我天生是一個(gè)“在路上”的人。但我和其他華裔美國大兵沒有聯(lián)系,美國也沒有華人戰(zhàn)友會,主要是人數(shù)太少。當(dāng)了5年兵,我只碰到一個(gè)同胞。畢竟,當(dāng)兵絕對不是個(gè)熱門選擇,尤其近年戰(zhàn)爭頻繁,美國一度出現(xiàn)征兵荒。能拿到美國綠卡的華人都非平庸之輩,誰愿意用生命做押注?
正因?yàn)槿绱耍绹鐣Υ蟊浅W鹁矗驗(yàn)槲覀冞@些志愿兵,他們不必將自己的兒子送上戰(zhàn)場。我穿著軍裝走在大街上,經(jīng)常會有人過來握住我的手:“感謝你對美國和我們所做的貢獻(xiàn)。”
我不忌諱向國內(nèi)的朋友說,我是一個(gè)為美國打仗的美國大兵,我在法律上是美國人,為它而戰(zhàn)無可厚非;同時(shí),我還是一個(gè)中國人,但我的身份絲毫不妨礙我熱愛中國。
不過,如果我爺爺還在世的話,不知會發(fā)生什么。這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解放軍也許會驚呼,天哪,我的孫子竟然成了美國大兵!逃不掉的食物鏈
樸小佛
有一次我無意中踩死了一只正在搬運(yùn)食物的螻蛄,周圍沒有人,我便蹲下來靜靜地看了一會兒,它健壯的兩條前腿還在顫抖,但是柔軟的腹部卻一片狼藉。我不知道它的家庭、妻子和女兒、餐桌,以及沒有食物的窘迫,不知道它鄰居的議論和它母親的號啕大哭。我想到從什么時(shí),候我們開始忘記了懺悔,感受不到自己屠殺的罪孽深重?
其實(shí)有很多時(shí)候,我們是可笑的,我們的驚訝,嘆息,以及鄙棄,在很多沉默窺視的生命服中無比膚淺。
一條狗在倉皇躲避你的柴棒的同時(shí)在心里暗笑你的勢利人生;一只蒼蠅冷冷地注視著你把它的朋友放在吃完的飯菜中賴賬;同時(shí)一只鳥,站在公園的樹上,微笑著聆聽,你對情人說天荒地老;甚至一只蟑螂,憐憫地思考你在洗澡間里面對鏡子的惶恐,是因?yàn)槌嗦愕某舐€是因?yàn)闅q月的如水流逝?
它們肯定會憐憫我們不自量力的欲望,憐憫我們被生活扭曲的臉,憐憫我們對失敗的惶恐和對瑣事的過于關(guān)注,憐憫我們再也無法像它們那樣欣然面對永久的消亡。
我曾經(jīng)在一個(gè)報(bào)社做過一段時(shí)間的熱線記者。我們無謂地看著血泊中的民工在鏡頭中沉默不語,看著他們破碎的頭顱,從絞肉機(jī)里拖出的身體,我們擁有的只是可笑的恐懼和惡心。只有蒼蠅伏在他們的身上。我愿意相信那是一種默哀甚至哭泣。
甚至后來這種頻繁的死亡也被我們所厭倦,我們寧愿去關(guān)注一只生長著三條腿的牛犢,或者寵物狗的保養(yǎng)。我們不愿意想那汗血后面的故事。
不愿意想那個(gè)民工的愛情和理想,他,也曾看見過這個(gè)世界的陽光,他把自己畏縮成一只蒼蠅或者一只倉皇的老鼠,然而最終還是沒有逃脫人們對死亡的白眼。我看見他慢慢起身,細(xì)致地擦拭每,一處血污,轉(zhuǎn)頭向我,說,你只愿意為一只螻蛄的意外死亡傷心落淚嗎?我惶然地?fù)u搖頭。
我認(rèn)識一個(gè)美食家,經(jīng)常眉飛色舞地對我說起各種肉香的區(qū)別,他吃過活割的驢肉,吃過烤牛眼睛,吃過活蹦亂跳的蝦,吃過頭尾都能動彈的活魚,他最喜歡烹飪飲食類節(jié)目,崇拜那些分析各種動物吃到嘴里有什么感覺,咽到胃里有什么營養(yǎng)的評委。他看到每一種生物,第一個(gè)念頭就是思考它的做法和味道。
他看不見鹿的溫順、鴿子的寧靜以及狗的忠誠——任何美好圣潔的事物最終都會被他切割,吞咽,然后化成一個(gè)飽嗝一個(gè)屁——他渾身布滿了各種生命留下的怨恨,每一個(gè)毛孔都散發(fā)出奇怪的氣味,血液中流淌著來自各種動物尸體的脂肪粒。
就是這樣一個(gè)人,他在吃過猴腦后幻上了神經(jīng)衰弱癥,耳朵里總是響著那只被堵住喉嚨的猴子詛咒般的囈語,腦子里總是它睜裂了眼眶而流血不止的眼睛,他在幾次失敗的自殺后離了婚,踏上了去高原的路,他從西藏界開始磕長身頭,后來便杳無音信。
他在上路前問過我,你……知道什么叫天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