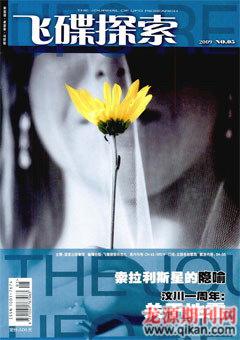地震預測的夢想與現實
方舟子
地震的“預兆”和“預測”
“5·12”汶川地震發生之后,許多人在震驚之余不禁感到疑惑:地震局為何沒有發出預報?這么大的地震會一點征兆也沒有嗎?一時間網上出現了眾多質疑、指責、嘲笑地震局的聲音,人們或者批評地震局玩忽職守忽視地震預兆,或者懷疑地震局為了社會穩定有意不發出預報。
最為一般人熟知的地震預兆莫過于動物的異常行為,于是《華西都市報》2008年5月10日刊登的一則題為《綿竹西南鎮檀木村出現大規模的蟾蜍遷徙》的報道被翻了出來。據四川省林業廳網站5月8日的文章稱,這個事件發生于5月5日,要作為汶川地震的預兆未免太早了。實際上,在2006年、2007年的5月間,綿竹都發生過大規模的蟾蜍遷徙,而網上流傳的綿竹蟾蜍大搬家照片實際上是2008年5月9日在江蘇泰州拍的。汶川地震發生前后在福州、深圳,2007年5月在唐山、9月在臨沂,2005年7月在長春都曾經發生過蟾蜍的大遷移。當然,那些地方都沒有發生地震。
四川省人民政府網2008年5月9日發表的一則題為《阿壩州防震減災局成功平息地震誤傳事件》的報道也被翻了出來,作為事先已有人預知將要發生地震的證據。但是那則報道說得清清楚楚,是鄉干部在給村一級組織傳達全省地質災害防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精神時,由于方言口音的緣故,村民們把“地質災害”聽成了“地震災害”,從而導致了誤傳。這只能說是巧合,和地震預測毫無關系。
同樣巧合的是陜西師范大學旅游學院一名23歲的碩士生于2006年發表在一份名不見經傳的雜志《災害學》上的一篇論文。在對發生地震的年份做了一番等差數列的湊數游戲之后,作者得出結論稱“在2008年左右,川滇地區有可能發生≥6.7級的強烈地震”。這被許多人認為是準確預測了汶川地震。但是“川滇地區”這個范圍實在太大了,而且這個區域發生強烈地震的頻率又太高了,平均每年發生0.45次。那么,預言任何一年川滇地區將發生地震,就有45%的概率蒙對,何況用的還是不確定的“2008年左右”呢!
有一位自稱中國科學院工程地質力學重點實驗室工作人員的人(在該實驗室的人員名單中找不到此人的名字)在網上發帖聲稱,某位自稱曾經預報唐山地震的“國寶”曾在2008年4月30日向地震局發出密件做了準確預報,但沒有起到作用,事發后欲哭無淚云云。既然是“密件”,外人自然無從得知其真實性,但是地震局的兩位發言人都否認地震局收到過任何有關汶川地震的預報。
中國人之所以對地震局抱有厚望,是因為他們普遍相信地震可以被準確預報,而這種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1975年對海城地震的成功預報。在那次7.3級地震發生的前一天,小震增強,政府部門據此發出了預警。但是只有少數大地震會有前震,而小震通常并不導致大地震,所以這次成功預報只能說是一個偶然。據《美國地震學會會刊》2006年7月的一篇綜述分析,它是“混亂、經驗分析、直覺判斷和運氣的混合”。但是它卻讓中國人誤以為中國地震專家已掌握了地震預測技術,即使次年發生的唐山大地震也不是沒有被預測到,而是因為地震局失職乃至壓制“國寶”的預測。
國際地震學界的主流觀點
在日本以及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這些大地震頻發的地區,地震部門從來沒有發布過大地震預報,也從未因此受到指責。這兩個國家都是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重視地震預測的研究,地震學家也一度對此充滿了信心。但是后來發生的兩個尷尬事件使這個信心深受打擊。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地震學家相信在日本中部將很快會有一場8.0級左右的東海大地震。據地震學家估計,日本東海地區平均大約120年發生一次大地震,此時距上一次大地震(1854年)已過了120年,大地震的發生似乎迫在眉睫,日本政府也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嚴陣以待。但是東海大地震至今還沒有發生,卻在1995年出乎意料地發生了死傷慘重的神戶大地震。自那以后,越來越多的日本地震學家意識到想要對地震進行預測是不現實的,從而將他們的研究重點改為研究地震機理,而不是地震預測。
1979年,美國地質勘探局的研究人員注意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帕克菲爾德似乎很有規律地定期發生5.5級~6.0級地震,平均間隔時間大約是22年。此前最后一次地震發生于1966年,研究人員據此預測下一次地震應該發生于1988年左右。1985年4月,美國地質勘探局發布預測:在未來的五六年內帕克菲爾德將會發生一次大約6級的地震。地震學家認為他們終于等來了一個可以對地震進行全程監控的機會,帕克菲爾德布滿了各種各樣的儀器,100余名研究人員參與了這項“帕克菲爾德實驗”。然而,“該來”的地震卻沒有來。在這次被稱為“地震學滑鐵盧”的事件之后,美國的地震研究也轉向研究地震機理和對地震災害的評估。2004年9月28日,帕克菲爾德地震終于姍姍來遲。
1996年11月,“地震預測框架評估”國際會議在倫敦召開。與會者達成一個共識:地震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不僅現在沒法預測,將來也沒法預測。他們認為,地球處于自組織的臨界狀態,任何微小的地震都有可能演變成大地震。這種演變是高度敏感、非線性的,其初始條件不明,很難預測。如果要預測一個大地震,就需要精確地知道大范圍(而不僅僅是斷層附近)的物理狀況的所有細節,而這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想通過監控前兆來預測地震,也是不可行的。所謂地震前兆極其多樣,不同的地震往往都有不同的前兆,而且一般都是在地震發生后才“發現”有過前兆,缺乏客觀認定,既無定量的物理機制能把前兆與地震聯系起來,也無統計上的證據證明這些前兆真的與地震有關,多數甚至所有的地震前兆可能都是由于誤釋,令人懷疑地震前兆是否真的存在。
東京大學、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博洛尼亞大學的地震學家據此在1997年3月出版的美國《科學》雜志上聯合發表了題為《地震無法被預測》的論文,引發了一場爭論。1999年2月~4月,就地震能否預測這一問題,多位地震學家進行了辯論。但是辯論雙方的共識實際上多于分歧,雙方都同意:至少就已有的知識而言,要可靠而準確地對地震做出確定性預測是不可能的。
進入21世紀以后,這仍然是國際地震學界的主流觀點。美國地質勘探局明確表示,他們不預測地震,而只做長期概率預報,對地震災害做出評估。例如,2008年4月,美國地質勘探局評估說,在未來30年內加利福尼亞州發生6.7級以上地震的概率為99.7%,但是不能預測地震發生的具體地點和時間。“大師”愛預測地震
現代科學還做不到的事情,偽科學就會乘虛而入,而且不難找到市場。地震預測也是如此。“里氏震級”的發明人里克特在1977年曾評論說:“記者和一般公眾沖向任何有關地震預測的建議,就像豬沖向滿槽的豬食……地震預測為業余人士、狂人和欺世盜名的騙子提供了一個狩獵樂土。”
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國自稱能準確預測地震的“大師”、“國寶”人數之多,在世界上大概是首屈一指。而他們使用的地震預測術,也是五花八門:“太極序列”、“可公度法”、“旱震關系”、“地質信息有序性”、“天地耦合理論”、“磁暴月相二倍法”……這些人大多是退休科研人員或民間人士,他們的意見不受地震局的重視,據說是因為地震局在打壓他們;而他們在國際上也不被理睬,則只能歸咎于“西方科學對東方科學的偏見了”。
這些“大師”的能耐并不限于預測地震,他們聲稱用同樣方法也能準確預測洪水、特大暴雨、特大山體滑坡、煤礦瓦斯爆炸等突發性自然災害。他們一般也從事或支持任何和現代科學對著干的活動(例如:研究永動機、反對相對論、反對進化論、自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等等)。
但是他們的精確預測往往都是馬后炮,而事先公開發表的預測又往往說得很模糊,涉及的范圍太大,在地震帶發生的地震都可以被囊括進去,很容易讓人產生“說得很準”的錯覺,正如那篇發表在《災害學》上的論文。
由于“大師”太多,預測次數太頻繁,如果有人碰巧準確預測了某次大地震,也是毫不奇怪的。據地震局工作人員說,他們每年大概收到100余份預報卡,北京的大地震從1月1日~12月31日都有人在預報。那么,如果哪一天北京真的發生了大地震,肯定有人可以吹噓他曾經做過準確的預報。
所以,這類地震預測術就像算命術一樣,不能因為有人蒙對了一次就真把他當大師,而要具體統計其預測的成功率。驗證方法其實很簡單。這些“大師”的預測都是閉門造車,無須親臨地震發生地進行勘探,那么也應該可以預測其他國家發生的地震。世界上每年平均大約發生18次7.0級以上的大地震,地震預測“大師”何不對未來一年內將要在世界各地發生的這些大地震一一預測一下,讓我們看看能蒙對幾個?如果擔心預測中國的地震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防震減災法》,那么預測其他國家的地震應該是不犯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