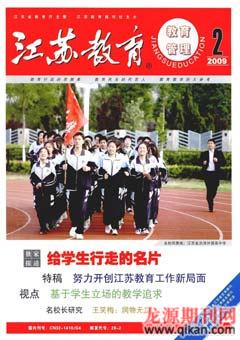保守性:不可或缺的教育“天性”
張 偉 秦德林
摘要:保守性是教育固有的天性,它是由教育所特有的文化性、教育所蘊涵的人本性中的向善性以及教育內在的公理(或規律)性決定的。然而,教育的保守性在現實中卻常常遭到尷尬和不幸。適度地堅守教育的保守性,須持有沉潛的心態,懷有古典的情懷,擁有哲學的理路。
關鍵詞:教育保守性天性堅守
2008年暑假,華東師范大學單中惠教授為我們通州市“名師之路”教育科研協會的老師講課,他展示了一百多年前國外學校教育教學活動場景(包括教室布置、上課、集會等)的一組照片。對比之下發現,它與我們當代學校教育教學活動場景有不少相似相同之處。這引發了我們的思考:時過境遷,教育在“變”的同時也有其“不變”的另一面;教育者有必要保持和堅守教育本身的一些“元素”。易言之,不管如何改革與超越,教育都還應當是教育,而不應當是其他什么。這或許就是教育的“保守性”。
其實,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看,教育既有其保守性,又有其超越性,是保守性與超越性的對立統一。但在關于教育的言論或理解中,人們往往過于強調教育的超越性,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乃至無視教育所固有的保守性。
一、保守性是教育固有的“天性”
“保守”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有兩個義項:①保持使之不丟失,如“保守秘密”。②維持原狀,不求改進,或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如“思想保守”、“計劃保守”。本文所言的“保守”,顯然是第一個義項。所謂教育的保守性,即指保持和堅守教育最原本、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元素和屬性,使之不再丟失,以確保教育仍然是教育。
最近翻閱張楚廷教授的《教育哲學》一書,他認為:“教育的保守性是人性在教育上的體現,人性是教育良心的來源,亦是其保守性的來源。”他進一步指出:“對于‘人本是怎樣的探討,使我們更加確信,教育保守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正是使人的本源不致喪失,教育所保守的是人的本性,也因此成為教育的天性。另一方面教育保守的是人類已創造的文明成果……”
關于教育的保守性,張教授主要是通過對“人本是怎樣”和“教育本是怎樣”的理性追問與哲學探討來進行闡釋和解讀的。除此之外,我們以為,至少還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明:
一是由教育所特有的文化性決定的。教育總是與文化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教育作為一種文化活動,是人類在運用已有的歷史文化培育和影響下一代,使已有的歷史文化得以傳承和保存,并發揚和壯大。在這里,“傳承和保存”是第一位的,“發揚和壯大”只是“傳承和保存”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和發展,是緊緊依附或依托于“傳承和保存”的。可以說,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保存”,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歷史文化的“發揚和壯大”,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教育。而“傳承與保存”則說明了教育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即保守性;它所要“保守”的,就是教育所特具的文化品質、文化品位和文化命脈。
二是由教育所蘊含的向善性決定的。教育的基本使命是使人成之為人或教人學會做人,讓人真正像“人”,是“人”。這里,“成之為人”和“學會做人”中的“人”,均指本源意義上的或價值理想中的“人”,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是兼具真善美于一身的人。人之善惡是由后天形成的,而教育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所蘊含的向善性,最主要的就是引領和影響人去求真、求善、求美。教育教人求真,并堅守其真,人就會走向善;教育教人求美,并堅守其美,人就會走向更高的善。從某種意義上說,教育的保守性,所要保持和堅守的就是教育的向善性,所要保持和堅守的就是人的真善美。
三是由教育所運行的規律性決定的。教育的發生、發展及其運行是有一定規律的。這種內在的規律性,反映了教育的本質和要求,揭示了教育活動許多本然的屬性,因此它在一定意義上是必須堅守的,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輕易改變或違反的。教育的內在規律性,可以通過教育公理來反映和體現。關于教育的公理,張楚廷教授認為有五條,即潛在公理、動因公理、反身公理、美學公理、中介公理。概括起來說就是:“人的潛在才智,以天賦欲望為引擎,通過自反心理作用,按照美追求并依美的規律,并不可避免地在一定中介的作用和影響下,來不斷發展自己,構造自己。”它們可以說概括了教育產生、發展及其運行的一般原理、原則和規律,堅守它,教育才能走向“自我的覺醒”。其堅守的過程,也即是秉持教育的“保守性”的過程。
二、教育保守性在現實中的境遇
保守性作為教育不可或缺的“天性”,在現實生活中,常常遭遇尷尬和不幸。還是以上述三個方面為例,其境遇大抵如下:
一是教育文化性遭遇輕慢和褻瀆。教育所傳承的文化常常具有其守恒性或不變性,它是經過千百年來人們的選擇和洗禮保存下來的,是人們確認和保留的重要的精神財富和精神遺產。但在現實中,總有一些人懷有一種不恭和輕慢的態度,將其隨意更改或“創新”。如《狐貍和烏鴉》的故事,這本是一則流傳已久的寓言,其寓意本來非常清楚,也很深刻、確鑿。可偏偏有人將其“別解”為“狐貍聰明”、“狐貍愛動腦筋”、“狐貍遇到困難能夠自己想辦法解決”,一個“貪婪狡詐”的“惡人”形象,就如此變成人們效仿的“榜樣”。這樣的“新說”、“新解”。實在是對教育本應固守的傳統文化的糟蹋和褻瀆。
二是教育向善性遭遇違拗和抵抗。教育的向善性,它所反映的是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種人的本性,它所代表的也是教育的一種本源性或循真性。循真性的教育應該是喚醒人們向善或鼓勵、引導人們向善的。可是在現實中,總有人將其舍棄或拋開,使教育所特有的價值引導功能有所黯淡乃至喪失。有些人一味強調教學的“效率”、“效益”,因此課堂教學只剩下“知識點”或“技能點”,什么學生的個性發展,個性中的向善性的增進和提高。統統被拋入不知所在的“爪哇國”里,由此,學生心目中也只剩下“黑色的競爭”和被扭曲的人生坐標。
三是教育規律性遭遇漠視和背離。在這方面,有些人的態度也是較為輕慢或隨意的。比如教育的動因公理表明,人有把潛在的才能和智慧表現和開發出來的欲望,并且這種欲望在幼兒身上就可以看到。可在現實中,不少人卻看不到兒童(學生)所具有的“把潛在的才能和智慧表現和開發出來”的欲望,其教育教學總是只憑自己的預設或“想當然”,讓教育對象只圍繞著自己認定的“框子”轉。
如此種種尷尬和不幸,確實令人深思和警醒。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尷尬和不幸”竟與教育中的某些改革與創新聯系在一起,或是直接出現在教育改革與創新的某一環節、某一過程之中,這就更需引起人們的思考和警覺。
三、適度堅持教育的保守性
對于教育的保守性問題,必須有一個科學的態度,重要的是努力做到適度、適宜、適切,為此我們有如下思考:
一是持有沉潛的心態。靜下心來,專心致志,教育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心態,對于教育的保守性問題,更需如此。教育自有其特定的文化內蘊,特定的本質屬性,特定的規律(公理),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好好地沉下去,靜下心來,用心去體悟和把握。只有把這一切都琢磨透了、把握準了,我們的教育才能清醒地行走在正確的軌道上,我們的改革與創新才能有方向、有根基、有底氣。教育關乎人的生命成長與發展,而生命成長與發展是不可逆轉和彌補的,教育可能成就人的一生。也可能毀掉人的一生。這就決定了教育改革與創新必須始終保持慎之又慎的態度,切不可貿然行事。這是一個“慢”的過程,也是應對教育保守性的一個真實、真切的過程。
二是懷有古典的情懷。教育需要一種古典的雅致、古典的淡定與從容,同時更需要對古典的文化、古典的傳統懷有一種謙恭和敬畏。“‘無古不成今,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今只是古的延續,不應當只是一個時間的概念。無論多么張揚的現代人,當他還想著自己是人的時候,對于古典,他會是十分謙恭的。無論教育多么強調現代化,它也應當是古典與現代的緊密結合。”這或許就是我們在處理應對教育保守性與懷有古典情懷之間關系時應有的態度。適度堅持教育的保守性,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敬重、敬畏我國乃至世界上優秀的古典教育文化、教育傳統,并使之發揚光大。任何教育改革與創新,都應該在此基礎上進行;任何教育改革與創新。都不能背離或褻瀆我國乃至世界上真正優秀的古典教育文化、教育傳統。
三是擁有哲學的理路。我們應對教育的保守性,首先需要的就是適度、適時、適切的堅守。當然,這種堅守決不是僵化的、機械的,在此同時必須擁有一種哲學的、思辨的理路和眼光。教育的保守性從來就是與教育的超越性相互對立與統一的。教育的保守性,突出的是對教育中原本的、最重要的元素和屬性的保持和堅守;而教育的超越性,則突出教育在“堅守”中的自我革新與進步。二者統一在促使教育持續的提升和發展上。因此,我們在強調教育的保守性時,一定要同時看到教育所具有的超越性;在推進教育的超越性時,也一定同時要注意到教育所具有的保守性。正確的態度是在堅守中創造,在堅守中前進,在創造與前進中永遠地堅守。只要我們擁有了一種哲學的、思辨的理路和眼光,并以此來正確對待和處理教育的保守性與超越性的關系,教育就一定會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人類也會由此變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