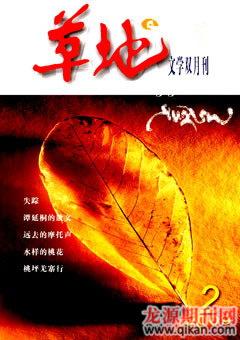失蹤
曉 鴻
1
就在我即將轉(zhuǎn)過村頭那叢酸酸果樹的當(dāng)兒,我扭頭瞥了一眼站在房頂?shù)母赣H,他正舉著左手不停地向我揮舞,在他身邊站著病懨懨的嫂子,身后是整天上躥下跳的瘦骨伶仃的侄兒。沒有母親的身影,從早晨我裝東西,上馬鞍開始,她就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間里,我到她房間道別時,她憂傷得連舉手的力氣都沒有,我真擔(dān)心要是哥哥真的回不來了,她會一輩子呆在自己的房間里不出來。
我們家里一共五姊妹,三女兩男。三個姐姐早在十年前就已遠(yuǎn)嫁他鄉(xiāng),只有我和哥哥還守在父母親身邊,眼巴巴等著家里的十畝地、二十頭牦牛落到自己頭上。大約六年前,哥哥娶了本村德伯家的長女格西措為妻,不到一年,生下現(xiàn)在這個侄兒。從此,哥哥便十分從容自信地開始打理起家里的土地和牦牛來了,我漸漸感到自己呆在家里的日子不會太久了。終于有一天,哥哥交給我一沓錢,很隱晦地叫我到三百多公里外的縣城做生意。我明白這是哥哥發(fā)出的打發(fā)我離開的信號,便接過錢,頭也不回地走了。要不是暢達(dá)的通訊工具通知我回家尋找失蹤多日的兄長,說不定這輩子我都不回這個家了。
穹瑪打著響鼻,還不停地咳嗽。這該死的老馬,年齡已經(jīng)二十多歲了。只要天氣稍有涼意,它就會患上一種我們稱為“哇嗆”的咳嗽病,每當(dāng)它咳嗽不止時,我們就得四處討要雞蛋為它治病。過去,我們這里還有人家喂雞,但后來發(fā)現(xiàn)喂雞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情。春天,雞們會跳到菜地里,將剛剛冒出頭的菜芽刨得漫天飛舞;入夜,黃鼠狼竄進(jìn)雞窩,被咬的和沒有被咬的都在雞舍里悲慘地嚎叫。叫聲在寂靜的深夜幾乎傳遍全村,人人都在這樣的夜里被吵得心神不定,以至于第二天個個都腫著雙眼,拖著步子昏昏沉沉地走路和干活。即使在大白天,雞們也照樣不能給村人帶來安寧,稍有疏忽,在空中盤旋或蹲在樹梢的鷹,就會箭一般的俯沖而下,猛地抓住其中的一只又風(fēng)一樣的回到天空,這個時候,往往地上就會出現(xiàn)這樣的場景:雞群在呱呱呱的慘叫聲里四散奔逃,人們邊跑邊舉著雙手在空中徒勞地?fù)]舞。在鄉(xiāng)下,讓人煩心的事本來就已經(jīng)夠多的了,村人當(dāng)然無法忍受雞群帶來的煩躁,不出所料,就在當(dāng)年正月十五跳完神后,雞徹底從我們的視野里消失了。
現(xiàn)在要找雞蛋,就只有到距離我們有半天路程的林場去買。那里有七八戶人家,過去他們扛著油鋸斧頭上山砍樹,現(xiàn)在卻拿著鋤頭鐵鍬遍山種樹,或帶著紅袖箍背著黃挎包四處巡山了。
他們的雞蛋買五毛錢一個,不算太貴,但不知何故,馬吃了林場買來的雞蛋后變得特別容易受驚。方圓一百公里以內(nèi)又沒有別的雞蛋可尋,顯然只有上縣城去買,不過人們粗略估算了一下,來回的車費(fèi)、住宿費(fèi)、伙食費(fèi),加起來總計超過兩百,而這些費(fèi)用的支出,只不過是因為一兩個小小的雞蛋。就讓馬忍受一下吧,說不定一兩天就會好起來的。父親和大伙不約而同的這樣想也這樣做了。
到了一處平緩的開闊地,穹瑪?shù)目人酝V沽耍粑岔槙沉嗽S多。要是這片開闊地的主人沒有變化的話,它的主人應(yīng)該由六家人組成,奇則的彭措,卡木梯的阿甲,奪洛的羅爾依,達(dá)加的茨仁洛伍,窮若的恩波,貢莎的昌旺。這片開闊地被這六家人種上了豌豆、青稞和麥子,看上去就像一塊補(bǔ)了綠布、黃布和青布的大毯子。
開闊地之后又是一段斜坡,穹瑪又開始咳嗽起來。我下了馬,牽著它走。后來,只要一遇到上坡,我就下馬牽著它走。有一天閑著無事,我屈指算了一下,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我牽著馬走的時間比騎著馬走的時間多一倍。
2
“烏云密布的天空下,一群大雁正在急急地往南飛。”這是六歲的侄女在她的作業(yè)本上寫的一句話。
那是某一年春末的一個午后,我給三姐送牛奶,看到被沉重的作業(yè)壓彎了腰的侄女,正坐在臨河的窗前絞盡腦汁地寫作文。她一邊抬頭望一下窗外一邊在腦中搜尋精美的詞語,這時候,一團(tuán)烏云正好掠過窗外那一抹平緩的山脊。我想,肯定是這團(tuán)烏云激起了侄女的聯(lián)想,她便寫下了上面那句話。可憐的侄女,由于全球氣候不斷變暖的原因,已沒有大雁再往南飛了,現(xiàn)在她只看得到滿天的烏云。
三姐曾是一家鞋楦廠的工人,五年前買斷工齡在河邊公園開了家小茶館,賣些泡茶、珍珠奶茶、甜茶什么的。我?guī)е业呐训饺慵胰?我經(jīng)常帶我的女友到三姐家),因為她白皙的皮膚,清秀的臉龐,加上那張可以把石頭都恭維活的甜嘴,頗受三姐的喜愛。她叫阿米初,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來自南方農(nóng)區(qū)的小女孩。
“阿米初!”還沒有看到三姐的影子,就可以聽到她發(fā)自廚房的聲音。往往這時候,阿米初就會朝我揚(yáng)一揚(yáng)她那兩道令我深惡痛絕的人工眉毛,得意洋洋地跑進(jìn)廚房。我在門廊里猶豫一會后,只好拐進(jìn)旁邊侄女的房間里去看她做作業(yè)。
今天,我和阿米初又到三姐家去,一路上,我對她的眉毛又一次表現(xiàn)出了我的厭惡,“好好的眉毛干嗎要把它修掉?年紀(jì)輕輕的完全可以不畫妝。”
阿米初仍和往常一樣不和我理論,她有她強(qiáng)有力的支持者——我的三姐。一到三姐那兒,不管我的理由有多么冠冕堂皇,都會在三姐刀一般的目光下煙消云散。
三姐是我們家的主心骨。多虧了現(xiàn)在便捷的通訊,家里一有什么風(fēng)吹草動,就可以打電話找三姐商量,終于有一天,姐夫按捺不住了,對三姐說:“我看你還是回老家去比較穩(wěn)當(dāng)。”
三姐看了她丈夫一眼:“要是丈夫能夠像一頭牛就好了。”姐夫不解地望著她,三姐把手機(jī)啪一聲合上,說:“只干活不說費(fèi)話。”據(jù)阿米初說,姐夫的臉氣得煞白。我想,要是以后阿米初也那樣說我的話,我也會非常生氣的。
今天,三姐破天荒沒有叫阿米初,而是招手讓我進(jìn)她的臥室。她目光里蕩漾著的焦慮讓我不知所措。
“我弟弟你哥哥一個星期沒有回家了。”
“總是到什么地方玩去了。”我把心放了下來,“每年這個季節(jié)他都要到北方草原賽馬喝酸奶。”
“不是,這次不是。”三姐搖著頭,“父親說最近老家偷牛盜馬十分厲害,他擔(dān)心弟弟的一去不歸和他們有關(guān)。”
“你說怎么辦?”我望著她。
“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現(xiàn)在我惟一的辦法就是讓你回去一趟,實在不行你恐怕還得上山去找他。”
“好吧,我去看看有沒有明天的車票。”
三姐默默地點(diǎn)點(diǎn)頭,轉(zhuǎn)身從衣柜里取出一件老羊皮袍遞給我:“阿米初我會照顧好的,你放心吧。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苦在等著你去吃,你千萬要挺住。”
從三姐家出來,我?guī)О⒚壮跞ゲ仫椀隇樗I了串松耳石項鏈。“我要出一段時間遠(yuǎn)門,我不在時,你就到三姐那兒住吧。”我說。
她把項鏈帶上脖子,歪著頭看了看我,“不會是和哪個死婆娘私奔吧?”
“目前除你以外還沒有找到可以與之私奔的婆娘。”我在她頭上吻了一下。她小鳥依人般靠著我。我倆就這樣相擁著穿過了那條長長的兩邊全是木椅子的步行街。
3
一想到侄女作文中的那一句話,我就有一種身在潮濕多風(fēng)的某一座大山隘口的感覺。現(xiàn)在,當(dāng)我騎著穹瑪行走在四周被松林環(huán)抱著的草原
時,頭上就堆起了濃濃的烏云。它們低低的懸垂在離我不到半米的天空,看上去就像一大團(tuán)浸在墨汁中的破棉絮。
這是一個興許會在轉(zhuǎn)眼間降下如柱暴雨,然后又在眨眼間落日溶金的黃昏時節(jié),這樣的場景曾被我無數(shù)次的在心中加以描繪:如血?dú)堦枴⒕К撀吨椤鳌⒀U裊炊煙、群群牛羊、朦朧雪峰、叢叢灌木、某一個自遠(yuǎn)方而來的騎馬挎槍的孤獨(dú)游俠……
我在自己描繪的場景里走了不到十分鐘,一頂黑色的牛毛帳篷出現(xiàn)在森林的邊緣。
剛跨過小溪,就清晰的聽到從帳篷方向傳來的藏獒憤怒的咆哮。聽聲音估計它至少有半歲牛犢那么大,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腰間的俄坤,要是那條藏獒撲上來,它會后悔一輩子的,我這樣想。俄坤在我手里會變成致命的武器,大約就在去年這個季節(jié),我和阿米初到草原收牛奶,兩條流浪的大獒圍住了我們,慌亂的阿米初居然一下子就躍上了我的脖子,緊夾的雙腿讓我差點(diǎn)喘不過氣來,但我還是從容地抽出俄坤,以一個不太標(biāo)準(zhǔn)的姿勢看似輕輕地一旋,兩只老獒連哼都沒來得及哼一聲就集體歸天了。要是你不相信,你完全可以到那個地方去打聽打聽,那里的人會告訴你,那是他們從未看到過的斗狗姿勢,一個男人扛著個女人居然沒費(fèi)吹灰之力就把兩條老獒洗白了。而兩眼昏花的老人至今還把我當(dāng)成是從天上下來的巨人。
今天這只藏獒算是有眼識珠,只站在原地憤怒地咆哮,根本沒有做百米沖刺的打算,我也出于禮貌,勒馬站在長滿了馬蹄葉的溪水邊,等待主人從帳篷里出來。
大約兩分鐘后,帳篷門簾被人掀開,從里面走出一個著粉紅色襯衣的姑娘。她站在門口四處瞭望。我吹了聲口哨。她把目光轉(zhuǎn)向我。
她把頭探進(jìn)帳篷,興許她和家人正在商量讓不讓我進(jìn)帳篷。片刻之后,她直起身子,朝我揮起手來。
“狗!”我朝帳篷旁邊蹦得老高的藏獒揚(yáng)了揚(yáng)下巴。
“哦。”她搖搖頭,走到我和藏獒之間。“沒事,她是拴著的。”她帶著一絲微笑。我明白她微笑的意思,因為我們這些來自山那邊的人,從沒在藏獒面前表現(xiàn)出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勇敢。
她幫我卸下鞍韉。我把馬拴在帳篷旁邊的木樁上。她過來替我松開轡頭。我回頭看了看,在夕陽下,我和她長長的影子,像一對奇怪的外星人,各自邁著足足占身子三分之二的雙腿,在潮濕泥濘的草地和稍遠(yuǎn)一點(diǎn)的帳篷之間來回走動。
帳篷門再一次掀開,一位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從里面走出來。
“都忙完了?”他的嗓音十分沙啞。至少這樣的嗓音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是的,爺爺,都忙完了。”粉紅色襯衣回答。
老人的目光轉(zhuǎn)向我。我朝他點(diǎn)了一下頭。
老人深褐色的臉上滿是灰白的毛發(fā),這些毛發(fā)讓我想起那些長在秋天巖石上的枯草,在這些枯草的后面,是一雙在夕陽下閃閃發(fā)亮的眼睛。
“做生意還是放牧?”他問我。
“都不是。”我回答道。
他疑惑不解的看著我。
“我在找一個人。”
“什么人?”
“我的兄長。”
“哦。”他朝地上啐了一口痰。“為什么要找他?”
我就把兄長何時不見、兄長至今不歸的原因以及我懷疑的對象告訴了他。當(dāng)我說完以后,我又有些后悔,因為我不知道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說出這些是否合適。
老人聽后沉默了一會兒。“是啊。”他說,“我們這里也從來沒有安寧過,十年時間,我們就有二十頭牛、五十多只羊成了他們的零花錢了。”
“你們見過我的兄長嗎?”我把兄長的身高相貌向他倆描述了一番。他倆一起搖著頭,讓我頗為失望。
一對老夫婦,加上一個小姑娘,這大概就是這頂帳篷里的所有成員。我不知道這位小女孩的父母去了哪里,我不便多問。
晚飯過后,小姑娘點(diǎn)上蠟燭,準(zhǔn)備帶我到外面的帆布帳篷里去睡覺。
“小伙子。”老人望著我,“我想了一晚上,有一件事我始終覺得應(yīng)該給你說。”
我拉著他的手,“是關(guān)于我兄長的事嗎?”
“是的。”他拍拍我的手說,“我聽說他在山上放了兩天牛后,便和那群牛一道消失了,奇怪的是你家的牛卻無一受損。”
“這事我也聽說了。”我泄氣地回答。
他用雙眼盯著我,火光在他的兩只眼珠里不停地跳躍,“我想說的是,你應(yīng)該懷疑你的兄長現(xiàn)在是不是正趕著鄉(xiāng)親們的牛群走向遙遠(yuǎn)的屠宰場呢。”
我感到血在往上涌。小姑娘走過來把我拉起來,“走吧。”她說。
我吃力地站起來。
“孩子,這些都是鬼老頭的一派胡言,你別放在心上。”在我走到帳篷門口時,老奶奶滿臉歉意地走過來對我說。
“沒事。”我說,“真的沒事。”
一彎新月高懸在天空,白帆布帳篷里被照得亮如白晝。
“你別放在心上。”小姑娘正試圖把一件長衫卷成枕頭。“爺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胡言亂語,你可千萬別當(dāng)真。”
“就像剛才我對你奶奶說的那樣,我真的沒事。”我說,“不過,我母親也一直擔(dān)心哥哥會做那樣的事。”
“我想也許不會的。”小姑娘抬頭望著我,“我有個妹妹在縣城打工,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找他。”
“好的。”我說,“她叫什么名字?”
“格桑。”她終于折好了枕頭,“這是干凈的,從沒有人穿過。”
“我不在乎。謝謝。”我說,“她啥時去的?”
“就在年初。”
“哦。”我艱難地脫下鞋子,里面早灌滿了黑乎乎的沼澤地里的水。“能告訴我你叫什么名字嗎?”
“倉旺措,不過喊我阿旺就是了。”
“好的,阿旺,明天早早把我叫醒行嗎?”
“好早?”她問我。
“雞不叫,狗不咬,烏鴉不穿褲子的時候。”
“好的。”她一邊笑一邊把一件寬大的老羊皮襖蓋在我身上。
4
晨曦微露,我就被阿旺從床上叫了起來。
帳篷門口拴著我的馬,不僅鞍子早已備好,而且連我的褡褳都放上了馬背。
一碗糌粑,三大碗奶茶下肚后,我翻身上馬,揮手向他們告別。
涉過小溪,穿過繁茂的杜鵑林,一道長長的山梁展現(xiàn)在我的眼前。
清晨的風(fēng)從后面的一叢灌木林里吹過來,抖落一路帶著青草和酥油花清香的串串露珠。數(shù)十只云雀懸停在太陽升起前的桔紅色的空中,啾啾的叫聲讓草原上的清晨顯得熱鬧非凡。穹瑪昂著頭輕快地穿行在密草叢中,咳嗽聲在這個清晨奇怪地消失了,仿佛它壓根兒就沒有患過“哇嗆”病。
太陽越升越高,露珠完全消失了,這時候的草原看上去顯得有些單調(diào)落寞。
已臨近中午,仍然沒有帳篷出現(xiàn)在我的視野里。拐過一處長滿了杉樹的山梁,杉樹林里滿是淡綠色的密密的松蘿。杉樹林邊有一塊突兀的巖石,看上去非常像一只高昂的鷹嘴,我下馬攀上“鷹嘴”,站在上面向四處瞭望。
在我左邊是一抹直抵天際的山梁,山梁背陰的地方,長著一簇一簇的冷杉林;在我前面,是一片無垠的草原,一條河流在上面畫了無數(shù)個“s”,就像一條藍(lán)色的巨蛇,在一張綠氈上蜿蜒而行;在我右邊,同樣是一抹長長的山脊,在山脊的后面,是一座座如犬牙—搬尖削的石山。
“我們該朝哪個方向走,伙計?”我掉頭問
穹瑪。
穹瑪輕輕抖抖鬃毛,默不作聲。
“你這白癡。”我罵了一句,然后仰面躺下,并拉下寬邊帽蓋在臉上。我這樣的睡姿,如果被遠(yuǎn)處巡邏的禿鷹看見,不出十分鐘,它們就會成群結(jié)隊地向我襲來。
曠野的風(fēng)從我身邊輕輕吹過。風(fēng)聲聽上去就像一群正在草叢中急步穿行的小動物的足音,或者一條緩流的小溪,甚至有點(diǎn)像淌過帳篷頂上的雨聲。這些聲音忽遠(yuǎn)忽近,忽高忽低地傳來,讓我在烈日當(dāng)空的中午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
5
穹瑪咴咴咴的嘶叫把我驚醒,我翻身坐了起來。
“你發(fā)什么神經(jīng)。”我沖它吼了一聲。
它圓睜著兩眼,鼻孔里呼呼地噴著粗氣,顯得十分興奮。
我四下里望了望,看到正前方一團(tuán)黑影正沿著小河朝這個方向緩慢地移動。
“走吧,伙計,我們到下面迎接他們。”
等我打馬下到前面的草灘時,可以看清楚那團(tuán)黑暗到底是什么了。這團(tuán)黑影由四個人和一群牛組成。四個人中一個人騎著馬,三個人步行。
但愿他們能夠給我一些有用的線索。我這樣想。我沒有下馬,而是趟過面前的河灘直接迎了上去。
到了看得清對方眉目的地方,發(fā)現(xiàn)騎馬的是我們村的壅忠,三個步行的人中有兩個人我認(rèn)識,一個是羅爾依,一個是恩波。
牛群大約有十五頭,有一大半是出生不到半年的牛犢。
“那些害人的,我累得都快要死了。”羅爾依拄著一根木棍從河對岸趟過來,氣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頭上的汗水順著他的長臉嘩嘩地往下淌,身上的褲子和衣服也完全被河水浸透了。“伙計們。我看這地方干燥,我們就在這兒燒茶!”他喘了一大口氣后,朝他們揮了揮手。
“那群該死的家伙,該死的茸真!”他一邊說一邊沉重地坐到地上,仿佛這一坐就打算永遠(yuǎn)也不起來了。“這該死的家伙。”他說,“他都讓我們傾家蕩產(chǎn)了。”
“盜牛賊?”我問。
“是啊,就是他。四天前他帶著兩個人搶走了我三十多頭牦牛,他們完全是搶的,三個人的槍全抵在我的后面。”他啐了一口痰,“媽的,其中一個還對我說,我們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喜歡喝白酒,喜歡下棋,心腸也不算太壞,否則,現(xiàn)在我們就可以送你上西天。”
他把淌著水的膠鞋脫下來倒扣在旁邊的矮樹上。“累死人了。”他說,“我想不通這些該死的小牛為什么那么喜歡灌木林,從昨天到今天,我們已數(shù)不清在灌木叢里鉆了多少個來回了。”
恩波是我小學(xué)同學(xué),他微笑著走過來遞給我一支煙,“羅爾依大叔請我們幫他趕牛,這不,都四天了,我們還沒有走到一半的路程,這么難趕的牛群,我不知道盜牛賊是怎樣把它們從我們那里趕出來的。”他說。
“他們有他們的辦法。”羅爾依說,“他們可以星夜兼程,一口氣把牛群趕到外省。”
我們在河邊找了三個比拳頭稍大一點(diǎn)的石英石,支成一個三腳爐。我們分別從自己褡褳里抓出一小把茶葉放進(jìn)茶壺,以此為標(biāo)志的草原上短暫相逢后的聚餐開始了。
“現(xiàn)在的盜牛賊比過去厲害。”那個我不認(rèn)識的人說,“他們有望遠(yuǎn)鏡,有手機(jī)。他們潛藏在山頂上,用望遠(yuǎn)鏡觀察我們的動向,一旦看出我們有離開牛群的跡象,他們就用手機(jī)通知待命的卡車到指定地點(diǎn)裝車。和他們相比,我們簡直就是聾子和瞎子。”
“他們其實人不多。據(jù)我所知,只有兩三人。”羅爾依說,“他們可以輕車熟路地把我們的牛趕走,我懷疑里面肯定有內(nèi)奸。”
“我也這么想來著。”壅忠說,“找到他我要把他碎尸萬段。”
“有國家法律,你想把他碎尸萬段是不可能的。”羅爾依對壅忠幼稚的話語不屑一顧,“我開始懷疑對方有內(nèi)奸是我在察西的那天晚上。當(dāng)晚十點(diǎn)鐘左右,我聽到有牛群奔涌的聲音,于是出門一看,借著星光看到有五、六十頭牛正在穿越前面的杜鵑林。我打了聲唿哨,牛群停下了腳步。這時候,我聽到有人沖我喊,這不是你的牛群,你不要攔我們的財路,否則今后你就沒好日子過了。他的聲音沙啞低沉,我知道他是捏著鼻子故意這么做的,怕我聽出他的聲音而露出他的馬腳來。當(dāng)時我手頭有一支火藥槍,我朝空中鳴了一槍,高聲對他們說,我不管這群牛是不是我的,但它們是這片土地上的牛群,所以,我有責(zé)任把它們留下來。那晚上我贏了,他們留下牛群走了。后來他們開始報復(fù)我,先是把我春天放牧的棚子一把火燒了,再就是用槍抵著我的后背,搶走了我三十多頭牦牛。”
“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他們更壞的人了。”那個我不認(rèn)識的人說。
“萬幸的是,他們還在途中給我遺下了這些火種。”羅爾依指指那群牛犢,“不過這些小家伙也讓我出了不少的錢。”
“出什么錢?”我疑惑不解地望著他,“這些不都是你的牛嗎?”
“是的,全都是我的牛。它們是在盜牛賊驅(qū)趕牛群的途中走散后,被沿途的住家戶拾到的。他們帶口信叫我去領(lǐng)牛,我去了,結(jié)果按每頭牛一百元的價格付了報酬他們才放我走。”
“真可惡。”我說。“你們知道我哥哥的事嗎?”
羅爾依環(huán)視了一下他的伙伴,“聽說好幾天沒有回家了,”他停了一下又說,“你這是去找他還是?”
“找他。但現(xiàn)在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我猶豫了一下,但還是說出了口,“他會不會趕著別人的牛到其他地方去呢?”
“誰知道呢。”羅爾依說,“現(xiàn)在的人變得太快了,誰敢保證自己在錢的面前會變成什么樣的人。”
6
從山谷后面刮來的席卷著紅柳枯葉的風(fēng),和著潺潺的溪流,在草原寂靜的午后顯得出人意料的喧嘩。這是一種讓人萎靡不振的喧嘩,在這樣的喧嘩聲中,我和穹瑪都低垂著腦袋,沿著草叢中若隱若現(xiàn)的小路緩緩前行。
我在這條狹長的小山谷里足足走了兩天,兩天里壓根兒沒看見帳篷,也沒見到人跡,只偶爾碰見一些放生牛羊和大片牲畜零亂的腳印。
第三天,我在一處河灣的石灘上生起了火。天氣不是很好,薄霧像一層輕紗圍繞在我的四周,夾雜在其中的霏霏細(xì)雨,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里,就在我的頭發(fā)和眉毛上結(jié)成了成千上萬顆晶瑩剔透的小露珠。
我到旁邊的紅柳樹下找了一些稍顯干燥的枯樹枝,回到火邊的時候,穹瑪抬起頭很響亮地叫了一聲,并同時朝我們的左邊望去。我順著那個方向望過去,朦朦朧朧看見一個騎馬的人朝我走來。
那人涉過河流,徑直走到火邊才下馬。他穿一身過膝的牛毛長衫,腳上是一雙土黃色的長筒雨靴。
“大老遠(yuǎn)我就嗅到你身上的臭氣。”他摘下滿是油污的寬邊呢帽,啪啪地抽打著身子上的露珠。
“你鼻子真夠靈的。”
“那是當(dāng)然,要不,別人怎么會叫我尕足尕爾恰呢。”他嘿嘿地笑著。
“你果真是尕足尕爾恰,那只臭名昭著的狐貍?”我仔細(xì)看了看他,零亂的頭發(fā)下面,果然是過去那雙狡黠的眼睛。“你終于從那里面出來了?”我說。
“是啊。”他蹲下來把手伸到火上。
“在里面有十年了吧?”
“差三天十年。”
“我聽說十年前有人借宿別人家中,結(jié)果把母女倆給干了,這件事不會是第二只狐貍做的吧?”我目不轉(zhuǎn)睛地盯著他。
他眼中剛?cè)紵饋淼幕鹈琪龅讼氯ァK麚u著頭說:“當(dāng)時我還以為遇上了一個好客的人家,后來才知道那是陷阱,母女倆邀來了很多的人,我們喝了一個通宵的酒,結(jié)果我醉了,醉得連舉手指頭的力氣都沒有了。第二天我被連續(xù)晃動著的東西搖醒,才知道自己闖了禍已被送上了警車,而我白天買牛得來的三萬塊錢一分也沒有給我剩。”
“你的意思好像你是被冤枉的?”
“我也說不清,盡管我因這事受到了懲罰,但直到現(xiàn)在我都不清楚我到底做沒做那樣的壞事。”
我一時也不知說什么好,沉默了一會兒,我問他:“你想喝點(diǎn)什么?”
“茶、酒?看在老天的份上,你有什么東西可以讓我潤潤嗓子?”
“對不起,我只有茶。”
“那當(dāng)然更好。”他點(diǎn)著頭說,“酒,我已經(jīng)戒了十年了。”
我們都一言不發(fā)地喝茶,直到太陽從云層后面鉆出來。他問我到什么地方,我說找哥哥,但現(xiàn)在還沒有線索。他建議我到西北方的小鎮(zhèn)去,因為那里是大地的十字路口,眾多南來北往的人會帶來令人意想不到的信息。
“那么你呢?”我問。
“我也打算到那個小鎮(zhèn)去,這么多年了,那里要騸的牲畜估計都可以裝幾卡車了。”他哈哈地大笑,好像這世界上除了他就沒有別的騸匠了。
“你這斷子絕孫的活計準(zhǔn)備啥時歇手?”
“在里面我就想過歇手,但出來后才發(fā)現(xiàn)還不到時候,母親和兄長都以我為恥,根本不讓我進(jìn)家門。”
7
從西邊傳來了沉悶的雷聲。
“得趕快找一個避雨的地方。”尕足尕爾恰一邊說一邊用雙眼在四下里尋找可以避雨的地方。
除了光禿禿的草地,周圍連一塊高過人頭的巖石都沒有。我掉頭朝西邊望去,看到那個方向的山脊上層疊著厚厚的雷雨云。
“也許還來得及,它們離這里大概還有個把小時的路程。”我說。
“也許吧。不過還是快一點(diǎn)為好,看在老天的份上。”尕足尕爾恰說完,雙腿一夾,飛馬疾馳起來。
大約半個小時后,出現(xiàn)了數(shù)十頭牦牛,接著越來越多,幾乎黑壓壓的一片。讓我們高興的是,在靠右的山洼里,出現(xiàn)了一白一黑兩頂帳篷,其中一頂黑牛毛帳篷還冒著炊煙。
就在我們低頭鉆進(jìn)帳篷的一剎那,豆大的雨點(diǎn)鋪天蓋地地落了下來。
帳篷里坐著三位老人,他們安詳?shù)貒跍嘏臓t火邊,手拿佛珠和經(jīng)筒輕聲誦經(jīng)。在隆隆的雷聲和嘩嘩的雨聲里,他們的存在讓人倍感溫馨。
主人是一個年紀(jì)大約在五十或六十歲之間的高大男子,他有一雙令人過目難忘的滾圓的眼睛,顯然他是一位熱情好客的人,因為他幾乎沒有問我們從何而來,便用他那厚實寬大的右手取出兩只瓷碗遞給妻子。
“走南闖北久了,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尕足尕爾恰低聲告訴我。這自作聰明的家伙。
奶茶清香怡人,顯然是用新奶做的。
“你們看見我的牛群了?”
“看見了,在離這兒大概十分鐘的路程。”尕足尕爾恰回身指著我倆來時的方向。
主人點(diǎn)點(diǎn)頭,“我現(xiàn)在人手不夠,時常有牛羊走失或被盜。這讓我整天愁眉不展。”
我朝尕足尕爾恰使使眼色,他會心地一笑,“大叔,你想沒想過雇一個人幫幫忙什么的?”
“想過,但他們要的工錢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我的能力。”
“雇他吧,你一定不后悔,他是一只價廉物美的騷公羊。”我說。
“真是這樣?”主人用有些不相信的眼光看著尕足尕爾恰。,
“是這樣的。”尕足尕爾恰說。“我只要管吃管住,然后再有一點(diǎn)零花錢就行了。”
“這沒問題。”主人略一思索,隨后雙手一拍,“好吧,就這樣!”
“這下讓央可以騰出手掙點(diǎn)別的錢了。”三位老人中的一位說。“幾年來這百把頭牛把你拖得夠嗆的了。”
“沒事的,爸爸,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的。”主人說,“如果諸事順利,明年我就可以帶您到拉薩去了。”
“謝謝,我的孩子。”老人摘下帽子,露出一頭雪白的頭發(fā)。
外面的雨聲越來越密,雷聲越來越響亮。有一陣,我們根本聽不清對方在說什么,只能靠雙手像聾啞人那樣相互交流。
女主人出去了一會兒,接著慌慌張張地跑進(jìn)來。
“讓央,好像有人在趕我們的牛。”她說。
讓央急忙站起來,從帳篷的角落里抓起一把火藥槍,快步走出帳篷。我和尕足尕爾恰也跟了出去。
透過朦朧的雨幕,我們看到讓央的牛群像牽了線似的穿過南坡那片矮小的小葉杜鵑林。很明顯,有人在后面驅(qū)趕著牛群。
讓央朝空中鳴了一槍,并高聲警告。
對方也在開槍,有一兩發(fā)子彈呼嘯著從我們頭頂擦過,他們一定是朝著我們的方向在開槍。
“躲在柴垛后面。”讓央說。我們都蹲到了柴垛的后面。
“好像是四個人。”尕足尕爾恰在一根圓木的后面探出了半個腦袋。
“這幫狗娘養(yǎng)的是從哪兒鉆出來的?”讓央疑惑不解,“他們的武器還真不一般。”
“為什么?”我問。
“他們有一支步槍、兩支小口徑運(yùn)動步槍、一支單筒獵槍。”讓央停了一會兒,接著說,“好像還有一支五十四手槍。”
“你怎么知道?”尕足尕爾恰說,“你不會都看見了吧?”
“聽出來的。”讓央告訴他,“我當(dāng)了六年的兵,幾乎所有的槍我都能憑聲音判斷出它們的型號。”
“不簡單,這簡直就是神話。”尕足尕爾恰不失時機(jī)地奉承起他的新主人來。
“也許還有別的槍他們還沒有用呢。”我說。
“也許。”讓央若有所思地回答說。抬頭看了看那幫人已經(jīng)走遠(yuǎn),便騎上馬朝牛群方向走去。
尕足尕爾恰猶豫了一下,隨后也騎上馬追了上去。
晚飯時,讓央遞給尕足尕爾恰一條鞭子,“我的眼睛從沒騙過我,你今天的舉動讓我相信你是一個誠實的人,你的雇期就從今天算起。”
尕足尕爾恰接過鞭子,朝我笑笑,“我的活計可以息手了,看在老天的份上。”他說。
“是的。”我說,“所有的母牛都會因此感激不盡的。”
他搖搖頭,最后把目光定在了飄忽不定的爐火上。
8
尕足尕爾恰慵懶的站在帳篷門口。
“我有一個家了。”他一個勁地朝我笑,“別忘了我請你帶的口信。”
“放心。”我翻身上馬,朝尕足尕爾恰和讓央一家揮手道別。
我沿著讓央告訴我的小路走向小鎮(zhèn)。這是一條在草叢、冰磧石和紅柳林中忽隱忽現(xiàn)的冬場小路,我很難想象在小路另一頭的繁華和喧囂到底是什么樣子。
這兒是群山起伏的高原,時值夏季,綠茵如氈,山上點(diǎn)綴著杜鵑叢。
翻過一道小山脊,前面就是直抵天際的大草原。草原中央,有一團(tuán)閃爍著銀灰色光芒的建筑群,我估計那就是我要去的小鎮(zhèn)。
經(jīng)過冗長的夏日旅行,大約三天后,我終于抵達(dá)小鎮(zhèn),那個有可能讓我找到哥哥的希望小鎮(zhèn)。
我隨一群騎馬的牧民走進(jìn)小鎮(zhèn)。一排低矮陳舊的磚木結(jié)構(gòu)的建筑進(jìn)入我的視野,在這些建筑物的墻上,還依稀可見當(dāng)年用朱紅色的宋體字寫的最高指示。一條泛著白光的土路在建筑物的面前漸漸變寬,直到最后在鎮(zhèn)中心附近變成了寬敞的水泥路。一群流浪狗吐著長舌,在炎炎夏日里
為一些失落在街頭的餅干或者骨頭吵鬧不休,以至于像我這樣的陌生人從它們身邊走過時,它們都無暇顧及。偶有一團(tuán)小小的旋風(fēng)突然出現(xiàn)在路邊,裹挾著它能夠帶走的所有小東西,但還沒到路中央,它就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在你還沒回過神來時,它又在稍遠(yuǎn)的小河邊,正卷著積雪在結(jié)冰的河面上來回游走。由于它的神出鬼沒,當(dāng)?shù)厝耸冀K把它看成是神靈和鬼怪的化身。
牧民們在一家看上去有點(diǎn)像超市的地方下了馬,我繼續(xù)往前走,一直走到一家叫做香格里拉的茶樓門口才停下來。
正像讓央所描述的那樣,這是一座只有五層樓的小樓房,茶樓在二樓向陽的南邊,巨大的白底紅字的招牌幾乎占據(jù)了整個樓的三分之二。
我在背陰的地方把馬拴在一根木樁上,整了整衣著,讓自己盡可能看上去像一位本地人。
那是一個大房子,十多張桌子全被黑壓壓的人群占據(jù)著。每張桌子上的每一個人都在斗地主,笑聲、罵聲、煙氣、面味、炒飯味幾乎讓我止步不前。但我還是硬著頭皮走進(jìn)去,在墻角處的一個空位上坐下。半晌,一位小姑娘走過來問我喝什么,我隨便朝茶單上一指,“就這個。”我說。“好的,請您稍等。”小姑娘躬身退了回去。
也許天下的茶樓都是一模一樣的,至少在這里,我想。中間是大廳,兩邊是雅間,大廳里是沒有身份地位的人在那里玩牌聊天,雅間里通常是那些有錢的人在里面一邊打麻將一邊密談。白天茶樓,晚飯飯館,深夜茶樓。這幾乎成了大部分城里人的生活軌跡。“但愿我要的線索不在雅間。”我說。
我環(huán)顧四圍,突然有兩個人的神態(tài)引起了我的興趣。一個是矮小的胖子,一個是尖下巴的高個子,我們之間是一桌正在大呼小叫興奮地斗著地主的五個青年男女。他倆隔著桌子用一種異樣的眼神不停地朝我張望。
“我有什么不對嗎?”我用眼角瞟了一下自己,沒看出異樣。
“也許他們看出我不是本地人,這沒什么大不了的。”我這樣想,并摸了摸腰間的俄坤。我摸腰間的俄坤就像美國西部牛仔摸自己腰間的槍一樣讓人心里塌實。
我并沒有把目光移到別處,而是緊緊地看著他們。他們猶豫了片刻,最終把目光移開了。他倆在一個勁地說話,我仿佛聽到其中一個提到了扎洛這個名字。我突然激動起來。我和哥哥是除了雙胞胎之外長得最像的兄弟,難道他們……
小姑娘端著我要的東西走過來,“這是你要的鮮榨西瓜汁。”她把一個盛滿了紅東西的杯子放到桌上。杯子之高,足有一尺。“鮮榨西瓜汁?是我點(diǎn)的嗎?”我有些哭笑不得,我怎么隨手要了一杯只有娘兒們才喝的東西。
小姑娘準(zhǔn)備轉(zhuǎn)身離開,我叫住了她。“有什么事需要我?guī)兔?”她躬身問我。
“真是一臺機(jī)器人。”我心里說。我招手示意她靠近一點(diǎn)。她有些遲疑,但還是走過來把頭伸向我。
“我想問你一件事。”我說。
“什么事?”
“知不知道你背對著的那兩個人是從什么地方來的?”
她回頭看了一下,“不知道,我從沒見過他們。”她說。“你不是本地人?”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她搖搖頭,“你打哪兒來?”
“察西爾。”
“察西爾?我是加戈瑪?shù)模覀兪青従印!彼f。
“是的,盡管中間隔了一座山。”我笑著說,“你們住在哪條溝?”
“斯達(dá)納,就是盡頭有一大片石灘的那個。那條溝里只有我們一家。”,,
我想了想。“我猜你肯定就是那個格桑了?”
“格桑?你怎么知道我是格桑?”
“阿旺說的。”
“是這樣。”她點(diǎn)點(diǎn)頭,“你去了我家?”
“是的。”我說,“你姐姐告訴我你在縣城,可你怎么在這兒?”
“我和老板鬧翻了。”
“扣你工資?”
“不是。”她說,“他冤枉我,說我偷了店里的飲料。”
“你沒偷?”
“你不信?”
“我沒說不信。”
“我想也是。”她說,“我要過去了。”
“你得幫我打聽一下那兩人是從哪兒來的,如果可以的話順便再問問他們?yōu)槭裁匆菢涌粗摇!?/p>
“我想一定是他們覺得你很酷罷。”她說。
“別開玩笑,把人笑死是要償命的。”
她見我一本正經(jīng)的樣子,強(qiáng)忍住笑轉(zhuǎn)身跑了過去。
他倆不時地朝我這里看上一眼。我站起來裝著上洗手間的樣子。我用余光瞟著他們,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的目光一直追隨著我。
我在洗手間里呆了一會兒,出來時發(fā)現(xiàn)那里的座位已經(jīng)空了,他倆是離開了嗎?
我在這方面沒有絲毫的經(jīng)驗,我該怎么辦?我是該尾隨他倆還是另尋它路?我是不是有點(diǎn)神經(jīng)過敏了?
我苦惱地喝著那該死的鮮榨西瓜汁,格桑走了過來。“我?guī)湍愦蚵牭搅恕!彼贿吥ㄗ雷右贿呎f,“他倆來自北邊的茸隆牧場。”
“打聽到他們是干啥的了嗎?”
格桑點(diǎn)點(diǎn)頭。她告訴我,他們替別人趕牛,兩周前,他們和其他人從北方趕了一大群牛到南方,途經(jīng)小鎮(zhèn)的時候,還在小店里買了幾十瓶酒,“肯定有什么值得慶祝的。”她說。
“也許是的。”我說,“我在找我的哥哥,他長得和我一模一樣,你見過他嗎?”
“沒有。”她搖著頭,“好啦,我得過去了,要是讓老板看見非得把我開了不可。”
“好的。”我把錢遞給她,“順便幫我把單給買了,這樣老板也就無話可說了。”
她會心地朝我一笑。很明顯,從她明亮的眸子里可以看出,她是一位熱心腸的好姑娘。
9
我走出茶樓,在小鎮(zhèn)的陽光下站了一會兒,隨后騎上馬到小店里補(bǔ)充了些茶葉、鹽、面粉和蔬菜。
是的,我已經(jīng)打定主意獨(dú)自跟蹤茸隆牧場的那兩個人了。
第二天,我在路邊一群曬太陽的老人那兒知道了他倆的去向,他倆一個騎著青馬,一個騎著黑馬,朝著北方去了。
我循著兩人的足跡一路向北,天氣晴朗,無風(fēng)無雨,特別適合跟蹤。
兩天后,在一叢矮樹叢邊,我發(fā)現(xiàn)兩人在此分道揚(yáng)鑣。我下了馬,研究著地上的馬蹄印,一個向北,一個向西。到北方的也許是回到茸隆牧場,而向西的去干嘛呢,由此向西不足百里就是外省了。
我決定碰碰運(yùn)氣,跟上了那個向西的蹄印。
越往西走周圍變得越荒涼,漸漸的青青的牧草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紅柳包和陣陣沙塵。我鬧不明白,他為什么要到這樣荒涼貧瘠的地方。也許他知道我會跟蹤他,所以把我?guī)У竭@里,然后設(shè)下圈套,讓我自投羅網(wǎng)?我不敢肯定其中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有多少僅僅只是我的幻想,它們對我尋找兄長究竟有沒有用?
多少讓我放心的是,直到現(xiàn)在,對方仍然還是一個人。一天黃昏,我終于決定動手,因為他就在山下的沖谷盡頭露營了,而且我發(fā)現(xiàn),越往前走,地形就越復(fù)雜。
天黑前,我站在山谷上面(如果那也叫山谷的話),確定了自己的進(jìn)攻路線。我把穹瑪拴在遠(yuǎn)處的杜鵑林里,以防它的咳嗽驚動了那個人。入夜,我悄悄地沿著沖谷的邊沿摸了過去。
是那個矮小的胖子,他在一處背風(fēng)的洼地里生了一堆火,正若有所思地坐在火堆旁邊的馬氈上,手里拿著的瓷碗里冒著熱氣。
我手里提著俄坤從火光外的黑暗里走出來,
他看到我后暗暗一驚。
“坐在原地別動。”我說,“這樣我們還可以好好談?wù)劇!?/p>
“你要做什么?”那個在茶樓上不斷打量著我的人問道。
“向你打聽一件事。”我站在火堆的另一邊,“干嗎在茶樓上老盯著我?還有,你怎么和你的伙計分手了?你到西邊干嗎?”
“這不關(guān)你的事。”他說,他的態(tài)度很不友好,而且可以看出他隨時都在尋找拿槍的機(jī)會。我看到在他用來做枕頭的馬鞍下面,一只長槍的槍托露在外面。
“是不關(guān)我的事。”我說,“當(dāng)初要是能夠把讓央的牛群趕走,也許你就不會在這兒,對吧?”
他臉上掠過一絲不安,隨即右手慢慢地移向馬鞍。我右臂一揮,俄坤挾著火光向他飛去。他大叫一聲,痛苦地捂著被擊中的右手。
“我希望我倆能夠愉快地交談,而不是現(xiàn)在這樣。”我說,走過去把他的槍抽了出來。一把松鼠牌單筒獵槍。
“看到你讓我想起了一個人。”他輕聲呻吟著,兩眼緊緊盯著我手中的獵槍,“我們六個人在山那邊偷了一群牛,大約有五十多頭,我們趕著牛剛翻過那座山梁,那個和你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就追了上來。他很固執(zhí),我們多次鳴槍讓他退后,他都充耳不聞,后來我們終于忍不住了,在一處松林里設(shè)下埋伏并擒住了他。也許他是個軟蛋,也許是條漢子,誰知道呢,總之我們抓住他以后,他表現(xiàn)得很平靜,很順從地跟我們走了。”
后來他們帶著他一路北行,并決定把他帶到南方買給煤礦的私人老板。只是隨后發(fā)生的事打亂了他們的計劃,一天晚上,他們把從小鎮(zhèn)買來的幾十瓶酒喝了個底朝天,然后借著酒興開始爭論,每個人都認(rèn)為自己才是最強(qiáng)的,直到后半夜還沒爭出個結(jié)果,情急之下,居然有人給110打了電話請警察來評判,結(jié)果一伙人被警察帶走了。
“真要把我笑死了。”我說,“你怎么沒有被帶走?”
“幸運(yùn)的是我沒有和他們一塊喝酒,我只是在睡覺,在離他們很遠(yuǎn)的林子里。”
“那個被你們抓住的人怎么樣了?”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么樣了,我看見遠(yuǎn)處的警車我就逃走了。”
“知道他名字嗎?”
“好像叫扎洛。”他抬頭看了看我,“你們不會是兄弟吧?”
我點(diǎn)點(diǎn)頭。“你那伙計怎么沒和你一塊兒來?”
“現(xiàn)在奪科不干了。”沉默了一會兒,他沮喪地說,“現(xiàn)在他和我分手了,那晚跑出來后他還雄心勃勃的。”
“那個尖下巴的高個子?”
“是的。”他說,“我們把我的表弟叫上,還到外省買了一些槍支,只是幾次出馬連根牛毛都沒撈著。現(xiàn)在這樁生意不好做了,家家戶戶都和政府簽訂了合同,我們一動彈就有一張網(wǎng)向你罩來。都是那件事惹的禍。”
“你還向西去,為什么?”
“那地方還沒人簽合同,也沒多少人管,而且還聽說那地方的人不怎么團(tuán)結(jié),我準(zhǔn)備到那里碰碰運(yùn)氣。”
“你怎么不到東邊?”
“東邊?”他咽了一下口水,“那是地獄,那地方的人太可怕了,他們抓住盜牛賊后也不報案,而是私下里用刑,你說那樣的地方誰還敢去?”
第二天,我?guī)е下罚R近中午,在一處長滿了紅柳的地方,突然從樹叢里飛出幾只山雞,它們呱呱呱地大叫著飛上半空。我們的馬蹦跳起來,胖子在我的眼角一頭栽到地上。當(dāng)我終于控制住受驚的馬,發(fā)現(xiàn)胖子仍躺在地上。我下馬走上前去,見他雙眼緊閉,嘴里氣若游絲。我迅速下馬,用手捧住他的腦袋,雙膝抵在他的肩上,用力一提,隨著一聲輕響,胖子吐出一口氣來。
“你差點(diǎn)到那邊報到去了。”我說。
“媽的,這該死的馬,自從離開了以前的主人,不知把我摔了多少回。”他揉著脖子踉踉蹌蹌?wù)酒饋怼?/p>
在小鎮(zhèn),我把他交給了一位正在巡邏的警察,并順便問了問那天晚上抓獲的人中有沒有一個叫扎洛的人,他們說已經(jīng)移交到縣上了,讓我自個兒問問他們。我在街邊找了個電話向那邊的警察詢問,他們說沒有這個人。
看來又得從頭做起了,我想。我走進(jìn)香格里拉茶樓,格桑迎了過來。
“今天不會再喝西瓜汁了吧?”她說。
“不會。”我笑著搖搖頭,“來一杯素茶就行了。”
“好的。”她說。
我找了個臨窗的座位坐下。幾分鐘后,格桑端著托盤走來。
“找著你哥哥了嗎?”她把茶杯輕輕放到桌子上。
“沒有。”我說。
“哦,真遺憾。”她嘆了口氣。
“不過,很快了。”我朝她點(diǎn)點(diǎn)頭。
她朝我笑了笑,“慢慢喝。”她說。
陽光穿過窗玻璃照在我身上,我一邊喝茶一邊享受著高原陽光的撫摸。在這里,可以望見廣袤的曠野,曠野盡頭連綿起伏的雪山。
路上沒有多少行人,在樓房拐角的地方,照例坐著一群曬太陽的老人。這時候,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xiàn)在我的視野里。他騎著馬,匆匆穿過街道,然后從那群老人的身邊打馬走了過去。我吃了一驚,是那個矮小的胖子。很顯然,他們把他給放了。
10
我決定先住下來,打聽消息。
我付了茶錢,我問格桑附近有沒有干凈便宜的旅店。
“有。”她說,“出門向右拐,離這大約五百米遠(yuǎn)的街口有一個小店,許多做小生意的人都住那,后院還可以拴馬。”
旅店是一座只有三層樓的小樓房,一位上了年紀(jì)的婦女坐在總臺看電視。
“有房間嗎?”
“有,你要多少錢的?”她目不轉(zhuǎn)睛地盯看著電視屏幕。
我看了看貼在墻上的價目表,“那就要一間五十的吧。”
“最近客人多,你不介意在你房間里安別的客人吧?”
“不會。”我說。
她把開好的票遞給我,“上面有服務(wù)員,你讓她開門吧。”她的兩眼始終沒有離開過電視屏幕,那是一部冗長得讓人昏昏欲睡的韓劇,此時,我相信這個小鎮(zhèn)上幾乎所有的婦女都坐在電視機(jī)前或哭或笑。
放好東西拴好馬,太陽開始慢慢西沉。街上響起了雜亂的馬蹄聲,那是一些附近牧場開始?xì)w家的牧民。
我在這些雜亂的馬蹄聲里走進(jìn)一家小飯店。那里,有一大碗香噴噴的牛肉面塊、一壺濃濃的奶茶在召喚著我。
當(dāng)我吃飽喝足回到房間,夜幕已爬上了窗戶。和夜幕一同到來的,還有一位身材頎偉的中年男子。
他坐在床頭,目光陰郁地看了我一眼。
他叫昔扎,是來報案的。昨天,他的六十七頭牛被盜了。
“肯定是茸真那伙人干的。”
“茸真?那個盜牛賊?”
“是的。確切地說,是一個殺人犯。那個天殺的。”他說,“他曾經(jīng)是個有工作的,因為偷雞摸狗進(jìn)了班房,出來后仍惡習(xí)不改,最終被單位開除了,四年前回到村子后不久就干起了偷牛盜馬的勾當(dāng)。他是一個孤兒,偷牛盜馬的事顯然需要人手,因此每一次出去他就帶上一兩個人,現(xiàn)在弄得村上所有的年輕人都成了他的幫兇。”
他停了一下,繼續(xù)說:“幾周前他就騷擾過我們,他帶著手下人,大白天撞進(jìn)我們的牛棚子,用槍逼著我們弄吃的,還揚(yáng)言要報復(fù)所有攔他財路的人。”
“這么長時間就沒有人抓他??
“警察去了幾次都沒抓著,村里人袒護(hù)著他,因為自己的子女。”
“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
“先前那伙人都被警察抓走了,除了他還會
是誰呢?”
他和衣躺在床上,兩眼直勾勾地望著天花板,仿佛可以從那里盯看出他的牛群來。
第二天天不亮他就離開了。五點(diǎn)過十分,我看見紅紅的陽光鋪灑在窗戶外面的山坡上,我翻身起床,正準(zhǔn)備洗臉,這時候,響起了一陣急促地敲門聲。
我打開門,是茶樓上的格桑。她裹著一條鮮艷的圍巾。
“真是太好了。”她徑直走進(jìn)房間,“一路上我就擔(dān)心你會不會天不亮就走了。”
“沒有。”我有些詫異,“你這是?”
“我聽到一個消息,也許是你哥哥的。”
“什么樣的消息?”
“昨晚有三個人到茶樓喝茶,我聽見他們在談?wù)撘粋€人被盜牛賊抓走的事。”
“那個盜牛賊是誰?”
“他們沒說。”她搖搖頭,“不過他們提到了一個村子的名字,那個村子我知道,在小鎮(zhèn)西北方大約五十公里的地方。”
“看來我得動身了,不管那人是不是我哥哥。”我說。
“我也這么想。”她說。
我突然有了一個主意,“你能不能借點(diǎn)錢給我?”我問她。
“多少?”
“兩千塊,我身上沒多少現(xiàn)錢了,再說,在這里我認(rèn)識的人也只有你。”
“我得回茶樓去拿。”
“我在茶樓下面等你?”我說。
她點(diǎn)點(diǎn)頭,轉(zhuǎn)身走了出去。
我用她借給我的錢買了一斤半貝母、一副墨鏡、一件襯衣和一根領(lǐng)帶,隨后把自己裝扮成了一個在這個季節(jié)隨處都可以看見的藥材商。
11
夏日炎炎的中午,空氣中滿是牧草被烈日炙烤后散發(fā)出的刺鼻的怪味,四周籠罩著一層淡淡的藍(lán)色煙霧。
我走過一片積水的草地,然后在一處紅柳樹旁邊拐上山坡。
山坡呈倒“V”字形向上延伸。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沿著山坡上面平坦的山脊一直向東北走三天左右,就可以抵達(dá)讓央的牧場。
在山脊中央,我遇見了一座湖,它停泊在一處足有兩個足球場那么大的山洼里,在湖泊的上游,是一道綿延數(shù)十公里的灰色冰山。我在湖泊南岸找了一塊平坦的,四周滿是小葉杜鵑林的草坪,作為當(dāng)晚的露宿地。
我拾了一些枯樹枝,生起一堆火,我得給自己燒一壺香噴噴的奶茶。
桔紅色的天空漸漸變成了深藍(lán)色,兩顆明亮的星星在我左邊的天空閃爍。山風(fēng)挾著對岸冰川的寒氣,圍著我的營火打旋。終于奶茶開了,當(dāng)我把熱騰騰的奶茶倒進(jìn)碗里,抬頭一看,黑夜也隨之降臨了。
臨近黎明,兩只餓極了的大灰狼醞釀著準(zhǔn)備襲擊我,我從它們發(fā)顫的嚎叫聲中聽出了它們的圖謀。我退到一塊突兀的巖石上,背靠冰川。它們循著我的足跡來到巖石下面。其中一只呲著牙從正面向我發(fā)起了進(jìn)攻,而另一只,則在巖石的后面心急火燎地尋找能夠攀上巖石的路徑。我用俄坤擊退了餓狼的四次進(jìn)攻,當(dāng)它發(fā)起第五次攻擊的時候,俄坤準(zhǔn)確無誤的擊中了它的左肋。它慘叫一聲,落荒而逃。
“它活不過明天的。”我望著另一只倉皇逃竄的餓狼,對穹瑪說。
我給穹瑪喂了一袋混和著茶葉和糌粑的飼料,給自己做了頓豐盛的早餐,我倆都算打了一次牙祭。太陽出來前,我又繼續(xù)上路了。
“尕足尕爾恰?他剛趕著牛上山了。”第三天早上,我來到讓央的帳篷門口。讓央掀開帳篷,告訴我。
“我找著哥哥了。”我說。
“是一件好事。”他說。
“可現(xiàn)在還在別人手里,我得請他幫忙。”
“大概幾天?”
“我也說不準(zhǔn)。”我說,“不過你放心,我會按你給他的工錢來補(bǔ)償你的損失。”
讓央沒有說話,不知是拒絕還是默許。
12
“什么?”尕足尕爾恰迅速勒住馬,“你是說你哥哥被茸真抓去了,那個婊子養(yǎng)的惡魔?”
“我想是那樣的。”
“消息可靠?”
“十有八九。”
“你這是讓我送死,不,是讓我們大家送死。”他情緒激動地說,“看在老天的份上,也許你壓根兒就沒聽說過這是個什么樣的人。你知道他的口頭禪是什么嗎?既然殺了一個就不在乎殺第二個第三個甚至第一百個,你看,這是人話嗎,這簡直就是魔鬼的咒語。”
“看來你是打定主意不愿去了?”
“對不起,伙計。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從那里面出來以后,就打算讓自己好好享受享受外面的陽光。”
“好吧。”我說,“我從一開始就沒指望你能幫助我取下惡人頭上的帽子。”
他轉(zhuǎn)身打馬離開。我沿著山邊那條小路向西走。我在山坡南面的水塘邊停下來飲馬。一陣馬蹄聲從后面?zhèn)鱽怼?/p>
“嘿嘿,伙計,我怕再也追不上你了。”
“不會的。”我兩眼盯著一只在水里瘋狂地打著旋的牛虻,連頭都沒抬。
“我怕讓央笑話,所以還是決定跟你去,這一次我可是說一不二的。”
“這是你自己說的,你可別后悔。”我說,勒起馬頭,趟過那片水塘。
我倆飛馬急馳,我打算在天黑前抵達(dá)科村。
科村是一座有三十多戶人家的村子,當(dāng)我們到達(dá)科村的時候,一抹殘陽還停留在村子北邊的山脊上。
我們牽著馬,沿一條布滿了牛蹄印的道路緩緩進(jìn)村。
“你們家有貝母蟲草買嗎?”我拉住一個從前面跑過來的小男孩。
“我不知道。”他搖著頭,隨后指了指不遠(yuǎn)處的一座小木屋,“旺扎是做生意的,你們可以去問他。”
那是一座小賣部,和鄉(xiāng)下隨處可見的所有小賣部一樣,它敞開的窗戶上同樣釘著一排鐵柵欄。
“聽說你有貝母和蟲草買?”我把頭湊到窗口。
一個白花花的腦袋從貨架后面探了出來,“你是誰?”他問。
“做小買賣的。”我回答。
“誰告訴你我有貝母蟲草買?”他有些不高興。
“只是聽說,說旺扎有貝母蟲草買。”
“這些該死的家伙。”他罵了一句,“你們找錯人了,我沒有貝母蟲草,只有這些。”他指著貨架上的東西。
“看來我們真的搞錯了,不過現(xiàn)在天快黑了,回去顯然已經(jīng)來不及了,你能告訴我們這地方哪兒有吃和住的地方嗎?”
“這一下算你問對人了。”他說,“你們一直向前走,直到在你右邊出現(xiàn)了一個大空地為止,那兒吃的喝的全都有。”
我們照他說的一直向前走,果真在我們右邊出現(xiàn)了很大一個空地。空地的兩邊停滿了車。
“都是些外地來的游客。”尕足尕爾恰說。
我們找了個地方拴好馬,然后朝坐落在東邊的一座房子走去。夜幕已經(jīng)降臨,四周閃爍著令人眩目的霓虹燈。三三兩兩操著不同口音的人不時從我們身邊走過。
推門進(jìn)去,一股熱浪裹著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撲面而來。
“啊,我的心臟要爆炸了,這該死的歌廳。”尕足尕爾恰在我身后抱怨。
“伙計,你得忍著點(diǎn)兒。”我說。“今晚我請客,吃的喝的你想什么點(diǎn)什么。”
我們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來。
“我們到這樣的地方來干嗎?”
“也許一會兒就有答案了。”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就不能直接告訴我答案?”
我沒有回答他,而是用目光仔細(xì)搜尋著酒吧里的每一個角落。
歌廳的包間幾乎都有人,坐在大廳里的人大多數(shù)都是外地的游客。我和尕足尕爾恰每人只喝了兩瓶啤酒,尕足尕爾恰就嚷著要上洗手間。
我一個人坐著,一會兒,我感覺有人在拍我的
肩膀。我抬頭一看,是那個矮小的胖子。
“別那樣看著我。”他說。
他挪開我身旁的軟椅,坐下。
“不是一個人?”他指著尕足尕爾恰的杯子問我。
我點(diǎn)點(diǎn)頭。
“我知道你會來的。”
“你現(xiàn)在跟茸真一塊?”
“看來你的消息夠靈的了。”
“然后抓了一個人?”
“那事我沒有參與,都是我來之前的事,不過……”他湊到我耳邊,“那人的確是你哥哥。”
“你看見他了?你肯定是他?”
“昨天的午飯就是我給他送去的,我還告訴他你在找他。他不像你,是一個沉不住氣的家伙,整天嚷著要去報案,讓警察來抓我們。”
“你這樣做的理由是什么?”我滿腦子的疑惑,“你這是放長線釣大魚還是玩別的花招,反正我看你也樂于做那樣的事。”
“因為你推遲了我去那邊報到的時間,我可不是那種知恩不報的人。”他說,“再說,茸真想把他賣到外省,我可不想賣人,賣牛可以,賣人可是要下地獄的。”
“賣有生命的東西,都得下地獄。”我說。
“不過你把我交給警察那事我會找機(jī)會感謝的。”
“我也不會讓哥哥失望的。”我向他舉起酒杯。
“我不在乎。”他抓過酒瓶喝下一大口啤酒。
我身后包間的門打開了,從里面走出來五、六個人。
“我們要走了,你在這兒干嗎,其洛?”一個黑黑的高個子朝矮小的胖子喊道。
“我遇上了一個朋友,茸真。”其洛說。
“朋友?”茸真上上下下打量著我,我也打量著他。他鼻尖上那顆大黑痣讓我覺得十分眼熟。
“該死。”我低聲說。這就是茸真,那個曾經(jīng)在我們縣城四處溜達(dá)的傳說中的萬元戶?
“你到這兒來干什么?”他問我。
“做點(diǎn)小生意。”
“什么生意?”
“比如收點(diǎn)蟲草貝母什么的。”
“收蟲草貝母?我估計你在這兒什么也收不到。”他看了看他的伙伴,然后大笑著說,“其洛,你就替你朋友問問我們這兒的蟲草貝母愿不愿意被陌生人收走。”
他帶著那伙人走出了大門。
“你哥哥關(guān)在村西的一間木屋里,有兩個守衛(wèi),木屋是漆過的,很好找。”其洛站起來,拍拍我的肩膀,“這下我們誰也不欠誰了。”
在洗手間磨蹭了大半天的尕足尕爾恰走了出來。“那家伙是誰?”
“答案。”我說。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就不能對我明說?”尕足尕爾恰說。
“是茸真那伙。”
“該死。”他罵了一句,張皇失措地朝四周望了望,“你看天都這么晚了,我們還是去找一個地方住下來吧。”
“今晚不用睡覺了,狐貍。”我說,“天亮前我們就離開這里,帶著我哥哥。”
“今晚?”
“對,就在今晚。”我說,“看見白天進(jìn)來時關(guān)在棚欄內(nèi)的馬了嗎?你的任務(wù)就是騎上我們的馬,再順手從馬群里牽走一匹,然后趕到小路交叉處的河邊等我。”
“牽馬,你那不是叫我偷嗎?”
“告訴你吧,那些馬都是茸真或搶或偷得來的,你不是去偷,而是順手帶一兩匹走。”我說,“不過你得小心,要是被發(fā)現(xiàn)了,茸真會發(fā)動全村人把我們撕成碎片的。”
我看看時間,還差十分鐘才到凌晨一點(diǎn)。
“咱倆再等等,兩個小時后動手。”我說,“時間還早,要不一人再來兩瓶?”
“行。”尕足尕爾恰揮揮手,“反正我已經(jīng)喝通了。”
13
空中掛著一輪滿月,這真是一個月明星稀的清涼夜晚。
我隱身在房屋投下的陰影里輕步向前。偶爾有一兩聲貓頭鷹的低吼從遠(yuǎn)處傳來,把原本就已十分寂靜的高原之夜映襯得更加寂寥空曠,在這樣的夜晚行走,你得格外小心,哪怕折斷一根細(xì)小的樹枝,其聲音都會傳出數(shù)十米遠(yuǎn)。
我踮著腳尖走過一片無遮無攔的開闊地,其洛說的那座小木屋出現(xiàn)在前面的一塊臺地上。
我躲在暗處仔細(xì)觀察,只發(fā)現(xiàn)一個人坐在門口的長凳上,另一個人始終沒見他的影子。
這可難住了我,其洛說有兩個守衛(wèi),如果他說的是真的,另一個人到哪兒去了?
我在距離木屋十多米遠(yuǎn)的地方轉(zhuǎn)了一圈,沒發(fā)現(xiàn)第二個人。
也許今晚只有一個人,我想。
我從木屋的北面弓著身子悄悄靠過去。在木屋轉(zhuǎn)角處,我直起身子探頭看看,那人抱著槍,正打著瞌睡。
我抽出俄坤,輕輕走過去。他聽見了聲音,睜開眼慌慌張張地站起來。我迅速揮動右臂,閃著寒光的俄坤繞過他的脖子。我用力一拉俄坤,他雙臂一張,像要展翅飛翔一般一頭栽倒在我的腳下。
“別出聲。”我提起他的衣領(lǐng)。
他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氣,圓瞪著雙眼,還憤怒地用雙腳踢我。
“你真是一個令人討厭的家伙。”我照準(zhǔn)他的腦袋狠狠一拳,他哼也沒哼一聲,腦袋一歪,不動了。我用他的腰帶捆住他的雙手,嘴里塞了一團(tuán)破布。并從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小木屋的鑰匙。
“扎洛。”我走進(jìn)木屋低聲喊道。
“班丹,我在這兒。”我順著聲音看過去,扎洛蜷縮在木屋南邊的角落里。
我快步走過去。“扎洛,快起來。”我說,“我們回家去。”
他站了起來,但一下子又跌倒在地上。
“怎么了?你受傷了?”我蹲下身子,將他的手臂放到我肩上,我感覺到他在輕輕打顫。
“你來了真好。”他說。
“現(xiàn)在我們走吧。”我吃力地將他扶起來。“我們得想辦法走出這個村子,至少在第二個人出現(xiàn)之前。”
“我會盡量的。”他說,
出了小木屋,沒有看到另一個人的身影。我松了一口氣。
走出不到一百米,我就聽到扎洛在痛苦地呻吟。“我不行了。”他搖著頭說,“幾天前,他們用木棍抽我的腿,之后腿一著地就鉆心地疼,直到昨天我才意識到一定是斷了。”
我看了看四周,倘若直接穿過村子,可以很快到達(dá)我們會合的地方,但村子里數(shù)目眾多的狗們絕不會讓我們輕松通過。遠(yuǎn)離狗群不驚動村子的惟一辦法就是繞過村子后面的小山坡。
“放我下來,班丹。”扎洛拍著我的肩膀,“讓我自己走吧。”
“你就省下力氣呆會兒用來騎馬吧。”
圓月正在緩緩向西滑落。寂靜無邊的草原上,除了我的腳步聲,我還聽到霜凍降落在草尖上的沙沙聲。
“班丹,我在這兒。”一個黑影從樹叢中鉆出來。
“馬呢?”
“在那邊。”尕足尕爾恰,“怎么那么長時間,我都快凍出病來了。”
“幫我把他放下來。”我說,“他的腿斷了,得麻煩你把馬牽到這兒來。”
尕足尕爾恰從樹林里牽出一匹灰馬。
我們把扎洛扶上馬,村子那邊突然傳來了幾聲狗叫,接著響起了嘈雜的人聲。
“快上馬離開。”我說,“他們發(fā)現(xiàn)了我們。”
尕足尕爾恰翻身上馬,朝村子方向打馬沖去。
“這該死的家伙,到底要搞什么鬼名堂。”
我扶著扎洛趟過小溪。我聽見尕足尕爾恰在喊叫,“來吧,我在這兒呢,來吧。”他一邊喊一邊打著唿哨。我勒馬回頭,看到一團(tuán)黑影穿過樹林,朝和我們相反的方向奔去。
“尕足尕爾恰把自己當(dāng)餌了。”我說,“他想把狼群引向東邊。”
“尕足尕爾恰是誰?”扎洛問。
“機(jī)村尕足家的措崩,尕足尕爾恰是他外號。”
“他出來了?”
“是的,他在里面呆了十年。”我說。
喧鬧聲越過山頭,在黎明即將到來的時候漸漸消逝在遠(yuǎn)山的后面。
我們已走了近十公里的路程,興許已經(jīng)離開了危險。但誰知道呢?在沒有完全確定之前,我們不能有絲毫地松懈。我們小心地盡量貼著森林邊緣前行。
第二天,我們到了讓央的牧場,沒有尕足尕爾恰的影子,我開始擔(dān)心起他來。
讓央默默不語地幫我把扎洛扶進(jìn)帳篷。
“他的腿傷了。”我說。
讓央低頭查看了一下傷勢,“斷了一根骨頭。”他說。
他出去了一會兒,接著手拿一把新鮮的紅柳樹皮和兩片松木板走進(jìn)來。
“我要給他接骨了,你得幫我按住他。”
我抓住哥哥的雙手,讓央抓著扎洛的腳腕,用力一拉,隨著咔嚓一聲輕響,扎洛像被人扎了一針?biāo)频膹椓似饋怼?/p>
“放松點(diǎn)。”讓央說。他先用兩片松木板固定住斷腿,然后又用紅柳樹皮自上而下將整個斷腿緊緊捆住。
“至少兩天以后你們才能走。”他說,“一旦錯位以后就成瘸子了。”
“好吧。”我說。“順便可以等等尕足尕爾恰。”
當(dāng)天黃昏時分,或者稍晚的時候,天下起了大雨。
我們在澎湃的雨聲里一直坐到天黑。臨近午夜,嘈雜的雨聲里傳來馬蹄聲,我和讓央起身走出帳篷,是尕足尕爾恰,他俯在馬鞍上,人和馬仿佛剛從水里打撈出來似的。
我們把他平放在他的床上,見他胸前有一大片血跡。
“他們用槍打中了我。”他微笑著對我說,“可我還是在眾人的面前溜掉了。”
“你命大。”讓央說。
“我也這么想。唉,伙計,看在老天的份上,你們能不能夠先給我弄點(diǎn)水喝。”他說。
我遞給他一碗水,他接過去喝了一大口,然后抬眼看著我,他微微打著顫,臉色煞白。
“你們還沒走?”他問。
“沒有,讓央說我們兩天后才能上路。”
“那樣也好。”他抬起身子看了看前胸,“你看我還這么清醒,這傷不算很重是嗎?”
“是的。”我說,“今晚好好睡一覺,明天我?guī)闵厢t(yī)院。”
“我不喜歡醫(yī)院,那里面的氣味令人作嘔。”
“我會找東西替你堵上鼻子的。”
“那樣感覺肯定不錯。”他說,“伙計,要是我今晚一覺睡下再沒醒過來,你可別忘了我托你帶的口信。”
“你放心。”我說。我握著他的手,感覺就像握了一塊冰冷的石頭。
半夜,我被外面的一聲響動驚醒。好像已經(jīng)到了下半夜。我打開手電,側(cè)頭看了看哥哥,見他正睜著雙眼望著天窗外面漆黑的夜空。
“在想什么?”我問。
“這一切經(jīng)歷讓我覺得好像是一場夢。”他說。
“告訴我你是怎樣走進(jìn)夢境里去的?”
“那都是你離開以后發(fā)生的事。”他說,“鄰村有幾戶人家受不了盜牛賊無休止的騷擾,打算低價買掉自己的牛群。我得到這個消息后也趕了去,買了六十多頭回來,打算養(yǎng)一段時間等牦牛價格漲了以后再賣掉。”
“你手頭緊?”
“不是,我想用這些錢中的一部分帶父母去朝圣,另一部分給你娶妻子。倒霉的是幾個月后被盜牛賊給偷走了。我跟著他們,我想要回來,不管有天大的困難我都想要回來。”
我心里一顫。
“知道媽媽是怎么想的嗎?”沉默了一會兒,我說。
“她怎么想的?”
“她整天都生活在矛盾中,你到底是被盜牛賊殺了還是像村里人說的那樣趕著別人的牛群跑了?”
“你是怎么想的?”
“那還用問,當(dāng)然是替媽媽找到答案,無論最終是希望還是失望。”
“真有那個必要?”
“是的,不管好壞,我不希望那個答案的惟一擁有者再也無法出現(xiàn)在我們的視野里,也不希望我那瘦骨伶仃的侄兒從此忘了爸爸的長相。”我說。
我聽到哥哥翻了一下身,還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責(zé)任編輯:藍(lán)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