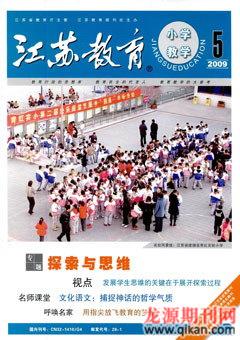母乳“文化”:文化語文課堂的民族性追求
陳國安
語文,對中國人而言就是作為母語的漢語教育。母語教育是人生開始的“根”,每一個人精神成長的文化“母乳”都應該是母語!
民族文化作為個體精神成長的“母乳”文化,起點是本民族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這些口耳相傳的口語形態(tài)的文本,祝禧于此是有不一般理解的,請由“開天辟地”一課來看祝禧文化語文課堂的一種民族性追求。
口耳相傳的本民族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是“母乳”文化的最表層特征之一,這樣的文本不是固定形態(tài)的每次“復制”都一致的一個文字文本,而是口頭流傳的“話本”,它因說話者(敘述者)不同而呈現(xiàn)出不同的內(nèi)容,于是雖同一個故事情節(jié),因不同的“爸爸媽媽”說給不同的“孩子”聽,內(nèi)容則出現(xiàn)了不完全一致的情況,但又不是一點都不同,這是最有“多元性”的講述吧。祝禧看到了這一形態(tài)的文本,將其引入課堂,真正地將“母乳”文化作為個體文化建構的起點了!
課堂中口耳相傳的講述形式不僅僅是將文字用口語形式表述出來,更重要的是將文字文本的“前生”變成“來世”,在課堂情境中把文字文本的“前生”——口語形態(tài)的文本重現(xiàn)。這恰似乎又成了文字文本的延續(xù)——“來世”。老祖宗當年的講述,現(xiàn)在的語文課堂,文本情境,課堂情境,生活情境,快速地疊加,文化的魅力頓時“民族”地顯現(xiàn)出了民族色彩的思考!
師:讓我們把掌聲送給4位同學,因為他們不僅把書上的內(nèi)容變成了自己的語言。充分地消化,而且把自己的語言變成了口頭語言,生動地講述出來。所以才讓我們覺得聽神話故事是一種享受。
文化語文課堂還時刻關注母語的文字特征,這是一種“母乳”文化的民族性追求。這節(jié)課從“大”、“人”、“天”、“立”這些象形字和會意字開始。漢字竟然成了課堂情境營造的誘因,成了充滿神奇的神話故事的引子。這是將我們這個民族的獨特的文化思維方式解構后演繹給孩子看。孩子未必懂得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理解這個世界的鑰匙,但總有一天他們會豁然開朗的!
最精彩的是祝禧講“立”字,如果戲用“八股”結構分析這一階段的課堂的話,“大”是“起”,導入主題;“天”是“承”,過渡而已;“立”是轉(zhuǎn),轉(zhuǎn)入主題;“開天辟地”是“合”,課堂的主題。“立”是“開天辟地”的課堂情境的關鍵詞之一。《說文》:“立,住也。從大,立一之上。”徐鉉校錄:“大,人也;一,地也。會意。”林義光《文源》:“象人正立地上形。”祝禧這一“轉(zhuǎn)”極具民族文化特質(zhì),無論是徐鉉所講“會意字”還是林義光所講“象形字”,于此而言,祝禧課堂這一環(huán)節(jié)的處理不能不說是極具匠心的。
文化除了表現(xiàn)在口語形態(tài)的文本和文字形態(tài)的文本中,還深深地根植于每一個個體的心底。任何一個民族的人都會首先在心底籠上一層本民族價值觀的色彩,這是一個人的生命底色!這是一種民族形態(tài)的文化精神!
“開天辟地”這個神話故事本身有著我們民族的一種精神,同時在這個神話中也有著我們民族的一種世界觀和價值觀。如未有世界之前如“雞子”,“雞子”這個形象就是極有民族性的,似乎是從“無形生命狀態(tài)”轉(zhuǎn)化成“有形生命狀態(tài)”的一種最生活化的代表范式。
師:同學們的想象真豐富,看來這不是一般我們所見的大雞蛋,它是一只神奇的宇宙蛋,那么混沌一團,沒有光,沒有聲音,可以說無規(guī)無序。有的同學說對大神盤古開天辟地感興趣,你們覺得盤古開天辟地的時候有意恩在哪里?我們來看看課文中是怎么寫的。
這是一種神話閱讀的方式,這是在還原一種民族的原始文化思維。
此外祝禧還抓住了神話所體現(xiàn)的我們這個民族的“勞動創(chuàng)造世界”的原始理解,學生在那一刻進入了民族色彩極濃的神話世界,他們的文化精神開始孕育了。
“垂死化身”是祝禧在勞動創(chuàng)世展開之后一再引導學生理解的一個命題,這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種極為浪漫的原始文化思維。“人”死了之后身體歸于大自然,化為三山五岳、花草樹木,這也帶有一種人類的原始文化思維的浪漫色彩。當然,著名的神話研究學者袁珂先生還列舉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很多種“開辟神話”中巨人尸體化為萬物的神話。我想祝禧也是看到過這些神話的,所以她的文化課堂由此就拓展開了,從本民族“母乳”文化的神話到其他民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課堂的文化視野一下子就打開了,這也許是祝禧文化課堂“大氣”的地方吧。
總之,祝禧文化課堂所追求的這一種民族的“母乳”文化是我所極為驚喜的,這是作為母語教育的語文教育“回家”之“路”的開始,走這樣一條路的人是要有睿智和勇氣的,我想祝禧是有睿智和勇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