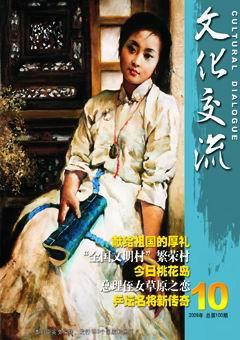海鷗老人的故事
謝昭光


從海鷗老人雕像說(shuō)起
在一個(g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到云南參加一個(gè)會(huì)議。在昆明報(bào)到前夕,我下榻海鷗賓館。這里離翠湖很近,翌晨我就直奔翠湖而去。翠湖公園早早就布滿了晨練的人群。漫步其間,仿佛自己也是其中一員。湖邊有一海鷗與老人的鑄像特別引人注目,仔細(xì)一瞧,那老人與海鷗相逗成趣,栩栩如生。旁邊還有一塊石碑,題為《海鷗老人鑄像落成記》:
翠湖,古之澤國(guó)也,連滇池,后水位漸退,形成沼澤,稱(chēng)菜海子。明清之際,先為沐府林園,后為吳氏宮苑,波光柳色,魚(yú)躍鳶飛,昔人有詩(shī)贊曰:六尺小船呼不應(yīng),水禽沙鳥(niǎo)向人啼。此昔日翠湖之景色也。及至近代,曾一度湖水干涸,殿宇鳩居,水禽沙鳥(niǎo)之景已不復(fù)見(jiàn)。今時(shí)逢盛世,翠湖幾經(jīng)修治,引水注湖,種樹(shù)植草,藍(lán)天碧水,柳暗花明,彰顯我春城之麗質(zhì),呈現(xiàn)我鄯闡之豐姿。環(huán)境優(yōu)美,百鳥(niǎo)不招而至,二十年前,海鷗從天而降,翔集湖光之表,嬉戲綠水之間。市民驚喜,群集觀賞,拋食饗鷗,迎接天外來(lái)客。爾后,每年入冬,群鷗必如期而至,誠(chéng)乃祥瑞之兆也。觀鷗人群中有一古稀老者,背雖駝而神采朗健,言笑而面目慈祥,每日按時(shí)來(lái)飼鷗,多年不輟。久之,眾人矚目,獨(dú)不知其為何許人也,乃以海鷗老人稱(chēng)之……
這是一個(gè)非常動(dòng)人的故事。
有一天,昆明《都市時(shí)報(bào)》記者采訪了他,才知道這位海鷗老人的一點(diǎn)身世。他叫吳慶恒,建國(guó)初畢業(yè)于革命大學(xué),“風(fēng)華正茂,意氣俊爽,因與世齟齬,屢遭縲紲之禍,歲月不居,年華虛度,及至平反,已垂垂老矣”。
然而,吳慶恒雖命運(yùn)多舛,卻具有“黌宮學(xué)養(yǎng),深明齊物之理,人海沉浮,恒存仁愛(ài)之心,故能人鷗相處,以尋詩(shī)意棲居”。
他節(jié)衣縮食,從微薄的退休金中留出大半來(lái)購(gòu)買(mǎi)海鷗的飼料,并且天天喂養(yǎng),“與鷗同樂(lè)”。實(shí)際上,這是一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麗圖景,也是春城人民愛(ài)鷗情結(jié)的象征。
碑文最后寫(xiě)道:“如今斯人已逝而精神不泯,故鑄像以志其永恒。夫天人合一,國(guó)泰民安,乃華夏文明之精義,然則,海鷗老人之精神,亦可通天人之道也。”
此碑是昆明《都市快報(bào)》、市園林綠化局和翠湖公園于2006年1月18日立的。愛(ài)鷗自有后來(lái)人。從此,殊不知又有多少喜愛(ài)海鷗的春城市民延續(xù)著“與鷗同樂(lè)”的故事,無(wú)論青年男女或婦孺老少,無(wú)論在職的或離退休的,也無(wú)論國(guó)內(nèi)旅客或國(guó)際游人……
這其中,有一位是昆明的離休干部,他攜帶著數(shù)碼相機(jī)和海鷗飼料,幾乎天天出現(xiàn)在這里,并不厭其煩地給海鷗喂養(yǎng)飼料,給沒(méi)帶相機(jī)的游客拍攝人鷗照片,因而他也就與海鷗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他是昆明市又一位杰出的“海鷗老人”,名叫高峰。
愛(ài)鷗情緣
高峰老人對(duì)于海鷗的情緣源自“海鷗落戶昆明”。
1985年11月12日,一群白色的海鳥(niǎo)在昆明城市上空盤(pán)旋翱翔。一開(kāi)始人們沒(méi)太注意,因?yàn)檫@里是候鳥(niǎo)遷徙的通道,然而這次鳥(niǎo)兒們沒(méi)離開(kāi),幾天后,在盤(pán)龍江、大觀樓、翠湖都可以看到它們美麗的倩影。
傳說(shuō),海鷗是一位美麗善良的漁家姑娘,為尋找出海未歸的戀人,身著素裝,赤誠(chéng)忠心,祈求神靈將自己化為一只俊鳥(niǎo),飛翔在蒼茫的大海上。她依嗚吁吁地叫喊著,仿佛是在向每朵浪花詢問(wèn):“他在這里嗎?……”那急切的神情,那凄厲的叫聲,寄托著漁家姑娘對(duì)戀人的無(wú)限深情。
在海鷗家族中,共有43個(gè)種類(lèi),通常統(tǒng)稱(chēng)它們?yōu)椤昂zt”是用詞不當(dāng)?shù)?因?yàn)橹挥泻苌賻追N鷗長(zhǎng)期待在海上。最能體現(xiàn)海鷗這兩個(gè)字的是鯡鷗,其數(shù)位居群鷗之冠。它離開(kāi)海岸主要是尋找一處沒(méi)有干擾和騷亂的繁殖地。高峰說(shuō),海鷗的繁殖地通常在海岸、湖、河周?chē)恼訚蓾竦?這些地方大多氣候溫和、陽(yáng)光明媚、餌料豐富。昆明市鳥(niǎo)類(lèi)協(xié)會(huì)曾收到兩只俄羅斯貝加爾湖威爾克漢雅繁殖地環(huán)志放飛的海鷗。高峰說(shuō),海鷗從繁殖地飛往昆明,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是來(lái)自貝加爾湖濕地。
每年的9月以后,貝加爾湖就會(huì)進(jìn)入冰天雪地。為了生存,嚴(yán)冬到來(lái)前,海鷗遠(yuǎn)離家鄉(xiāng),舉家向溫暖的南方遷徙。它們由北而南,千里迢迢,從西伯利亞飛到昆明,空間直線距離3000多公里。鳥(niǎo)類(lèi)學(xué)家研究表明:“海鷗遷徙的行為驚心動(dòng)魄”,每次遷徙,數(shù)字高時(shí),甚至?xí)幸话胱笥业募t嘴鷗慘烈死亡。
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海鷗是一群勇士。高峰說(shuō),候鳥(niǎo)的繁殖地冬季不適合鳥(niǎo)類(lèi)生存。越冬地,海鷗會(huì)選擇冬天氣候溫暖,有水域、濕地、有豐富食物和安全的環(huán)境。這成就了昆明人與海鷗的這份情緣。
鷗傳兩岸情
2008年12月15日,這是一個(gè)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即臺(tái)灣海峽兩岸直接通郵的第一天,80歲的高峰意外地收到了蓋有臺(tái)灣郵戳的信。信封正面粘貼著臺(tái)灣郵票,寄信人的地址:臺(tái)灣嘉義市中山路422號(hào),寄信人為何信吉。
打開(kāi)信封一看,里面裝有一張刻錄數(shù)碼照片的光盤(pán)。
高峰興奮地回憶說(shuō):那是半個(gè)多月前的11月27日,“我到大觀公園去拍人與紅嘴鷗親密接觸的照片,何信吉和另一位臺(tái)灣同胞當(dāng)即請(qǐng)我當(dāng)‘模特,我一直喂著紅嘴鷗讓他們拍到滿意為止。拍完后他們連聲道謝,表示回臺(tái)灣后一定要將照片寄來(lái)給我。”
沒(méi)想到他們說(shuō)話算數(shù)。老人說(shuō),這封信可以成為兩岸通郵的見(jiàn)證,紅嘴鷗也成了兩岸人民友誼的信使。他和兩位臺(tái)灣游客的信件來(lái)往會(huì)一直保持下去。
這件事使高老非常感動(dòng)。他用東巴文創(chuàng)作了《海鷗傳情,兩岸和諧》《和》等十多件作品。截至今年3月,他共拍攝了500多張海鷗照片,其中有百歲老人,也有一兩歲的小孩。這些照片內(nèi)容健康向上,如《海鷗奶奶》《飛舞》等,有趣味,有思想,也有藝術(shù)性。
尤為可貴的是,老人還創(chuàng)造性地將書(shū)法和攝影藝術(shù)結(jié)合起來(lái),創(chuàng)作了《雙喜臨門(mén)》《亭亭玉立》等十多幅作品。每幅作品均為書(shū)法和照片有機(jī)地組合,互為映襯,相得益彰。他說(shuō),這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他的作品《海鷗傳情》被評(píng)為“愛(ài)鷗十大經(jīng)典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