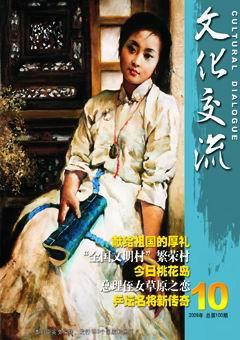尋找孟姜女故里
戚天法



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孟姜女故事家喻戶曉,膾炙人口。優美的《孟姜女》小調到處傳唱,小調旋律中人們熟悉了孟姜女、范杞梁、秦始皇。孟姜女的忠貞愛情故事,早在國人的記憶中定格,且根深蒂固。
幾年前,我在考察西安至玉門那段“蜿蜒躍上千仞間,延綿不絕古長城”時,總抑制不住對“巨龍”和“脊梁”的萬千感慨,深為數百萬筑城的“范杞梁”所付出的智慧與艱辛而折服。“民之傳說,史之影矣”,我的疑云與好奇心陡然而生:孟姜女故事流傳了兩千余年,她的家鄉又在何方何地呢?這不僅是民間文學工作者需要考證的課題,更是舞臺劇和電視劇創作者必須獲知的人文元素和環境平臺。
“眾里尋你千百度,卻在寧波海隅處。”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寧波民間故事集》和《寧海民間文學集成》兩書中發現了孟姜女的故里,它竟在浙江寧海縣桑州鎮境內。書中一篇題為《孟姜女升天石》的故事中有附言曰:“桑州鎮海云寺邊有孟家、姜家兩村和孟姜女廟。廟址尚存。”
盡管古人左丘明在《春秋左傳》中有記述:“陳人城, 板墜而殺人……齊侯歸,遇杞梁妻于郊,使吊之。”公孫丑在《孟子·杞梁妻》一書中亦有記載:“昔者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這兩書明確指點孟姜女的家鄉應在齊魯一帶無疑。已故的著名劇作家顧錫東先生在游遼東后有詩贈我:“潮頭插劍欲屠龍,碣石峻嶙對峙雄,扈蹕求仙旗蔽日,揮鞭作賦馬嘶風。秦宮碑斷蒿萊草,姜女墳空荊棘叢。卻喜兩岐歌麥秀,凌云鐵塔遍遼東。”詩明白告之孟姜女墳墓和故事發生在遼東。然而資深的民間文學專家賀學君先生在《論四大民間傳說的總體特征》一文中說:“我國民間文學大師顧頡剛先生在1927年統計,山東、江蘇、山西、陜西、湖北、河南、湖南、云南、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直隸、京兆、奉天等地都有孟姜女的傳說在流傳,有的被認為是孟姜女的出生地,有的被認為是她的葬身地,有的則認為是她尋夫經過的地點。許多地方還出現了相關的文化建筑,僅孟姜女墓或祠廟或古跡就有20處之多。”
我受此民間信息的誘惑,疑竇與好奇心油然生發。尋思此事:如若不謬,那么孟姜女傳說如同梁祝傳說、徐福東渡傳說一樣,又將是一張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寧波金名片。為此,我邀請了幾位記者驅車前往桑州鎮實地調查與采風。
在桑州外岡山西麓的永樂寺東側,我與記者找到了那座近似塵封的孟姜女廟,以及和孟姜女比肩并坐的范杞梁塑像,大家都感到莫大的驚訝和興奮。出于崇敬之情,我們在考究廟匾,查找廟碑,攝錄具有文物考古價值的廟磚瓦礫時,顯得格外細致和小心翼翼,惟恐錯過點滴的佐證實物。在我們尋訪當地“三老”、錄制“孟姜女小調”的過程中,又意外獲知了每年農歷六月初三日,那些早已遠離故土的孟姓、姜姓和范姓的后裔們,都會從四面八方聚集攏來,使冷落的廟堂頓時呈現祭奠的盛況,情同清明節掃墓一般。據傳,此習俗已成為當地民眾的鄉風。
我又翻開桑州鎮的歷代年譜,它那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底蘊卻令我不得不信服。史料記載,桑州鎮雖然素稱浙東的窮鄉僻壤,可就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海隅山溝里,在宋、明、清三個朝代中出現過八名進士、三名舉人和一名探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山川秀美,百姓勤勉,文化底蘊深厚,堪稱人杰地靈。那么人們定會思索:在千年的歷史演變中,有誰能反證桑州之地沒有出現過“孟姜女和范杞梁”這樣的尋常百姓呢?又有誰能否認忠貞熾烈的“孟姜女”甘為遠方服役的丈夫送去寒衣呢?作為桑州鎮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濃厚的文化底蘊,我驀然意識到自己創作的戲劇和電視劇《孟姜女》中,不論孟姜女夫婦也好,秦始皇也好,萬里長城應當是他們不朽生命的共同背景。孟范的忠貞愛情和凄美傳說的社會意義和愛情的文學、史學價值,不應停留在血淚控訴秦皇暴政這一層面上,它應當從人生道德的評判角度來透視普通人對全局利益,即國家命運的心理狀態和道德標準,藉以探討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從而反映出作為具體的人對國家、對社會、對人類應當具有的公民責任感這一重大的社會主題上來。不過,我認為在孟姜女的愛情內涵里,應當表現得尤為突出和強烈。當然,也不放棄對秦始皇作出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鑒于這一理念,我創作的舞臺劇和電視劇《孟姜女》,獲得了浙江省“五個一”工程獎。
孟姜女的家鄉在浙東,還是在山東?或在遼東?這雖然無關宏旨,都不重要,然而,我認為孟姜女故里確在寧海桑州鎮這片靈秀之地;我也絕對堅信,寧海桑州鎮這片靈秀之地,終將成為寧波歷史文化旅游的又一處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