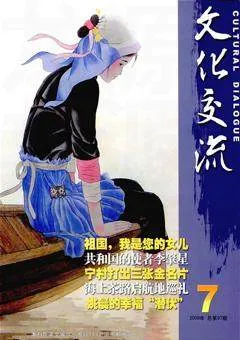浮生只合“小團圓”
戚永曄


2009年5月24日晚7點,上海。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內,燈火通明,高朋滿座。
臺下,是復旦大學的博學鴻儒、莘莘學子,以及來自各地的資深“張愛玲迷”。
臺上,是主持校訂《張愛玲全集》的內地散文家止庵,以及香港資深文藝評論學者馬家輝。
他們討論的只有一個話題:張愛玲的遺作、一出版便引發文化界熱議的《小團圓》。
止庵說:“《小團圓》是一部情感小說,一部心理小說,是張愛玲對自己一生中的各種感情,包括親情、愛情、友情等等的全面清算。“小團圓”不是“大團圓”的一部分,而是對“大團圓”的徹底顛覆,生命的輪回到此為止。”
馬家輝說:“《小團圓》畢竟是小說,不是傳記或歷史。即便書中寫了很多真人真事,小說家與傳記作者也有著不同的把握,而在《小團圓》中,這種小說家的把握來得特別充分,特別深切,又特別微妙。”
在文化名流們的侃侃而談中,那一段浮華的過往漸漸明晰。而早已身在歲月那頭的張愛玲,也仿佛正在和如今的“張迷”們,通過《小團圓》這個窗口,進行著心與心的交流。
緣起手稿
香港,加多利山,一片鬧中取靜的豪宅區。很少有人知道,這里有一幢古樸別致的公寓樓,曾留下過張愛玲生活的印記。
公寓的主人名叫宋淇,他和他的妻子鄺文美,都是張愛玲的生前好友。他們曾是張愛玲的文學顧問和經紀人,幫助她打理出版等事務。作為翻譯家和著名紅學評論家,宋淇常常會對張愛玲的作品給出中肯的意見。
1961年夏天,張愛玲為了給自己的美國丈夫賴雅籌集醫藥費,回香港趕寫了兩個劇本。那次她就住在好友宋淇夫婦家中,終日足不出戶,只顧埋頭寫作。
據說張愛玲當年借住的那間臥室非常簡單,“只有一間房,一張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她去美國讀書后,宋淇夫婦便把這個房間改成了衛生間。曾有“張迷”慕名而來,他們說想看看張愛玲居住過的地方,宋淇只能帶他們看一個衛生間。
1995年時.張愛玲在洛杉磯過世。臨終前,她交代遺囑執行人林式同,把所有的遺物都寄給好友宋淇夫婦,其中包括從未出版面世的《小團圓》手稿。
但之后1996年,宋淇去世;2003年,鄺文美又不幸中風,生活難以自理。于是,整理張氏遺物的工作,落在了他們的兒子宋以朗身上。“直至那時,我才知道,母親對張愛玲的手稿、作品及遺物所負有的責任。也是在那時,我第一次知道有《小團圓》的手稿。”宋以朗說。
可惜的是,宋以朗的母親鄺文美病重,言語多模糊不清,不能很清楚地告訴他此稿的來龍去脈,而宋以朗本人對于張愛玲的記憶,更多則是停留在兒時那點模糊的印象。
“看到整部手稿共有628頁,我是一口氣給讀完的。”雖然當時這部書沒有出版過,但還是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而且知道它影射了一段真實的歷史,想到這里,宋以朗的心情難以平復。
宋以朗說,《小團圓》手稿看起來并不像初次寫作時的草稿,上面少有修改的痕跡。應該是張愛玲寫完這本書后,她又專門謄寫了一遍。所有這六百多頁的手稿,筆跡非常清晰而完整。“當你看到一部這樣的手稿,它是一個女作家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地謄寫出來,而且字跡一筆一畫寫得極為工整時,我就告訴自己:不管怎樣,我都不會毀掉這樣一部作品。這是一個人用全部的心寫就的作品。”
心路迂回
如何處理一直沒有出版的《小團圓》?宋以朗不得不做出決定。于是,他花了幾個月時間整理和仔細研究查閱張愛玲和父母之間在40年間600多封來往書信,找到了《小團圓》一直被“雪藏”的緣由:
1970年,張愛玲開始動筆寫這本書,時年49歲。彼時,她與胡蘭成已離婚20年,賴雅也已去世。一切塵埃落定,給了張愛玲寫作這一本頗有總結、自傳意義小說的機緣。
1976年,張愛玲完成了整部小說的寫作,把副本郵寄到香港的宋淇那里,委托他交由香港和臺灣的報社出版。當時,她希望每天在報紙上刊登一部分,分幾個月連載完,這樣可以吸引讀者往下讀。但宋淇看了原稿后卻潑了張愛玲涼水,他說:“停下來。別再想出版的事了,不要跟任何人提起這部書稿。”當時有太復雜的政治背景。張愛玲是個有名的作家,任何一個人只要了解張愛玲,就知道這一本寫她自己人生經歷的作品。而彼時胡蘭成在臺灣中央研究所教書。這遭到很多人的非議:怎能讓一個漢奸教書?
在宋淇看來,如果在這時,張愛玲出版《小團圓》,胡蘭成很可能借機在臺灣舉行新聞發布會,以此挽救自己在臺灣的聲譽和窘境。
之后,宋淇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可以讓《小團圓》面世。他對張愛玲建議:“你為什么不將書中男主人公的角色重新設定,比如把他寫成一個雙面間諜,最后還被人暗殺了。做了這樣的改動,胡蘭成就不能站出來說:我就是書中的那個人。因為世人都知道,你胡蘭成是個漢奸,為日偽政府工作。你怎敢說自己還是雙面間諜?而且在小說中,男主角都死了,你更不可能是那個男主角。”
但這個建議沒被張愛玲采納,她不止一次透出本意——“最好的材料是你深知的材料”,又在信中回復宋淇的建議說,“因為情節需要,無法改頭換面”。只是在時機上躊躇不定。她當時的顧慮所在,又不單單是因為胡蘭成和民族主義,更牽掛到母親、姑姑等兩邊家史。《小團圓》與其他的小說不同,這是張愛玲自己的故事。在她心中,這段歷史深埋太久。一旦動筆,恰如洪水決堤,無法再停下來。相反,如果非要依宋淇之意大變妝容,再好的材料豈不是也換了味道?這樣看來,張真心所期待的,并非是濃妝艷抹的登場,反倒是素面朝天的亮相。
但在這之后,張愛玲也擔心人們對“張胡之戀”的興趣,會沖淡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考慮要銷毀這部小說。但是遲遲不忍心自己動手。有時候,她說要銷毀;有時候,她又說必須完成,否則對不起讀者。直到1993年,張愛玲還致信平鑫濤說:“欣聞《對照記》將在11月后發表,《小團圓》一定要盡早寫完,不再會對讀者食言”,而其在遺囑中又說“小說手稿應該銷毀,不予出版”。
浮生已逝
洗盡鉛華后,《小團圓》終究以鉛字的形式出現在讀者面前。
張愛玲遺囑里的“《小團圓》要毀掉”,想必已經成了此書最大的賣點,就像是從焚燒的書堆中搶救而出,無論內容是否精彩,總值得奉為至寶。據香港的朋友說,此書上市不過半月,不僅高居各大書店排行榜首,不少書局更是掛出售罄的牌子,一時一書難求。大陸這邊,自從2月上市以來,也被人一路追捧,而有人更將其稱為中國的《追憶逝水年華》。
對于他們,張愛玲的個人經歷及其創作小說中的情節,既屬于青春歲月關于愛情的集體記憶,又是消費時代永不過時的談資。
《小團圓》的故事情節其實很簡單,講述了女作家九莉的經歷,幼年時在新舊世代交替中,身處的傳統家族,而后在修道院女子中學遇到各式同學,直到九莉遇上被稱為漢奸的有婦之夫邵之雍之后,一系列的感情的迷亂、掙扎,而且這種感情旋渦沒有隨著時間慢慢平靜,反而越來越狂猛,最后演化成一種焦慮,憂心忡忡,連夢境都是這種感覺。
明眼人都看得出,“九莉”不像張愛玲其他作品里的女主角一樣,是經過深度提煉的形象。相反,她是張愛玲自己的倒影。張愛玲曾抱怨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寫他們之間的事“夾纏不清”。在完成《小團圓》的初稿后,張愛玲曾告訴摯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之后也還有點什么東西在。”而這,恐怕才是張愛玲寫作《小團圓》的最終意義。
“她永遠看見他的半側面,背著亮坐在斜對面的沙發椅上,瘦削的面頰,眼窩里略有些憔悴的陰影,弓形的嘴唇,邊上有棱。沉默了下來的時候,用手去捻沙發椅扶手上的一根毛呢線頭,帶著一絲微笑,目光下視,像捧著一滿杯的水,小心不潑出來。”
這是《小團圓》里,女主角審視男主角外貌氣質的一段描寫。女作家內心的細膩,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馬家輝說得好,浮生在世,驚鴻一瞥,“大團圓”只是過程,而“小團圓”才是最終所歸。對于感情來說,越是想忘卻的,越是記得清晰。感情遭受變故之后,若遇上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往往會撕裂那看似愈合的傷口。
在這一場無涯的愛情中,比照作者經歷讀《小團圓》,各人的觀點也不同。有的人同情張愛玲,譴責胡蘭成薄情寡義,有的人也會批駁張愛玲的狹隘。而站在局外人立場上說,愛無罪,若深陷其中,又有誰能逃脫得了呢?就像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情感歷程一樣,是是非非,版本眾多,當事者迷,旁觀者也未必能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