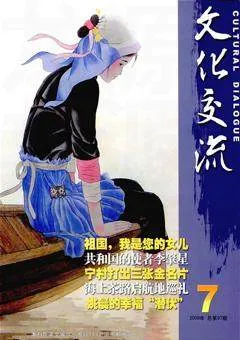風情萬種的老撾女孩
木 子


我是從越南去老撾的,辦理老撾方面的入境手續,原來和買張公交IC卡一樣簡單!特別是在你已經辦好簽證的情況下。你甚至不用擔心語言問題,老撾方面的邊防人員會說中文,雖然只是“簡單的”。
初識老撾女孩
來到老撾,首先傳入耳中的是一句動聽的“Hay You(嘿,你)換老幣嗎”,這個“你”字說得鏗鏘有力,卻又帶著幾分婉轉,它從一個年輕的老撾女孩口中說出,給我一種異樣的感覺。
細看這女孩,如越南的女性一般將全身裹得密不透風,只露出上額和一雙大大的眼睛,她緊緊地盯著我,好像放松一點就會失去這筆生意。在越南海關旁,我已兌換了少許美金,忙連聲推卻。
摩托車很快將我從海關載到了老撾的邊境小鎮。鎮子很小,只有一條街道,兩旁的房屋與越南通常三四層的小洋房相比,反差很大,全部是低矮的平房或稍高一點的竹樓。最后一班到沙灣拿吉的車已經出發了,只好在鎮上小住一晚。
安置好行李,我閑坐在小旅館前的遮陽吧,一群做外匯兌換生意的老撾女孩也懶懶散散地呆坐四周,打扮竟同我看到的第一個老撾女子一模一樣,一有生意來了,如同覓到食物的麻雀蜂擁而上。
耐不住困倦,一個紫衣女孩后來在一旁的長凳上睡著了,她的睡姿很奇特,只因為她的裝扮很怪異:黑色緊身長褲,紫色短袖T恤,白色長筒遮陽手套和口罩,黃綠相間的圓帽,唯一沒有被遮掩的是雙腳。
入夜,一陣喧鬧的音樂把我引到小鎮聚會的地方,它設在小山坡上,一邊是小吃、燒烤和各種游樂小玩意,居然還有在中國常見的彈珠有獎游戲;另一邊是燈火輝煌的露天舞場,四周擺滿了餐桌,男人和女人聚在一起開懷暢飲。老撾女子身穿傳統的筒裙,在我眼里,那是一種很“性感”的服飾,它將老撾女子婀娜苗條的身段展現無遺。音樂響起,人們圍成圈,面對面翩翩起舞,節奏很慢,類似傣族舞蹈,手腕的動作和腳步的移動尤其優美,叫人浮想聯翩。旁邊一個老撾小伙慫恿我也去跳,但最終我依然只是個看客。
一手撐傘玩“飛車”
去往沙灣拿吉的交通工具是那種破舊的老式汽車,雖然我的個子不算很高,但座椅間距依然逼仄,我只得老老實實地挺直腰板,兩腿保持垂直。車廂后面一段沒有座椅,被當成了家禽牲畜寄運欄,有雞有鴨,有羊,甚至還有小黑豬。車子開動時,車身吱吱啞啞的聲音與各種禽畜發出的鳴叫聲交織在一起,像原野協奏曲,熱鬧,好玩。
綠色與黃色是老撾的兩種原色,黃色的土地上到處是蔥郁高大的綠樹,大大小小簡陋的或灰或黃的竹樓在空曠的原野上輕柔而立。
汽車在一座小村莊旁停下載客,我伸了伸腰,活動一下有點麻木的筋骨,隨意朝旁邊的竹樓瞥去,就在那一瞬間,我呆住了。一個坐著的老撾女孩,那眼神里有些說不出的傷感,卻又那么純凈、自然、真摯。
這是一個老撾女孩目送親人離去的眼神。她,18歲左右的樣子,一頭長長的秀發自然垂散肩頭,穿著老撾傳統的筒裙,裸著雙腳和小腿,兩手依在胸前,端坐在竹樓前沿,兩腿垂落下來;她一動也不動,烏黑的雙眸凝視著親人離去的方向,陷入無盡的思緒之中;她雖然很黑,但無礙于那種自然流露的端莊與美麗。我舉起了相機,但很快又放下,生怕打擾她。
帶著對老撾女孩的驚鴻一瞥,我們到達沙灣拿吉,這里是老撾的古都,一座安靜而古樸的城市,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公共汽車,只有摩托車和三輪車。湄公河的那一邊就是泰國,夜幕降臨,四周沒有燈紅酒綠與紛亂嘈雜,只有夏蟲的清鳴。我驚訝地看到老撾女孩用一只手撐傘,另一只手開摩托車,即使在摩托車奇多而陽光同樣毒辣的越南,我也沒有瞧見任何女子用這么“酷”的方式飛馳。老撾女孩永遠讓你意外。
遭遇調皮鬼
除了首都萬象和古都沙灣拿吉,老撾最熱鬧的地方是瑯勃拉。四月初的瑯勃拉市是水的世界,為了慶祝傣歷新年,這里的人早早就開始潑水了。要知道,潑到身上的水越多,意味著收到的新年祝福就越豐厚。于是我們各自買了一支中號水槍,每天隨身攜帶,一來防身,二來也找機會偷襲。
一天夜里,我們提著水槍,來到湄公河邊的一家露天酒吧,每個人自然又是一瓶Beer Laos。喝完酒,卻發現水槍的“彈藥”早就用完,于是向酒吧的女孩討水。女孩很快提著一大桶水走過來,邊走邊笑。我已隱隱感到有點不對勁,難道?可就在遲疑間,整桶水已經兜頭潑了我一身,然后是一陣爆笑。
反擊!我們很快投入戰斗,分工合作,找水盆、水桶、找水源。對方又來了一個女孩增援,并控制了水龍頭和水管,我們顧不了那么多,就算全身早已濕透,也要給兩個如此放肆的野蠻女孩一點紀念。
“戰斗”的慘烈程度可想而知,我們一次又一次沖向女孩們的陣地,向她們“傾訴”我們的“祝福”,戰場上尖叫聲不斷。最可笑和可氣的是,每一次女孩們舉起雙手喊著“戰斗結束了”,結果卻總是又一次突然襲擊。難道這也是老撾女孩的性格?被潑得濕透的我們面面相覷。投降吧,徹底沒轍了。
次日就是離開的時候了,下午路過酒吧,那女孩對我做了一個潑水的動作:“嘿,你……今晚還來潑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