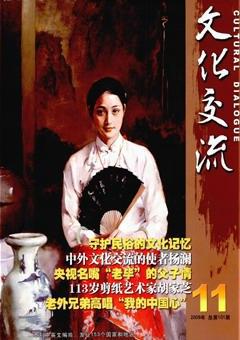陶心云與紹興東湖
陳榮力

位于紹興鳥鳴山麓的東湖,素以江南第一山水盆景著稱。與杭州西湖相比,東湖的煙波雖不大,但清奇精致卻十分出眾。這樣的清奇精致,由人工積年累月取石采鑿而成。東湖原是紹興東門外的一個著名石宕,上劈山腹、下穿地肺的采鑿,泛成一泓幽峭的清水,積時既久巖石便起變化,淹沒了斧鑿之痕,成為獨特的景致。當然,如果沒有在此基礎上的人工構筑與布置,使其凸現丘壑之美的同時,更添清幽之趣,東湖也不可能能成為現在的東湖。這筑堤造橋、營室建亭,以點鐵成金的手筆和匠心,將一個景致獨特的石宕提升成一方勝景的始作俑者,便是一個叫陶浚宣的人。
陶浚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沖,號心云,別號東湖居士,清會稽陶堰人。1876年,30歲的陶心云鄉試中舉。10年后經會試,出任由張之洞創辦的廣東廣雅書院山長,并在同為張創辦的廣雅書局任職,后又任職于湖北志書局。陶心云在廣州待得頗久,他也因此結識了不少華僑和革命志士,十分同情革命,主張救國必須提倡教育與進行政治革新。
1896年,為東湖的獨特景致所吸引,陶心云與從兄弟仲彝、七彪集資8000余銀元,利用采石形成的峭壁、水塘,筑堤修路隔湖化幽,營室建亭綴水活景,造橋植樹倚石立美,對鳥鳴山下的石宕開展全方位的人工構筑與布置。三年后主要工程告罄并取名為東湖。當然陶心云建設東湖,并不僅僅只是修山水于江湖,而是寄托著實踐自己提倡教育、進行政治革新的主張在內的。因此在建設東湖之初,他即在湖旁筑屋數間,設立了東湖通藝學堂(后改為東湖法政學堂)。學堂開設史學(包括經、史)、算學(天文、數學)、譯學(外語)等課程,聘請謝飛麟、陶成章等為教席,傳播新知識、新思想。周作人由日本歸國后,亦在東湖通藝學堂里授過兩個月的英文課。1904年,也就在東湖建成的5年后,將近花甲的陶心云返還故鄉定居,一心經營東湖。因為陶心云同情革命,當時紹興的革命志士秋瑾、徐錫麟等,常在東湖通藝學堂聚會,此處也成為光復會的秘密聯絡點之一。1907年,秋瑾被害后,陶心云曾書寫萬言奏折,指斥浙江巡撫張曾敫草菅人命,枉殺無辜,其手稿今尚存浙江圖書館。1912年,陶成章遇刺后,陶心云特將東湖玻璃廳辟為“陶社”,以示紀念。
如果說因建設東湖揚名桑梓的話,那么陶心云的聞名晚清,則更多地緣于他杰出的書法和詩學成就。同為會稽人氏的晚清老名士李慈銘,在他的《越縵堂日記》里,稱陶心云書法“頗清老有風力”,“詞翰高潔,亦有魏晉風骨”。在“廣雅書局”圖書館、校書堂等處,留下過陶心云的許多楹聯,如:“地接南園,看蒼翠成林,疑身到六橋三竺;天開東壁,聚黃卷滿架,此中有百宋千元。”“校經愛學顧千里;佞宋遙分黃一廛。”在當時的廣州,諸多的五羊人士更以一得陶心云的書法和黃士陵的刻印為榮。
十分講究寫字的梁啟超,對陶心云的書法可用崇拜來形容。他在《飲冰室文集》之《稷水論書序》一文中曾這樣說:“……一日,蔣百里挾一寫本至,且曰:三十年夙負,合坐索矣。視之,則會稽陶心云《論書絕句百首》原稿。”“……計十二三歲時,在粵秀堂三君祠見心老書一楹帖,目眩魂搖不能去,學書之興自此。”陶心云曾幾次到過北京,且與時任相國的翁同龢結識、論書。翁同龢是十分講究碑版的大書家,又位高相國,但對陶心云卻持手書相邀,并一再申明“免去官禮,彼此輕衣小帽相見”。翁同龢在光緒十六年(1890)五月初六的日記中,記下過他初次見陶心云的文字:“陶文沖(浚宣)來見。此君善六朝書,能詩,今在廣雅書局。”
陶心云自幼習碑,上自秦漢下迄六朝,無所不學,每臨一碑,輒至數千百遍,其臨池之勤,自幼至晚年不輟寒暑。也有坊間傳聞,說他寫字的時間都在晚上,而且緊閉門戶,不讓人看見的。也正是憑了這樣的勤奮,陶心云真草篆隸皆精,尤工魏書,其筆力之雄勁、筆法之壯麗,幾臻化境。當年光緒時所鑄銀元、角子、銅板上“光緒通寶”的模字和今蘇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的碑刻,皆為其所書。在工書法的同時,陶心云也善詩,每每登臨佳山秀水,便有詩留存,當年和五羊人士往來酬酢也寫下不少詩,其詩風清新可喜,留有《論書絕句百首》一幀。
隨著時間的推移,陶心云的作品大都散失了,而唯有他花了大量心血建設且晚年定居的紹興東湖,還相對集中地留存了一些。東湖相關景點上由陶心云自己撰對、自己書寫的一些撰聯、碑刻,如:陶公洞峭壁之“倒下蒼藤成篆籀;劈開翠峽走風雷”、仙桃洞橫額之“洞五百尺不見底;桃三千年一開花”、飲淥亭之“聞木樨香否;知游魚樂乎”、飲心亭之“崖壁千尋,此是大斧劈畫法;漁舫一葉,如入古桃源圖中”、東湖入口處之“此是山陰道上;如來西子湖頭”等等,為我們提供了一睹陶心云書法雄勁風骨和細品詩句清麗風采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