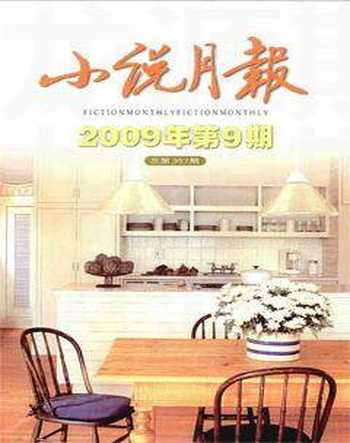好人難尋
紅 柯
1
馬奮祺年前調到縣文化館,周末回家,老婆娃還在村子里,娃念書老婆種地。看了老婆娃,馬奮祺還要去看看王醫生和店老板老趙。兩個老朋友就笑:“到了縣上就沒交下新朋友?”馬奮祺就說:“我這年紀還交啥新朋友?縣城那地方想交也交不下新朋友。”王醫生說:“縣城還算個城?西安寶雞還馬馬虎虎,縣城頂多就是個大村莊。”馬奮祺跟王醫生碰了一杯,“對著哩,對著哩,縣城算個屁,就是個大村莊,沒啥了不起,又不是北京上海。”王醫生的娃在上海念大學,王醫生有條件說這話。
馬奮祺調到縣文化館,就沒開心過,同事們全是城里人,馬奮祺一只腳在城里一只腳還在泥坑里,這是同事私下談閑話說出來的。馬奮祺老婆娃在農村,馬奮祺想把娃弄到城里念書,跑斷了腿連門兒都摸不著,再聽人家說風涼話,就氣得不行。一個人喝悶酒,都是四五塊錢的太白酒。讓同事看見又一頓恥笑。“太白,太白是老農民喝的。”城里人喝西鳳喝五糧液,牛皮一點的喝茅臺。馬奮祺連茅臺瓶子都沒見過。對馬奮祺來講,太白酒很不錯了。農民過年過節過紅白喜事都打散酒,瓶裝太白都是看老丈人用的。狗日的城里人就這么糟踐太白酒。馬奮祺該捍衛太白酒,人家王醫生就用太白酒招待他與老趙。
周末回家,馬奮祺就帶一瓶太白酒去看老朋友王醫生和老趙。王醫生老婆做幾個菜,把酒裝在錫壺里熱好,這種聚會越來越讓人感到欣慰。王醫生說:“老馬你好好弄,你看你三錘兩梆子就把自己弄到了縣上,再弄上幾下,把老婆娃弄成城里人,你弄不動了你也不后悔。”對呀!老趙也拍大腿,跟馬奮祺碰一杯。馬奮祺連灌兩杯,細細這么一想,這話實在,馬奮祺就拍了大腿。弄!就這么弄!馬奮祺就離開鎮子。
馬奮祺來回騎自行車。二十來里路嘛,對馬奮祺來說碎碎兒的一個事情。馬奮祺推上車子往出走時,一身酒氣,王醫生就勸他坐班車,馬奮祺跨上車子原地轉兩圈:“要鍛煉哩,再不鍛煉,痔瘡長成蘿卜那么大,狗子受罪呀。”馬奮祺和他的車子三搖兩晃出了鎮子。老趙說:“狗子夾得緊緊的,就像夾了個碎人妖精。”
馬奮祺騎車子狗子夾得緊!從村子到鎮上到縣上大家都這么看。沿途的行人也這么看,馬奮祺經過的地方總是一片呼聲:“哈,狗子夾這么緊。”“沒緊褲帶。”“沒騎過車子。”最后這句話有點道理,馬奮祺就像剛學車子的生手,騎得萬分緊張驚心動魄,不要說行人,來來往往的機動車都紛紛讓路,馬奮祺所到之處,草木皆兵,連路都在搖晃。
縣城外邊有一個村子,除了本村人以外住了許多打工的,吵吵嚷嚷跟廟會一樣。小吃小攤擺在路邊,打工的男男女女就在路邊小攤隨便吃點去干活。醪糟面皮,扯面豆腐腦兒,又添了一家烤燒餅的,芝麻燒餅饅頭韭菜合子南瓜合子樣樣式式。馬奮祺從烤饃饃的攤子前邊來來往往三四回了,這個攤子剛開張不到一個月,馬奮祺第一回路過的時候就想下來吃個芝麻燒餅,大老遠就能聞到芝麻的香味,比韭菜、比南瓜還香。那些吃飯的人個個埋頭狠吃,性子急的就掂一個熱氣騰騰的燒餅夾菜合子,或步行或騎車子,車子也有摩托車自行車三輪車,車子跑得歪歪扭扭,邊走邊吃邊跑邊吃,到城里大街上才能吃完。從村子到城里路不長,可擁擠得厲害。再擁擠也得給馬奮祺讓路,馬奮祺的樣子太嚇人了。奇怪的是沒人罵馬奮祺,大家多多少少都不大穩當,一手駕車一手掂著吃喝,但也沒有馬奮祺那么夸張。說到底還是打工的人厚道,沒有嘲笑馬奮祺的意思。進到城里,大家一邊觀望一邊評點。有認識的還要點明:文化館的大文人,大秀才,哈哈,把狗座都夾斷了。
馬奮祺必須在文化館大門前十幾步地方停下來,他不想讓他的同事再議論他,他推上車子進單位。從同事的表隋上能看出來,大家啥都知道。就這么大個縣城嘛,王醫生說得對,跟村莊沒啥區別。比村莊富,可也比村莊毛病深。啊呸!啥尿地方嘛,我愛咋騎就咋騎,我想咋騎就咋騎。這都是憋在他心里的話,他不說鬼知道。可大家還是知道了。老館長說:“老馬你想開點。”“我好好的我有啥想不開的。”老館長說:“這就對了,你就這么想,反正是你騎車子不是車子騎你。”“你說啥?你說啥?”馬奮祺急了,老館長也吃一驚:“哎呀,你就權當耍雜技哩。”把他娘給日的!馬奮祺在心里罵開了,馬奮祺嘴巴抿緊緊的,馬奮祺心潮起伏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生怕心里的萬丈波瀾噴涌而出,不可收拾。我總不能推著車子進城嘛,又不是進金鑾殿。就在這個時候,鼻子救了他,他聞到了芝麻燒餅的香味。
第一回經過燒餅攤子前時人家賣燒餅的還朝他招呼了一下,他的車子慢下來了,賣燒餅的就掂一個熱騰騰的燒餅朝他晃。他只是放慢了速度,他也確實聞到香味,可他的腿不聽鼻子也不聽嘴巴更不聽肚子,他身體的另一半把他硬給拉走了。而且不是一次。第二次他都下定決心了,停下來,吃上一個熱燒餅。賣燒餅的還是老樣子,熱情得不得了,不停地朝他晃那金黃金黃的燒餅。這回不是腿,是身上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把他拉走了。這股邪勁兒左右了他兩次。他記得清清楚楚是兩次。不就一個燒餅嘛,吃就吃嘛。這一回他非吃不可。沒等人家招呼他,他就從車子上跳下來了,車子差點倒了,他用力過猛,好像鐵道游擊隊在跳敵人的火車。他的腳本能地一撐,沒讓車子倒下去。賣燒餅的已經招呼他了:“老板、老板,嘗一哈(下),嘗一哈(下)。”熱燒餅在麻紙里裹著,他就嘗一哈(下),丟一塊錢,人家找他五毛。他的全部感覺都集中到舌頭上了,燒餅又脆又酥,咬在嘴里發出咯錚錚的聲音,柔和舒緩,就像灶眼兒里的麥草火,麥草火細發,烙鍋盔攤煎餅要用麥草火。人餓急了,也要吃柔和細發的食物。吃酸拌湯吃發面鍋盔。這都是馬奮祺三十四歲以前當農民干體力活的切身體會。
馬奮祺一板一眼認真細致地吃完燒餅,一抬頭,正好到單位門口。
馬奮祺在門口停一下,往回看一眼,半條街,以往他就那么狼狽不堪地騎著車子奔過來,遠遠地跳下車,再推上往單位走,那樣子不但狼狽而且滑稽。
他曾經謀劃過端上一個保溫杯,跟個大干部一樣從城外一路走來。不成,勢太大,那是縣長的派頭,不適合一個文化館的小小的創作員。拿上一根煙,咱也不拿“好貓”,拿“猴王”或者“白沙”,抽上一口,走他個十來步,跟蒸汽火車一樣騰云駕霧穿城而過。不是縣長的人也能這么弄嗎。都謀劃好了。都把煙打火機備齊了。還是老經驗救了他,臨上場前,他在房子里演示一遍,嚇出一身汗,派頭沒了,架子沒了,勢沒了,活脫脫一個戲子,在演戲。馬奮祺骨子里還是個農民,鄙視戲子。戲子很牛皮的,不比官差多少。老觀念作怪,寧可受罪也不淪為戲子之流。馬奮祺技窮沉默。燒餅攤子出現了。剛出攤人家就招呼他。他不理人家,人家也不生氣,一如既往地招呼他,直到放下架子,跳下車子,親口嘗了一哈(下),效果一下子就出來了。
第二回吃燒餅馬奮祺留了心。從燒餅攤子開始,他混在人群里邊走邊吃。那些打工的
人吃得又急又快,三口兩口吃完一個,又開始吃第二個,也是三口兩口吃完,再喝豆漿,豆漿很燙,時間全浪費在喝上了。喝豆漿的占少數,都是工種比較好收入比較高比較講究生活質量的人,大多數人就是兩個燒餅夾面皮,當然是搟面皮和烙面皮。吃肉夾饃的人很少。馬奮祺吃得不緊不慢。馬奮祺就有了心理優勢,就慢下來,就很悠閑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細嚼慢咽。燒餅很有嚼頭,農民自己磨的面粉,不是面粉廠加了各種增白劑的那種面粉。面也醒到了揉到了。肯定是夜里和好面,發一個晚上,天亮開始做,做整整一天,現做現售。進入大街了,人群少了大半,馬奮祺手里的燒餅正好下去一半,另一半可以從容不迫地吃到單位。一手推著車子一手捏著熱燒餅,邊吃邊去上班,一看就是公家人,而且是不太講究的大男人,不怎么愛護自己,緊緊張張地對付一下,忙啊。男人嘛,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樣子走向單位,沒人多看他一眼。馬奮祺十分正常地進了單位。
馬奮祺并不是每天如此,一個禮拜一次嘛。馬奮祺正常了嘛。馬奮祺松了口氣。馬奮祺就想,我干嗎老吃燒餅呀,韭菜合子南瓜合子不是很好嗎。馬奮祺就吃了菜合子。菜合子不耐餓,得吃兩個,韭菜南瓜各一個。也不再拘泥于周末返城時吃,周一至周六天天都能吃。想吃就去吃。
2
大概是某周二的中午,馬奮祺誤了午飯。文化館人少、且窮,開不起灶,就跟博物館文體局在一起開灶,灶也不錯。相比之下,文化館事少,基本上是上班到單位轉一轉,就待在自己屋里看書寫作。馬奮祺也不例外。文化館的人錯過吃飯的機會比別的單位多多了。別人經濟條件馬馬虎虎,誤了飯就上館子。在小攤上吃沒面子。馬奮祺把啥都想開了。關鍵是那個燒餅攤子確實不錯。價格又便宜,一塊錢就能吃飽。某周二的中午,馬奮祺寫完一篇稿子,已經快下午了,他寫得性起,沒有午休,收筆一看表,快兩點了。放松了,喝點水,肚子一下子就空了,好像久旱的土地,遇上水反而更旱,這就不是一點點水的問題了,要降雨,讓老天爺說話。民以食為天,先吃飽肚子,還要吃好吃舒服。馬奮祺在館子里就沒啥舒服過。除過跟王醫生趙老板在一起,馬奮祺就不愛跟人吃飯。不管是在鎮上還是在縣上,跟人吃飯頓頓都是鴻門宴,都是陰謀詭計。馬奮祺也沒指望能在縣城吃上個舒心飯。這個燒餅攤子是個例外,例外得讓人不可思議,讓人懷疑它的真實性。
某周二快下午的時候,馬奮祺步行到城外的燒餅攤子上,賣燒餅的早就把一個熱燒餅掂到手上了。沒有早晨那么多人,擠疙瘩誰也看不清,甚至看不清攤主。現在就清亮多了。攤主是個瘸子,腋窩里夾一條拐杖,身子斜著,擠在人堆里看不出來,單個站著就相當清楚了,掂著熱燒餅問馬奮祺:“老板,老板來一個?”
馬奮祺要了韭菜合子。馬奮祺不急著走,坐在小凳上慢慢吃,吃完韭菜合子,又吃了南瓜合子。菜合子就得一塊錢,有菜嘛,兩塊錢一頓飯不算貴。馬奮祺點一根煙,抽了一口。瘸子看出了他的身份:“你不是老板,你是公家人。”馬奮祺笑笑。馬奮祺又抽一口煙。馬奮祺情愿人家叫他公家人,他就是公家人嘛,吃皇糧快十年了,叫他公家人聽著踏實。叫他老板就相當滑稽了。馬奮祺心情不錯,馬奮祺就指著鐵皮爐子上的那個紅油漆刷的“燒餅”二字說:“有菜合子呀,咋不寫菜合子?”瘸子說:“你就沒嘗出來?燒餅比菜合子地道嘛。”“我還真沒嘗出來。”“菜合子有菜么,那種香是菜帶出來了的,燒餅純純的糧食,做燒餅費的工夫大,燒餅實惠耐饑。”“你把我當麥客呀。”“不是不是,給你實話實說。燒餅是我的拿手好戲,是絕活。”“菜合子呢?”“捎帶著做哩。”“你還是個實在人。”“憑這活人哩,不實實在在弄就日踏尿了。”
馬奮祺就隔三差五到燒餅攤子上解決午飯。有時是菜合子,有時是燒餅。吃燒餅就在相鄰的面皮攤子上要一份面皮,夾上吃有味道,馬奮祺就夾上吃。馬奮祺去之前泡上茶,回來喝茶溫度剛好。熱茶下去,肚子就咕嚕嚕響上一陣子。他拿上一份參考消息,從一版看到四版,可以休息一會兒了。上床之前,再拆開信,是某雜志社來的用稿通知,薄薄的一封信,要是退稿就是個大牛皮紙袋子,就會在同事中間傳一圈,人家還一個勁兒問:發了沒有?發了沒有?別忘了請客。真正的用稿通知就一張紙。人家會把這種信從門底下塞進去。有好幾次他都踩在腳底下,信封上的鞋印比郵戳還清晰。他開門時就小心翼翼,特務一樣探頭探腦觀察一下,再轉身進門。看完用稿通知,往枕頭上一挺,瞇瞪半小時或一小時。下午兩點半,到辦公室去閃一下面,證明他在上班。
大家又有話說了。有人問他:“老馬混得不錯嘛,灶上飯都咽不下去了。”“得是有人請哩?”馬奮祺淡淡來一句:“反正沒餓著。”
不出三天,就真相大白,就有人勸馬奮祺:“小攤上不衛生,小心傳染病。”馬奮祺還是淡淡一句:“吃著美就成,誰還管這些。”“那都是打工的吃飯的地方。”馬奮祺這下可不是淡淡的一句了,馬奮祺嗓門兒高起來了,比得上帕瓦羅蒂了:“打工的咋了?咱就是打工的嘛,咱就給公家打工哩,咱以為咱是誰呀?咱以為咱這搭不是地球?”再也沒人說雜點話了。馬奮祺頭仰得高高地去小攤吃燒餅夾面皮,吃韭菜合子南瓜合子。馬奮祺回到屋子喝了熱茶,先不急著休息,先到院子里轉上兩圈,站在盛開的月季跟前,一邊賞花一邊放肆地打出一串飽嗝,咯咯咯就像裝了一肚子青蛙。有時候還大張著嘴巴,拿根牙簽在嘴里掏啊掏啊掏出一點點東西,啊呸!吐地上。抹抹嘴問老館長:“你看我這副球樣子像不像城里人!”老館長就笑:“你是個難日頭,你是個雌牙,我認得你了。”“你這是表揚我哩,有你這話我就踏實了,人要難日哩,人一難日人就輕松了,人就活出個人樣了。”
就在馬奮祺成為難日頭成為雌牙的這一天,馬奮祺又逍遙自在地去攤上吃燒餅夾面皮。馬奮祺意外地碰到了瘸子的瘋子老婆。馬奮祺聽相鄰的賣面皮的女人說過,瘸子的老婆是個瘋子,只知道吃只知道屙只知道生娃娃,除此之外啥都不知。馬奮祺就說:“那不是個累贅嘛,正正經經娶個老婆嘛。”“好端端個女人誰愿意嫁個殘廢?”“人家有手藝,能掙錢。”“擺小攤子又不是開大飯店開大賓館,又不是掙金山銀山,想娶個好端端的女人做夢去吧。”這話是當著瘸子面說的,瘸子也不生氣:“說的是實話,說的是實話。”賣面皮的女人就笑:“他喜歡瘋老婆喜歡得不得了。不信你問他。”瘸子笑瞇瞇的:“我不心疼我老婆我心疼你呀。”“你挨刀呀。”賣面皮女人的丈夫拉著架子車在一旁咧大嘴笑:“好你瘸子你還想心疼我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要是愿意你就讓瘸子心疼心疼你。”“放你娘狗屁,你吃了屎嗎你嘴這么臭。”拉架子車的丈夫伸伸胳膊展展腰:“我人不輕省我想歇上幾天,誰想頂就頂上幾天。”女人馬上回擊:“大男人這可是你親口說下的,你可別后悔。”“我不后悔,我有啥后悔的,我歇去呀我又不吃虧。”男人
拉上車子走了。女人擺攤子男人拉車子送貨。憑馬奮祺的經驗,這兩口子都是暗藏玄機話里有話。馬奮祺朝路邊的小攤掃了一眼,果然發現五六米以外的那個賣雞蛋醪糟的漢子漲紅了臉,低著頭渾身不自在。馬奮祺就知道這是丈夫在向妻子發出警告,同時也警告了這個給人家女人打瞎主意的男人,甭胡騷情,我可不是好惹的。從女人的話里可以聽出來,女人不敢胡騷情,女人用另一種貌似蠻橫實則惶恐的心態向丈夫表了忠心。往后的日子就平安多了。真正要感謝的還是這個瘸子,他點到為止,夫妻兩人短兵相接乒乓兩下也不傷感情,那個男子也沒丟面子。馬奮祺不由得對瘸子刮目相看。
話題又回到瘸子身上。賣面皮的女人說:“他對老婆可真是細心到家了,跟哄娃娃一樣,老婆連父母都認不出來了就認瘸子,喊一聲瘸子瘋老婆就出來。”賣面皮的女人喊了一聲瘸子,十幾米外的那排房子里就出來一個女人。打一眼看不像個瘋子,而且斯斯文文像女教師,甚至有點秀氣,等走到跟前才發現那雙眼睛空蕩蕩沒有一絲光彩,跟個木頭人一樣。馬奮祺這時候也成了木頭人。
3
馬奮祺不知道他是如何離開那個小攤的。一連好幾天馬奮祺都沒去小攤上吃飯,也沒到單位灶上去吃。馬奮祺跟死人一樣躺了好幾天。差不多快餓死了。大家敲門,喊他,他才應了一聲。開了門,他的樣子肯定很嚇人,把大家嚇壞了。老館長指揮年輕人趕緊往醫院里抬。都抬到院子里了,馬奮祺才喊叫起來:“我沒病我沒病,給我吃的給我喝的。”
院子有風,風一吹把馬奮祺給吹醒了,也吹出感覺了,最大的感覺就是肚子餓,肚子空了好幾天了。
那是大家最熱愛馬奮祺的一天,馬奮祺一輩子都沒有得到過這么多的關愛。馬奮祺想哭。馬奮祺吃著同志們的方便面。那時候方便面剛剛興起,一般人吃不起,幾個愛時髦的年輕人才有這種稀罕東西,都貢獻出來了,泡在飯盒里,熱氣騰騰,吃得馬奮祺滿頭大汗,眼淚汪汪。大家一邊看馬奮祺稀里呼嚕吃方便面,一邊七嘴八舌吵吵嚷嚷,馬奮祺聽到的大概意思是這幾天大家以為馬奮祺神秘失蹤了,甚至有人懷疑馬奮祺受到什么刺激尋了短見,城外的北干渠以及幾條深溝大壑都去搜尋了。唯一漏掉的就是他的房子,黑著燈,叫半天沒動靜,趴窗戶看,床上空蕩蕩、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這三四天馬奮祺就坐在門后的藤椅上仰望天花板似睡非睡,中途曾經夢游般喝了茶水吃了泡漲的茶葉,后來就處于混沌狀態了。同志們再次敲門喊叫時他神不知鬼不覺地應了一聲,這一聲還真救了他的命。兩份方便面下去,馬奮祺就困了,在巨大的困倦中馬奮祺朝大家鞠躬,差點摔倒被同志們扶到床上,就徹底地睡著了。
第二天醒來,馬奮祺沒有立即下床,馬奮祺睜大眼睛望著窗戶外邊,天空灰蒙蒙的,陽光里全是灰塵,陽光也是臟兮兮的。館長來過一次,館長是個書法家,懂點中醫,號號脈,沒啥大毛病,睡上幾天就沒事了。館長說:“你好好休息,不要想啥。”“我這樣子了我還能想啥。”
馬奮祺一直等著館長來詢問一些情況,館長一直沒問,他徹底康復了館長也沒問。他豎起耳朵,跟雷達一樣高度警覺,奇怪得很,一點動靜都沒有。他再也聽不到人家議論他了。他還注意了大家的表情,都很正常很平靜。這種正常這種平靜讓他很不踏實。他開始失眠。看不進去書,寫不成東西。讓電燈泡白花花地把他照著。那時候的養雞專業戶已經開始用大功率的電燈泡徹夜地照射母雞,母雞們讓老板如愿以償,每天下兩個蛋。馬奮祺聽到的議論也是與他專業有關。你看人家老馬,熬一個通宵又一個通宵,熬出來的可是文章呀,那可是精神文明。馬奮祺的耳朵豎得尖尖的,跟刀子一樣,有時馬奮祺還問人家:“你還看到啥?”“電燈泡嘛,亮一個晚上嘛。”“那你聽到了啥?”“吹風哩,蛐蛐叫哩,還能有啥?”不能再問了,再問就赤裸裸了。人家來一句:“你想聽到啥?”他連退路都沒有了。他就不敢再問了。他心里就這么想著。他覺得大家已經知道那件事情了。人人都知道了,也就懶得背后議論了。你又沒辦法問。你又解釋不成。
他開始吃安眠藥。只安然了一禮拜。再吃就不頂用了,問醫生要,醫生不敢開,再開就把你吃死了。“還不如吃死算了,把人難受死了。”醫生就笑:“那么容易讓你死呀,好好活著吧。”
這期間他去了一次賣燒餅的小攤。他還見到了那個瘋女人。瘋女人還朝他笑一下。還好,這回他沒有失態。他甚至伸出手去接瘋女人遞過來的熱燒餅。賣面皮的女人說:“嘿,她能幫上手了。”瘸子也說:“我老婆有救了,能幫我做事了。”也就遞給馬奮祺。另來一個顧客,就不靈驗了,瘋女人沒反應。馬奮祺快撐不住了。瘋女人誰也不理,蹲地上抓石子玩。
瘸子的妹妹,大家經常見的那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一直幫瘸子做生意。其實大多時間在照顧瘋嫂子。姑嫂關系不錯,小姑一招呼,瘋女人就跟上走了。讓馬奮祺吃驚的是瘋女人還有娃娃,兩歲多的一個男娃娃,小姑子抱著,在十幾米外的房子前邊玩兒。租的房子,瘸子說他們離縣城三四十里路,快到另一個縣了,很偏僻的一個地方。
馬奮祺一個月去兩次。第二次情況好多了,他甚至看了一會兒瘋女人。瘋女人這回沒有笑。瘋女人皺著眉頭望著馬奮祺,馬奮祺低下頭,馬奮祺感覺她還在看他。瘸子遞給馬奮祺韭菜合子,瘸子說:“你不用怕她,她瘋瘋癲癲的,除過我除過我妹我兒子她誰都不認,有時候連我都認不出來。”馬奮祺沒吭聲也沒表情。馬奮祺往回走的時候聽見賣面皮的女人對瘸子說:“把你那瘋老婆管好,癡不呆呆瞪著人家,影響生意哩。”
馬奮祺發誓再不到小攤上去了。好像在挑戰自己的神經,過了兩周他又去了。這回瘋女人沒過來,瘋女人在村子里亂跑,小姑子在后邊追,追上了又拉不動,就死死地抱住瘋女人的腿。瘸子過去,瘋女人就不瘋了,乖乖跟小姑子回到房子里。這回馬奮祺沒吃東西,就回去了。馬奮祺回去就后悔了,賣面皮的女人又會抱怨影響了做生意。
有一天,縣城聯合進行掃黃打非,文化館的任務是突擊檢查地攤上的淫穢報刊。收了一大堆,堆在文化館的院子里,后來全都燒掉了。文化館想當廢紙賣掉,公安局不同意。必須燒掉。公安人員冷笑:“賣廢品收購站,再轉到造紙廠,你以為會搗成紙漿呀。”老館長說:“對呀對呀,廢物利用嘛。”公安人員就一板一眼地告訴老館長:“有三分之一能搗成紙漿就不錯了。”老館長真是愚到家了,還追問那三分之二,把公安給氣笑了:“你個蔫老漢你都蔫成茄子了,碎娃們可都是生瓜漏,專偷你這三分之二。”公安出去的時候還嘟嘟囔囔文化館里咋都是老古董加小古董。按要求要寫一份報告,對這些淫穢報刊進行歸類綜合。這是老館長的強項。老館長卻把這個重任交給馬奮祺,馬奮祺推了又推推不掉就接下了。老館長還說:“說不定還能給你提供寫作素材呢。”
馬奮祺還真找到了幾個好素材。馬奮祺很興奮,話也多了,也愛跟大家交流了。大家也都關心馬奮祺。
馬奮祺已經成縣上的名人了,作品越來越多,重要的刊物都發表他的作品了。傳說有可能給老婆娃農轉非。別人問馬奮祺,馬奮祺就神秘一笑,真假難辨。老館長讓馬奮祺寫材料,也有交班的意思。
馬奮祺對這項任務很重視,也很扎實,用了整整一個禮拜。眨眼到了周五,可以收尾了。有個同事又轉交一份材料。大框架出來了,往里邊一塞就可以了。馬奮祺有一種大功告成的感覺。馬奮祺抽一根煙。馬奮祺快兩個月沒回家了。都是那個瘋女人給鬧的。文人脆弱呀。馬奮祺好像在等一件事情。馬奮祺把煙頭摁進煙灰缸,馬奮祺確實在等一件事情。馬奮祺打開新資料看了一會兒,五六份呢,都是描寫妓女墮落的詳細過程,幾乎都有一個程序,純潔少女被色狼欺騙失身,進入非正常生活。其中有幾例,還生了孩子,孩子與未婚媽媽的悲慘遭遇。有的瘋掉了。在瘋掉這一段畫了杠杠,用紅筆畫的。馬奮祺站起來,坐下又站起來,坐下。他知道此時此刻許多雙眼睛從不同方向盯著呢。同志們也太小看他的心理素質了。馬奮祺抽一根煙,不到半小時就把材料整理出來了。不就加兩頁紙嗎?他在眾目睽睽之下喊小戴。小戴是新來的小伙子,打雜的,他吩咐小戴找打印部打出來,明天交給老館長。那時候還沒大禮拜,周六要上班的。對馬奮祺來說,已經是休息日了。馬奮祺迎著眾人隱秘的目光站在院子里,擴胸扭腰轉體,活動筋骨。
馬奮祺到商場去挑了一個電動玩具汽車。馬奮祺到小攤上去吃了燒餅夾面皮。瘸子的妹妹抱著小孩過來了,瘸子說:“你不要來嘛,你看著你嫂子。”“我嫂子睡覺哩。”馬奮祺結了賬,馬奮祺說:“我喜歡碎娃我抱一抱碎娃。”瘸子很高興:“你想抱就抱。”馬奮祺就把娃娃抱起來,兩歲的娃娃很沉的,農村人的習慣不能說娃娃沉,要說娃娃乖,最好是摸摸娃娃的小牛牛。馬奮祺摸了牛牛,娃娃沒哭,還咧嘴露出豁豁牙笑哩。賣面皮的女人說:“他媽是個瘋子,娃乖得很,又乖又靈醒。”瘸子說:“我娃八個月就會叫媽叫爸了。”賣面皮的女人說:“叫他瘋媽他瘋媽答聲哩?”瘸子說:“不答聲,也不鬧,就癡勾勾看著娃娃,沒反應,有反應的話就能治好。”馬奮祺說:“你這當家的不容易呀。”瘸子說:“給自己過日子哩有啥容易不容易的。”馬奮祺就把電動玩具汽車掏出來讓碎娃玩兒,碎娃喜歡得不得了,不跟大人玩兒了,趴地上玩兒汽車。瘸子急了,硬往馬奮祺手里塞錢:“我不能收你的飯錢。”馬奮祺說:“我喜歡碎娃,沒別的意思,大人是大人,娃娃是娃娃。”瘸子說:“我又沒給小汽車的錢嘛,你讓我的面子往哪擱?”賣面皮的女人做出裁判:“老馬你是公家人,你也要理解我們,你給人家娃娃送個玩具,人家請你個客在情在理,燒餅錢你得收下。”馬奮祺就收下燒餅錢。瘸子就松開手。瘸子手上勁很大,抓著你你就別想動彈。
4
馬奮祺徹底放松了。馬奮祺老婆娃農轉非也有眉目了。馬奮祺兩個月沒回家了。馬奮祺先不回村子,先到鎮上見王醫生趙老板。老朋友見面無話不談。王醫生說:“兩個月不見個影子我就知道你弄大事去了,老婆娃的事比啥都大。”三個老朋友這回喝的是西鳳酒,老趙說:“等老馬一家進了城,咱到城里吃老馬去。”又碰了一回酒。
馬奮祺酒后吐真言,告訴兩個老朋友:五六年前廣播站那個瘋掉的姑娘嫁了一個瘸子,在城門口賣燒餅。王醫生趕緊問馬奮祺:“她認出你來沒有?”
“我沒想到她瘋成那個樣子,只認識丈夫小姑子和她兒子。”“她還有兒子?”“兒子又乖又靈醒。”王醫生和老趙就像聽神話故事,大眼瞪小眼,讓他們更驚奇的是馬奮祺沒有他們想象中的痛苦。當年那個鎮廣播站的姑娘跟馬奮祺好了一場,懷了娃娃,在王醫生的私人診所刮宮后瘋了,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了。那時候大家都以為再也見不到她了。三年四年五年,寫快板編故事的馬奮祺幾經磨難,影響越來越大,離開鎮文化站調到縣文化館當創作員。真是山不轉水轉,在縣城跟瘋女人碰上了。
馬奮祺很沉痛地告訴王醫生和老趙:“我最操心的是她嫁了啥男人。嘿,是個瘸子,身殘心不殘,有一顆金子般的心,遠遠超出我的想象,女子嫁了一個好人,你說,你說,嗨,還有啥說的!”馬奮祺腦袋往后一仰,半躺在涼椅上,又是伸腿又是展腰又是舞胳膊:“我最擔心的是怕她墮落。前一響配合公安局掃黃打非,收繳一大堆黃色書刊,亂七八糟都是女人如何如何墮落,天天看這些東西,把人刺激的。最后還要讓我寫材料,把他的,我差點爆炸。女娃是個好女娃啊,她后半生出個啥事,我一輩子良心不得安生。”
王醫生冷冷地問馬奮祺:“你現在安生了?”
“那當然了,我隔三差五去她丈夫的小攤上吃燒餅。”
“照顧生意?”
“話咋這么說哩?我要細心地觀察觀察,我發現她丈夫是個好人,細發得很,比她父母都好,你說這么好的男人全世界有幾個?好人難尋,好人難尋呀!眾里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老趙說:“這挨屎的吟開了唱開了,這挨求的。”馬奮祺站起來,走過來走過去:“你不要說我是挨尿的,你就說我是挨刀的,挨刀的馬奮祺,我比挨上一刀還要痛快,今兒上午我給瘸子的娃娃送了個玩具汽車,我還摸了碎娃的牛牛,我一下子輕松了,展暢了。”王醫生還是那么冷冷的:“有你挨尿的不輕松不展暢的時候。”
馬奮祺當下就硬在那里,足足有十分鐘,沒有說話,只有出氣聲。中間王醫生老婆進來倒一次水,氣氛不對,女人沒言語躲出去了。馬奮祺硬了十分鐘,自己把自己解開了:“老王你是咋了嘛,怪聲怪氣的。”王醫生還是那么不陰不陽:“那是你自己怪,你就覺得我怪,你就覺得全世界都怪。”馬奮祺聲音大起來:“你明明是掃我的興哩嘛。”王醫生還是那么不陰不陽:“我咋能掃你的興,我是給你助興哩。”馬奮祺當下就蔫了,馬奮祺指著王醫生的鼻子:“你你你。”王醫生頭都不抬,只管喝茶。
馬奮祺推上車子都推出小鎮兩三里路了,還推著走。熟人越來越多,熟人就叫:“老馬老馬,你不騎車子咋叫車騎你哩?”馬奮祺往手上一看,我的爺,手里有一輛車子嘛,把他娘給日的,嗨!王醫生王醫生,你咋是這么一個狗東西!這么一罵,馬奮祺就上了車子。
很快到了家,見到了老婆娃。都怪王醫生掃了他的興,他整個人都蔫了。老婆以為他病了。他說沒病。老婆嚇得不敢出聲,兒子上中學了,兒子也怯生生地看黑臉父親。馬奮祺就難受了,我這是干啥哩嘛,把老婆娃嚇成這樣子。馬奮祺就大模大樣咳嗽一聲,摸一下下巴,跟個大領導一樣,沉著臉告訴老婆娃:再等上一兩個月,你倆的戶口就遷到縣上了,把屋里收拾收拾,該帶的帶,該放的放,該送人的送人。老婆還愣著,兒子叫起來,“媽哎,咱吃上商品糧啦,咱成城里人啦。”老婆就笑了:“這么大個喜事還沉個臉,我以為把禍惹下啦。”屋里當下就熱火了。
老婆眨眼做好了飯,油餅雞蛋酸拌湯,不是一個人吃的,是十來口人吃的。老婆把村里
有聲望的人都叫來了,滿滿坐了一炕。老婆把平時攢下的煙酒都拿出來了。全村人都知道馬奮祺全家要進城了。大家高興。村里出個文曲星。老婆心細,老婆發現丈夫心里不展暢。村里人可不這么看。這么大個喜事你看人家馬奮祺,不驚不乍,臉沉得平平的,干大事的人都這樣。大家都覺得馬奮祺了不起。
馬奮祺回到單位,還是蔫蔫的。他沒心思去小攤上吃飯。他返回城里過燒餅攤子時混在人群里混過去了,好像那是個關卡。有好幾次他誤了午飯,就鼓起勁去吃燒餅夾面皮。都走到大街上了,都看見燒餅攤子了,腿腳不聽使喚了,他心里大罵王醫生。王醫生,狗日的王醫生你啥意思嗎?你陰陽怪氣的你到底啥意思嗎?馬奮祺等不及了,這個周末就去問王醫生,到底是啥意思。
還沒到周末,城外出了車禍,女瘋子被拉煤的大卡車軋死了,后輪軋的,不怪司機,司機沒責任。瘸子丈夫也說司機沒責任。瘋子嘛,胡跑亂跑,誰也沒想到她在路邊好好待著,聽見喇叭響,不是鳴笛的喇叭,是那種新式大卡車的收音機放出好聽的音樂還有廣播電臺女播音員的聲音。
女瘋子就奔過去了,就讓汽車后輪軋到了。據說女瘋子曾當過播音員,鄉鎮廣播站的那種廣播員。聽到這個消息馬奮祺不假思索地糾正了大家的議論:“不是據說,是真的,她真的當過廣播員。”
5
瘸子忙了半年,料理老婆的后事。半年后,瘸子還在老地方賣燒餅。馬奮祺到瘸子住的地方,給瘸子的老婆上了香。房東跟瘸子吵過,不讓瘸子在房子里放香爐設靈牌,“到你屋里弄去,這搭又不是你屋。”瘸子就求人家,就加房租,總算對付下來了。馬奮祺上香時房東的女人往里看了看。馬奮祺已經把老婆娃弄到城里了,馬奮祺再也不像老農民了,舉止間有了些威嚴,房東女人沒吭聲走了。瘸子的妹妹大聲對房東女人說:看啥看哩,是娃他舅,你把眼窩睜大是娃他舅。馬奮祺心里一驚,這個碎女子跟妖精似的,說出這么厲害的話,把房東嚇住了,把馬奮祺也嚇住了。馬奮祺把瘸子的兒子,也就是女瘋子的兒子抱在懷里,摸摸后腦勺又給娃擦擦鼻涕,“娃乖得很,越長越乖。”瘸子的妹子讓小侄兒把馬奮祺叫舅,那娃乖得很,連叫三聲舅舅,童子聲,又脆又響,底氣很足,馬奮祺就應了一聲。瘸子的妹妹說:“娃把你叫舅,你要經常來哩。”
馬奮祺就隔三差五去燒餅攤子。節假日就到瘸子住處吃上一頓飯,去時帶些禮物。有一次瘸子喝酒喝多了,就哭了,哭他可憐的女人,連哭帶說,聽得馬奮祺頭皮發麻。瘸子的瘋老婆犯病的時候就脫光衣服。那些流氓混混就趁機糟蹋可憐的女人。女人的肚子莫名其妙大起來過三次,瘸子都打算要這些來路不明的生命了。醫生堅決反對,那都是有先天疾病的胎兒。醫生明確地告訴瘸子:這些流氓都有性病,個個都是污染源。可憐的女人受多大的罪。瘸子這樣結束他的談話:“車禍把她解脫了,她再也不受這個罪了。……她死得很安靜,跟睡著了一樣。”
馬奮祺記得清清楚楚那是他跟瘸子交往以來唯一的一次長談。從那以后瘸子就沉默了。一心一意地賣燒餅,一心一意地撫養孩子。
馬奮祺還記得瘸子把瘋老婆的死當成一種解脫,他就問人家瘸子:“你是不是想讓她死。”瘸子就對馬奮祺望了好半天,瘸子說:“我想這個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了,打從我老婆第一次被人糟蹋我就想這個問題。”馬奮祺永遠也不會告訴別人他也想過這個問題,他第一次在縣城外見到瘋女人時,他就有這個想法。他甚至想到了汽車。還真是汽車。后來他跟王醫生和好了。好幾次他等著王醫生問他:你心里一定想過瘋女人早早死掉,她的存在會讓你難堪。這些都埋在王醫生的眼睛里,王醫生就是不說。王醫生不說誰也沒辦法讓狗日的王醫生說出來。王醫生竟然在馬奮祺毫無防備的時候來了一句:“瘸子是個好人,好人難尋,好人難尋呀!”狗日的王醫生,你啥意思嗎?你說這話你啥意思嗎?馬奮祺心里胡亂喊叫,就像一條瘋狗沒完沒了地叫。
[作者簡介]紅柯,本名楊宏科,陜西岐山人,1962年生,畢業于陜西寶雞師范學院中文系。1986年遠走新疆,在奎屯生活十年。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大河》等6部,中短篇小說集《美麗奴羊》、《躍馬天山》、《太陽發芽》等8部,學術隨筆集2部共約五百萬字。曾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長篇小說獎及多種刊物獎。現在陜西師大文學院任教,中國作家協會會員。